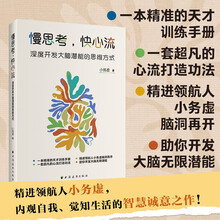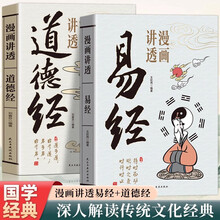一九三八年(成都)
第一信
廷光妹:
去年,家母同令兄绍安开始提到我们的婚事,我因一向从事于学问,常觉此类事之增加累赘。所以好多年来都是违悖母亲之意。但令兄是十年来之朋友,妹在舍间也曾住半年之久,尚能与家母相得;且屡读妹与家母及二妹之函,深佩其意念真切,与流俗人大不相同,所以觉很愿意。因为我想人只要在精神上能互相勉励,求人生之向上,则婚姻也可互相帮助。所以母亲同我谈几次后,便答应了。后来又由令兄征求妹之同意,昨日老伯到成都来会见,也很赞成此事。在老伯之意欲用旧式方法决定,但令兄家母及弟意还是应该由我们彼此增加了解,暑期以后会面时用较正式之形式决定为好,所以我现在就直接同你通信,你该也不会见怪吧。
绍安兄是弟多年的朋友,由他又同令兄斯骏交好。斯骏前同我说过,妹兼有他们二人之长。虽然我比你年龄长,在某方面的知识,或许稍多,但是朋友间的结合主要的是人格性情有互相敬爱之处,以我同令兄等之交好,假设不是社会上有许多已成的习俗,我们应当早成朋友了吧。现在母亲同令兄所提到的事,不过换一种方式来成朋友而已。
我从十四五岁以后,因为父亲的教训即有志于学问。记得在十五岁生日那一天,曾经含着眼泪作了几首要立定志向的什么诗。以后虽然时觉精神懈怠,但大体上总是向着一方向去。在我本来造学问的意思并不只重在知识,生活的充实,人格的完成,一向是我为学究竟的目标。假若将来你有机会看我十四年来的日记,当可知道,只是因为我自己素与社会一般人不大合得来,而十年来都是一人在外漂荡,虽然到处都有朋友,也时有人称赞我,但精神上终感着一种悲凉,遂造成一种孤介的性格,如柏溪随笔便是在这种情调下写的。(柏溪随笔是不好,但到底代表我三年前的生活之一部,所以把它寄上一览。)悲凉的情绪到底是不健全的情绪,孤介的性格到底不及和平温润的性格。所以近数年来遂逐渐加以改变,对于一般社会上的人,鄙弃的意思渐少,而悲悯的意思加以引导的意思渐多。尤其是去年回川后,得家庭生活的慰藉,觉得生活更和适不少,快愉不少。一般人只求享乐是不对的,但是精神上的快愉对于心灵的开展有极大的关系,为求心灵的开展而增加精神上的快愉,我想也不算不对吧。所以我想假如我的家庭生活能更美满一些,我的心灵必将有更大的开展,也许柏溪随笔一类的东西当不会再写,而从更积极的方向去生活了。
至于从纯粹学问方面说,我的兴趣一向在哲学,文学我只欣赏而已。哲学尽管使我受过许多苦痛,然而它到底是可爱的,宇宙人生微妙的道理确实令人玩味不尽。道可乐,真是不错。其次中国真正的哲学家太少了,我想中国应该多有几个,许多朋友于此鼓励我扶持我为我延誉(绍安是最早的一个)。我自己也渐渐相信自己真能。因为哲学的天才其本质在能常常自反,在永远有原始人小孩子那样的心,那样好奇,那样新鲜,我想我是有的,我想只要假以年或使我再能到他处读书,我必然有特殊之成就,与古人比美,又何难哉。你能不笑我夸大吗?
至于我对于国家民族,我想在文化教育上贡献我的力量,关于这点说来话长,以后再说。在最近我能做的事,只是办重光月刊,办此刊贴钱贴精神不少,也算我对国家民族所尽的一些责任。前家母曾寄数份来,你看了有何见教?
我对我的弟妹我当尽我的力培养他们造一种专门的学问,他们都有志趣,都不安于平凡,所以我一定要尽我的责任,使他们有专长,所以我希望朋友的妹妹也如此。听说你要转学,我想这是很好,因为教育学院办得不好是不能发展人的才能的。反不如四川大学等教育系了。以上顺笔写来,拉杂得很,字太潦草,尤为惭愧。我可不知妹意如何?甚望告知,又关于绍安兄与家母所谈之事本身,妹之感想怎样?此事最初虽系各人顺家庭之意,但此事之完成,全看彼此自然之了解与同情,不容丝毫人为。(人与人间一切感情都是要创造的,记得卡本德在爱的成年中如此说,那是一部好书。)所以我想应多通信才对,如果你不愿别人看见你的信,可交华西高中华西大学或省中三校转(不然则交长顺上街),最好由华西高中转唐君毅,并候安好。(从前听说多病近来可好了?)
弟君毅上。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六日
(此信他人未见,不要交与令尊,因他恐不赞成,信又是白话。我希望你回信不要拘执顾忌,假如自己已有选择定方。)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