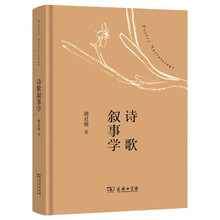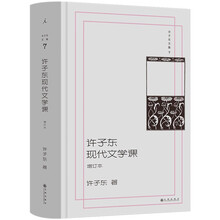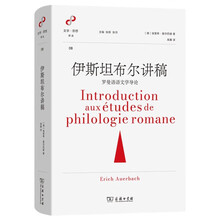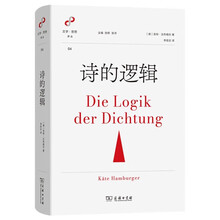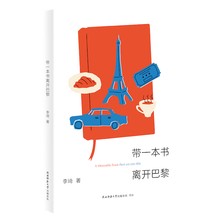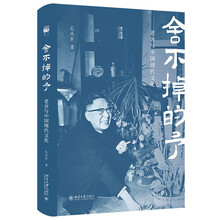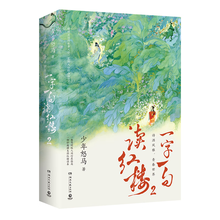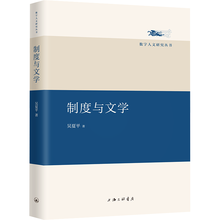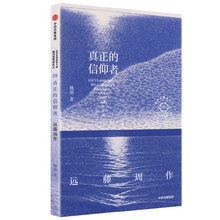3 視點·側面·線索:作品個體及其
與文學史之關係
很有必要對“文學史”本身作一反省,雖然反省並不能保證徹底的澄清,但總比沿襲混亂要好,“語言混亂是我們文明襄最不祥的特徵之一”(韋勒克《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它表徵著思想的混亂。“文學史”通常被視為“文學”和“史”的結合體。就“文學”而言,可以有寬、狹兩種理解。狹義地即指“文翠作品”;廣義地可指整個文學活動:從創作到作品到接受的過程。我相信狹義的理解更明瞭些,當然也應適當聯繫文學活動的整個過程,但其歸宿仍在作品,在作品所具的或曰作品的為人所理解的藝術價值(對接受理論而言)。就如對“哲學史”中的“哲學”,人們最終關注的仍然是思想觀念本身,雖然如康德散步之守時、叔本華在柏林授課被黑格爾奪走聽眾,對理解他們的哲學未始無益,但終究不能是核心一樣。其次看“史”,不妨接受通常的理解,指在過去時間中發生的事件,所謂“文學”的“史”,不妨說是過去時間中發生的文學事件(以作品為中心)。但問題並末結束:以文學作品為核心的文學事件如何構成了“史”?文學史的實踐者早就意識到,聯缀文學事件與其說是構造一部歷史,不如說是展覽歷史的片斷;也就是說文學史中的“文學事件”作為歷史性的客觀知識並不就是“文學史”,“文學史”還須具有内在的聯繫性。要將文學事件聯綴成一個序列,就像文學活動本身,首先是一個敘述問題,需要抉擇和安排,需要一個可以連貫的有意義的模式,從這個角度說,對文學事件之間關係的建構遠不僅是客觀知識,而且是主體詮釋的結果。“真正的歷史對象不是客體,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物,是一種關係,在此關係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真實和歷史理解的真實”(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只要跨越客觀主義的幻想,我們很容易意識到,建構文學史首先是一個理論問題。
首先可以問什麼是“文學”?貌似簡單的問題寶则包含著最難的答案。我們如今接受的文學內涵是過去學術研究中積累下來的,從根本上缺少統一的考察。我們接受這一部分文學為文學性的而排斥了另一部分,實質上是不同時期文學觀念不自覺衝突、調整後的結果。從早期文學史包括大量如今劃歸學術史的内容,到近來古典文翠宏觀研究中還在爭論的關於中國文學是否呈現雜文學特徵的分歧,都體現了對中國文學本體性理論思考的不充分。今天建構文學史,不能沒有對文學本體性理論思考的基點。比如,如果接受吉川幸次郎關於中國文學以實在經驗為中心而無事於積極虛構的觀點(《中國詩史》第一篇),那麼諸如作為虛構藝術的戲曲何以遲生的問題就僅僅具有文學類型學的意義,而不能構成中國文學史的重大課題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