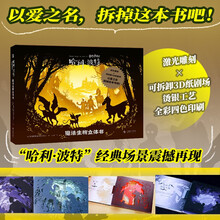中士季马·帕斯图霍夫是个好警察。
当然,他偶尔也会使用一些不太合法的手段来教训无耻的酒鬼们,比如,狠狠地往牙上揍或者用脚踢。但只是在酒鬼严重违法或者拒绝去醒酒所时才为之。季马不排斥从乌克兰或中亚黑户手头收下五百卢布,因为说到底,既然警察的工资少得可怜,那就让那些不法分子把罚金直接交给警察本人好了。他也压根儿不反对在他辖区的小餐馆里给他斟上一杯白兰地取代倒上一杯白开水或本该找回一百卢布零钱时却找给他一千卢布之类的事情发生。
归根结底,工作毕竟是工作。既危险,又艰苦。
这表面上一眼是看不出来的,本应该有物质上的鼓励。
不过季马从来不从妓女和皮条客身上榨钱。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他所受的教育中有某种东西阻止他这么做。季马也从未把那些喝高了但尚未失去理智的百姓往醒酒所里拽过。但是一旦遇到为非作歹之徒,他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追捕。对于小窃案他也认真寻找证据,写出调查报告(当然,如果被害人坚持这么做的话),而且总是尽力记住那些“通缉犯”的面孔。他已经逮住过好几名罪犯,包括一名罪证确凿的杀人凶手。此人先是杀了妻子的情人,这可以原谅;后又杀死妻子,这可以理解;最后又拿着刀子对揭发他妻子不忠行为的邻居行凶。被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激怒的邻居锁紧房门,拨报警电话“02”报了警。
接到报案电话赶来的帕斯图霍夫逮住了正用那尽管涂满了鲜血,却仍然有气无力的书生拳头敲打着铁门的凶手,他接着犹豫了好一会儿,不知是否要将那告密的邻居拖到楼梯边,擦干净他的脸。
总之,季马认为自己是个好警察,认为他距离真理也不是太远。
在一些同僚们中,他看上去是个勤奋的人,就像过去关于阳光城里“不知道先生”的老书中的民警斯维斯杜尔金一样。
(译者注:指尼古拉·诺索夫的童话小说《阳光城的“不知道先生”——民警斯维斯杜尔金的冒险》中的主人公)季马职业生涯中唯一的污点发生在一九九八年一月。当时十分年轻、乳臭未干的他和中士卡明斯基在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区巡逻。卡明斯基当时似乎是作为年轻民警的指导(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民警,或者干脆叫“雷子”,当时既没有时髦的“警察”,也没有侮辱性的“警吊子”之说),他对自己的这一角色很是自豪。他的建议基本归结于在哪里和如何可以轻松挣到钱。于是,在那个夜晚,当看见一位匆匆忙忙从地铁往通道走过去的略带醉意的男子时(此人手上甚至还拿着一瓶开盖的廉价伏特加),卡明斯基兴奋地打了声口哨,接着他们俩赶紧上前拦截。显然,那人马上就得损失五十,没准是一百卢布。
可是,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出了点鬼茬。有几分醉意的男子用让人意料不到的清醒目光瞅了瞅他俩,并建议他俩也喝上一口。那目光清虽然清醒,不过里面含有某种像是早就在人群中失去灵性的无家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让人害怕的,野性的东西。
他俩居然听从了。他们走到小摊前(此时叶利钦执政的混乱时期已接近尾声,但伏特加还可以直接在大街上卖),像疯疯癫癫的人一样嘻嘻哈哈地一人买了一瓶和那位醉汉同样的酒。后来又一人买了一瓶。
再后来又各买了一瓶。
三小时后,帕斯图霍夫和卡明斯基这滑稽搞笑的一对被自己的巡逻队从大街上提了回去,这下才救了他们,还狠狠地罚了他们一顿,但最终没把他们开除出警局。卡明斯基从此没完没了地向别人发誓说遇上的那个醉汉是个催眠师,要么甚至是个通灵人士。帕斯图霍夫没有去诋毁那个醉汉,也没有做一些凭空的猜测。但是他牢牢地记住了那个人。
唯一的原则就是不要在路上再碰见他。
不知是那次愚蠢而丢人的醉酒事件被牢牢地记住了,还是帕斯图霍夫身上渗透上了一些突如其来的能力,反正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也开始能够发现那些带有奇异目光的,不一样的人。帕斯图霍夫自个儿称他们为“狼”和“犬”。
前者的目光中带有某种捕食者的冷漠,不是恶意,不是,狼欺凌羊时没有恶意,甚至带有爱意。帕斯图霍夫对这种人只是尽量避开,同时尽量不引起注意。
后者更像多年前那个有几分醉意的年轻人的目光,像狗的目光。
时而内疚,时而耐心而细致,时而忧伤。只有一点让帕斯图霍夫困惑不解:那些狗不是朝主人看,而是朝主人的小孩看。
所以帕斯图霍夫也避开他们。
相当长一段时间,他这么做还挺有效果的。
如果说孩子是生活的花朵,那么这个孩子就是盛开的仙人掌。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