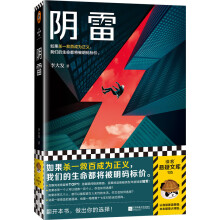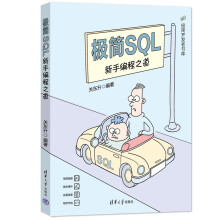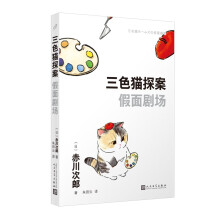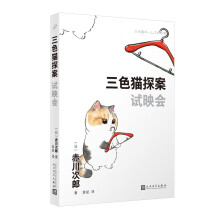王亚蓉,著名的纺织考古学家,古丝织品、古代服饰的保护与修复研究专家。1975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即追随沈从文先生。1978年,转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与王先生并为沈先生古代服饰研究工作的助手。几十年来,先后参与马王堆西汉墓、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陕西法门寺唐塔地宫、北京大葆台汉墓、河北满城汉墓、新疆尼雅中日联合考古发掘汉晋夫妻合葬墓、北京老山汉墓、杭州雷峰塔地宫、江西靖安东周大墓等多处丝织品的现场发掘、清理、保护与修复研究工作。自1985年开始以战国、汉代出土纺织品为标本,开展古代纺织品的实验考古学研究,其成果被湖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收藏展出。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制插图)、《中国民间刺绣》等。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