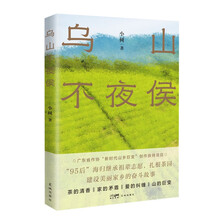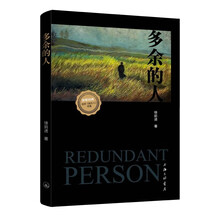船进入上江,就不断有小艇围上来,是那种影视剧里海上枪战中常出现的雅马哈快艇,塑钢船壳,漂亮得像炫翅的金蜂,嗡嗡叫着。它们在陈拴钱的大船前后游弋,犁出一道道白色浪花。拴钱的船尾也拴着一艘,追随着大船。拴钱尤其喜欢驾驶这艘小艇撒野,如同开惯了大卡的司机稀罕玩一玩两轮摩托。但现在拴钱不睬他们,原速前进,一会儿那些小艇就散开了,像是一群没找着肉的苍蝇。
根水把头探进驾驶舱,说,三叔跟他们谈价呢。拴钱朝后视镜瞄了一眼,老三把速度放缓了,后面的船都跟着慢了,船头越来越小。过了一会儿,对讲机嗡嗡的杂音里传来老三陈三宝的声音——哥,他们只要五块呢。
拴钱说,走。
三宝说,哥,你再想想,比白脸那边便宜一半呢,我省了五千,你就省了一万,固城船队就省了几十万。
拴钱说,你再不跟上,耽误在白脸那儿排队了,你莫非真的放得下白脸那儿的乐子?对讲机里只剩了嗡嗡的杂音,老三没声音了。拴钱看后视镜,老三的船头从一点苍蝇屎膨胀成了火柴盒大小,老三还是跟上来了,整个船队也跟上来了。
那些小汽艇是打沙船派出的说客,过了和县,江面上就停泊了三三两两的打沙船,船不大,二三百的吨位,但声音巨大,马达轰鸣能让几里路内的江面震耳欲聋。你想想,它有一根一人抱不过来的铁管子戳在江底,把江底的黄沙吸上高出江面几十米的船舱,那样的力气,吸沙泵需要多大的马力。
拴钱对根水说,就像把一根钢管捅进了,女人的深处。根水说,那这长江的江底一定痛得厉害。拴钱说,你这伢子,还真把这长江比女人了,就是女人,每个月也得把身子里没用的血淌出来。不淌出来就阻了血脉,像这长江,不吸掉江底的泥沙,就要抬高河床,阻塞河道,那也不舒畅。
其实,你把长江比做女人也真没错。拴钱一只手摸出一根烟,另一只手还是放在舵盘上,根水用打火机帮他点上了。拴钱吐出一口烟说,就是一个女人,也不能不停地让男人去干,那就把它当成了婊子,就把这女人害了。
政府限制打沙船,就是规定了不是什么男人都可以干,江底的沙子也是一层保护层,挖深了挖多了,两边的河床就会坍塌,甚至江堤的根基也会凹陷,那洪水一到,两岸边的老百姓就遭殃了。
根水说,你比我们大学里的老师讲课还讲得好哩。
拴钱说,你伢子笑话你叔呢。
确实,长江这碗饭不是什么人都能吃的,你得有相关部门的营业执照,执照限额,这塑料皮本子就比黄金还贵,转一下手就是上百万。这世道有钱的人多,你买吸沙泵,置打沙船,出手就得二三百万。你再花百万大洋买到了营业执照,但管事的部门未必会让你过户,你走通了红道,还有黑道,有钱不等于就能在长江里充大爷。长江里的大爷很多,一段江面就有一个大爷,有的还不止一个大爷,人家是时刻准备着豁出身家性命的。
能让岸上江上的各路大爷都敬你让你,这样的人不多,白脸算是一个。
拴钱认准了在白脸这里装沙,原因有很多,最简单的一条,白脸能一年四季不停吸沙泵,水警一封江,其他的打沙船都哑了,白脸的马达叫得更欢。装沙的船只排出几里路,白脸的手下拿着记录本,不是老客户都得响机器走船,你哭着喊着求都没用,白脸说这世上做什么事都有规矩,守规矩就是讲道义。
白脸的黄沙是比别人贵,但白脸能保障供给,沙子也永远比别人的好,饱满,金黄,堆在船舱像是金黄的稻谷堆在粮仓。白脸的手下开着小艇四处转悠,人家不是揽生意,人家不需要揽生意,他们发现了谁家的打沙船打出了好沙子,他们的打沙船就会径直开过去。识相的赶紧移船别处,不识相的隔天就会机器出故障,甚至操作手失踪。白脸会亲自上船,扔上几捆百元大钞,叫你赶紧修机器,机器一响,黄金万两,停一天就是几十万呢;或者表示对失踪者的深切同情,人心都是肉长的,每个江上混生活的背后都有一家老小指望着。不是不讲道理,讲的不是岸上的道理,在水上只讲水上的道理。
三宝不是不明白拴钱的心思,可是三宝眼窝子浅,舍不下眼前能省下的五千块沙钱。拴钱担心的不是三宝的脑筋不够用,而是担心一个男人眼界不宽广,容易被绊得鼻青眼肿,老话说,行船眼观十里水哩。
到了荆州段江面,白脸的打沙船在拴钱的望远镜里越来越清晰,船楼上挂着一面金黄的旗帜,旗帜的中间是一个大大的“4”字,这是白脸的第四条打沙船。边上泊着两条空船等着装沙,尽管吨位不大,但是因为货舱空着,船体浮在江面,像是两幢高大的楼房耸立着。相比之下,打沙船就显得像是高楼下的窝棚,只是那根输沙管直冲云天,居高临下地让人不敢小瞧。
一阵喜庆的锣鼓声在嘈杂的马达声中跃然而出,接着欢呼声向拴钱的船头袭来,“欢迎欢迎,欢迎拴钱老大来装金沙!”拴钱和根水都开心地笑了,这是打沙船的大喇叭里播出的,这样的待遇只有几个在长江里名声响的船队老大才能享受。拴钱嘴上不说,心里受用,他按响一长一短两声汽笛致意,驾驶着气势雄浑的钢船缓缓靠过去。
下了锚,三宝的船也靠了过来,拴钱放了软梯,根水挤过来,拴钱说你去凑什么热闹!根水说,我去替我爹娘为龙王爷上香。
拴钱无语,三宝先下了软梯,说快走快走吧,衬衫的口袋里塞了鼓鼓的钞票,他让这点钱烧得慌。拴钱白了一眼三宝,让根水也下了软梯上小艇。
2.郑守志喜欢这种火辣辣的天空,太阳一出来,就像一只大灯泡吊在你眼前,热,却无风。对一个在长江里谋稻粱的人,不喜欢风,永远不喜欢。有风就有浪,有雨就有险。这与农民不同,天涝的季节,农民盼太阳,盼天晴。天旱的时候,农民盼雨水,盼天阴。在这一点上,船民目标单一,坚定不移。郑守志不是船民,若干年以前他可以说是长江里的一个水手,但现在不是了,是江口集团的老总。江口集团吃的是长江里的饭,发的是江水里的财,所以他讨厌风风雨雨,每天看天气预报,看到电视上那个小太阳卧在云絮里,在他眼里就是金元宝躺在银锭上。其实也不单是郑守志如此,哪怕你只做过一天船工,你也会养成睁开眼皮就看天的习惯。
郑守志的办公室在江口村招待所的顶层,据说城里人买房,层数越高价格越贵,但到了顶层价格就会滑坡,冬天最冷,夏天最热,有空调也费电费。郑守志喜欢顶层,倒不是他有钱不担心付电费,他觉得该冷就得冷,该热就得热,人活着就得有冷有热。更主要的是,你住顶层,就永远把别人踩在脚底下,这感觉很重要,倘若你不在顶层,就只能听任别人在你头顶上吃喝拉撒。他是个敏感的人,考虑问题总比别人想得深看得远。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