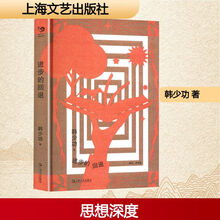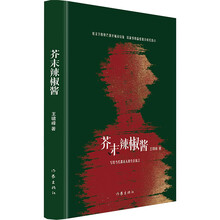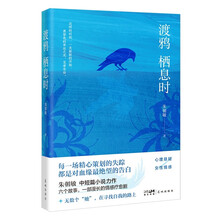田文林懒散地坐在圈椅里,一身青灰色的绸缎长袍,干净利落,刚剃了头,很是精神,面颊清瘦但肤色滋润,细长的眼睛含着善意透着精明。他一只手轻抚着圈椅向外翻卷的圆头扶手,用每一道掌纹体验、琢磨着红木的圆润。或许是抚得时间长了,倒不知是手心柔润了红木,还是红木沁润了手心,圆头扶手泛着细腻的光泽,似是有了体温。田文林的心里感到一种久违了的祥和与舒适。另一只手端着沉甸甸的茶盏,金骏眉清爽纯正的香气幽然而来,这是他的最爱。这最爱,与其说是这盏中的茶,不如说是这盛茶的盏。这是只宋代建盏,建盏历来是品茗上茶的至尊茶具,口大底小,很是敞亮,显得包容和大气;颜色褐中蕴黑,手感沉稳厚重,衬出饱满和自信。厚重,是田文林喜欢它的重要原因,这分量让人觉得心中特别有底。在这茶盏里当然须用小井冷泉急火烧沸,冲之以武夷山上等金骏眉才相衬。细细品着,先是舌津口润,然后便是身心体验着凝重和清爽了。
田文林脱口念出两句诗:
轻涛松下烹溪月,
含露梅边煮岭云。
这是陆廷灿的《武夷茶》。听松涛层层涌来,看露映点点梅花,烹溪下之月,煮岭上白云,这是怎样的魄力和境界啊!田文林玩味着、体验着,竟渐渐地觉得自己的心胸也宽了许多。
晌午的阳光无遮拦地穿过窗格,掠过原木色核桃木的九格钱柜,落在深栗色紫檀木的八宝柜上,柜子上精致的描金反射着光泽,原本隐约的牡丹花纹不露声色地显现出来。错落的光影让屋内更显出了层次。这房间里的大小物件,有的是田文林祖上传下来的,有的是他相中了从天南地北运回来的,还有的是他请了工匠精心设计制作的,那可是件件有故事,款款有讲究。袅袅水汽在光柱中聚散游荡,田文林的目光渐渐从盏口漂浮的一叶茶移散了开来。
前几日有消息传来,从湖北购得的川字牌砖茶已在新店码头顺利装船,经长江运至汉口,由陆路往北。一路波折,虽有几股强盗骚扰,但凭着田家的声望、玉轩的机敏和赵向义的威名,一路走来,还算顺利,只破费些酒钱,眼下已到了太原府。想到这些,田文林的嘴角不由地往上提了提,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笑容。
田文林放下茶盏,长长地舒了口气,身子向后靠了靠。从南方贩茶至北方,从北方贩马至中原,是田家祖上就做的生意。砖茶是北方草原牧区生活之必需,应急时还可充当货币,有一块砖茶一块银之说。贩马主要是为朝廷军用,多用作战马。最让他得意的是,田家曾多次为僧格林沁的骑兵补充战马。他欣赏这位横刀立马的英雄,做这生意让他觉得自己身上也多了些英雄气概,更何况还挣足了银子,在朝廷中还有了好名声。
田文林瞅准了商机,加上精明的头脑和良好的信誉,几年间田家在山西忻州一带已是声名鹊起,很是响当。忻州县令自然也就成了田家的常客,当然,每次来访都是满载而归。田家也乐得其所,一方面结交官府,茶引等自不必说,另一方面捐银助事,也为大清出点力,心中实也有所慰藉。
中断多年的茶路重新畅通,说明南方战事趋缓,天军的残余势力渐无踪迹。这几年的战乱搅和得田文林不能顺当地做生意,不但没赚到多少银子,还常有意外损失。他审时度势,减少了长线的生意,靠着多年的积蓄和信誉开了间票号。无奈世道不好,大家生意都难做,票号也只得些微利,也就维持田家老小的生活不受制。重新联络好这趟生意,终于让田家看到可以重新振作起来的一缕阳光。更让田文林看重的是,这是玉轩第一次南行做生意。他本该亲自出马,带带这孩子,奈何这腿上的风湿犯得厉害,走起路来膝盖疼得钻心,只好派温掌柜和赵向义陪着玉轩走,一个在生意上能帮衬玉轩,一个是贴心的保镖。儿子大了,也该历练历练,田文林宽慰自己。话虽这么说,他人在家,心却一直跟在路上,每日里盼着南边的消息,惦记着生意,更惦记儿子。眼瞅着儿子快到家门,他稍稍心安,但什么事不到最后又怎能说成败,他要沉得住。
南方局势稍有平息,这北方可是另一番景象。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