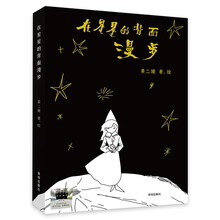《暴暴!快跑!》:
一座墓碑的变迁——纪念马骅君马骅不是那个跳健美操的马华。
他是复旦的学士,北大的硕士,本来将成为马骅博士,如果他可以带着他在雪山脚下写就的诗篇与关于藏族文化的论文回归城市的话。
但是他不能再回来。因为他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在云南梅里雪山脚下明永村的小学教书,坚持要送那一届小学生直到毕业考试完毕,某天的交通意外将他葬在雨季的澜沧江里。
他是我敬爱的同事,兄长,圣徒。
是他的离去让我终于鼓起勇气离开。
于是,从2004年起迄今,几乎每年我都会去一趟明永村,看看那座象征他的白塔。
第一次去的时候,小县城里拉着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向马骅同志学习”。明永村的两户人家主动平了两家玉米地交界处的一块地,大伙儿凑钱为他修建了一座白塔。男女老少都知道他,人们说,噢,那个老师,人好的很,可惜了,可惜了。在距离村子不远处的江边峭壁上,还挂着招魂的经幡,藏人觉得他只是潜藏在江底。白塔前后都是宽阔的玉米地,正对着奔腾的江水。
那时候,他私人寻觅的旅途,不知怎的后来被叫做“志愿者”,成了大城市里共青团的宣传模范。我知道,他只是在另一友人的帮助下,觅得那里,停留下去,自省而清静,并非“支边”的“志愿者”。
大概因为他是诗人,而且是中国最早的自助游书籍藏羚羊系列的编者,他的意外去世在文人圈子引起不小的震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里,北大举办了一个关于他的纪念会,和马骅情同父子的萧颂兄弟,一个混不吝小子、诗人萧开愚的儿子,和马骅另外一位朋友扭打起来。我被紧急传唤,在距离北大三角地不远的路口,举着伞接走了情绪激动的萧颂。
我一手撑伞,一手搂着他抽动的肩膀,他哽咽的脸庞在忽明忽暗的雨中悲伤而绝望。
多年以后,萧颂还是一个混小子,在全国四处游走,写作,时而穷得叮当响,时而意气风发钱咬手的请所有人吃饭。跟他打架的那位老哥秦晓宇,则是成功的广告商人兼诗人,他就像磨铁文化的老板沈浩波,书商起家,亏得一塌糊涂后却因春树残酷青春的畅销而被拯救,也会掏钱赞助纯文学一样。
老哥秦晓宇赚钱了也不再工作,在京郊租了个小院子潜心研究诗歌。有次在饭局上遇见他,他对于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深论吓我一跳,真心是爱诗爱写。散场好久打不着车,待我就地念咒“嗡达列都达列都列梭哈,,后,出租车翩然而至,他也吓一跳,愣了半天。
当年马骅最后一次回到北京,住在老友许秋汉的家中。那大下午,是他广而告之的分享会,他准备了很多诗歌、照片和故事,以飨朋友。我拎着一只鸡兴高采烈地赴约,心想,定有好菜好酒好多朋友。
开门的正是瘦了三圈的马骅,穿着最老式的带着三道白条的蓝色运动衣裤,上衣还扎在裤腰里。他见到我大吃一惊,房间里并没有我想象中济济一堂的热闹,马骅眯缝着眼讪讪地笑说,大家都有事儿,已经取消了哈,取消了。
那个落寞的下午,就只有俺两人,翻看有的没的相片,马骅的讲解意兴阑珊,我恨不得自己是孙悟空,拔根毫毛变出一百个朋友。
虽然我还是不敢遑论,为何萧颂非要跟秦晓宇打架。可显而易见,马骅让很多敏感的心都受到了震动,哪怕事情的继续,总是那么难以预料。
后来,那座白塔越来越斑驳,每次去,我总会耐心地换上一圈簇新的风马旗,在塔边撒上一瓶上好的青稞酒。
再后来,马骅住过的小屋、修过的小院被拆了,一座由上海资助的希望小学拔地而起,成为村里最巨大的建筑,完全挡住了白塔正对的澜沧江,我暗暗替他有些不高兴,村里的孩子完全不够填满如此巨大的一座教学楼,所谓的阅览室的桌子上晾着新收的玉米以防被猪偷吃。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