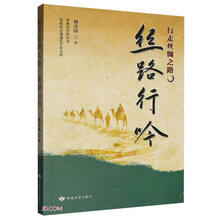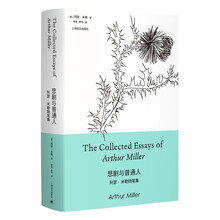第一章
1.“性”就是“命”
老了吗?
不。
端木林相信,只要还能和女人做爱就不算老。
端木林的实际年龄逼近六十岁,但始终是“逼近”。婚前他打通关节偷改了身份证,于是,好几年了,他缱绻“天命”、徘徊“耳顺”,跟岁月兜圈子打转转,踯躅不前。潜意识里他对六十岁畏之如虎,仿佛那是一道悬崖峭壁,越过去就会粉身碎骨、万劫不复。他强烈地感觉到,年龄对女人是大忌,对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通常而言,女人三四十岁的时候最怕老,跨过五十岁门槛也就死心塌地、灰心绝念地认老了。女人对老的恐惧体现于外表,容颜凋衰、回天无力,“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以后,她们的心也随之安宁,无奈地接受波澜不惊的沉静,“空留缱绻,闲说风流”。她们清楚地明白:大势已去、败局已定,拼足全力也打拼不过年轻貌美的女孩子,不管多么心不甘情不愿,还是拱手把男人的世界让出去,任由嫣红姹紫的女孩们去驰骋占领。男人对老的恐惧则深藏于骨子里。女人服老,男人不服老,男人愈老,追逐女人的欲望愈强烈。女人过了五十岁再闹绯闻就是笑话,男人即使过了八十岁,闹了绯闻也还是英雄,而且愈老愈英雄。女人用化妆品抵御衰老,男人靠女人抗拒死亡,女人是老男人最有效的“强心剂”,年岁愈大的男人,愈喜欢追逐年轻的女性。毛头小子可能喜欢中年妇女,耄耋老翁却最迷恋十八岁的小姑娘,他们拿小姑娘抵御对死亡的恐惧。老男人和小姑娘相恋,如同枯树逢春、杠上开花,自有一种奇诡之美,使生命呈现罕见的艳绝,如同寒梅吐蕊、红灯映雪。
端木林第二次离婚后身边极少有固定女人。年逼花甲,对异性不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他又看不上中年妇女们,他要的是能够激发生命活力的妩媚妖娆之女性。走近他的漂亮女人倒也不少,但她们醉翁之意不在酒,个个都是手持钓竿的垂钓者,比他这个老渔翁还要“江湖”,他只能小心翼翼、按兵不动: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
偶尔,端木林也想去欢场寻找风尘女子寻乐。欢场女子有百弊却有一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货银两讫、方便快捷。无奈他患有顽固的心理洁癖,作为画家,他嗜好在床上像欣赏艺术品那样,细细地咂摸和感觉女人,并带着艺术家的眼光玩味女性特有之美。欢场小姐们不管怎般艳丽,都如同开在涝池里的屎壳郎花,与“美”不搭界。屎壳郎花他小时候见过,艳红如血地开在乡下涝池里,远远地看去就像燃烧的火焰,俏丽而又打眼,但花蕊深处弥散出的腐烂气息令人掩鼻,看得碰不得。看到欢场小姐,他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鬼魅的屎壳郎花,怎么都克服不了巨大的心理障碍,心理障碍又会导致身体的障碍。他认定,身体死机不举,就预示着死亡的莅临。对他而言,所谓“性交”就是用女人的存在证明自己的存在,女人的身体就是男人的战场,而男人的最大成就就是驰骋疆场、斩获辉煌,如同俗话所说,女人活一张脸,男人活一杆枪。对老之将至的端木林而言,“性”就是“命”,“命”就是“性”,两相钳合才能叫作“性命”,失性就等于丧命,延命只能依靠“壮性”。年岁愈老他愈看重“性”的能量发掘。不愿也不能沾染“小姐”,又没有固定情人,端木林身边就成了女人的真空地带。“性”的生理问题倒在其次,他需要的是女人带来的精神之氧和源自血液深处的生命本能,渴望女人对他而言不是好色,而是抵制衰老、热爱生命。他很清楚:这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分阴阳两极,大到天地乾坤,小至花草虫鱼,阴阳交融则盛、阴阳失衡则衰,这是天经地义的自然律法:“阴阳交合,天地气开”,“合气通天地,心智贯开辟”。身边长期缺乏身心交融的女人,男人就会以惊人的速率不可遏制地走向衰萎,性器官也会迅速钝化:“枪头”都是愈磨愈光,不磨则荒,长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就会驽钝生锈、凋残朽废。
端木林常常想到一则逸事:他的老友从部队带回一只退役的狼犬。这狼犬是朋友的至交,曾如猎豹般智勇双全、所向披靡。然而,退役后由于饱食终日、无所事事,那老犬形容枯槁。眼见得自己的爱犬就要无可救药地走向死亡,朋友心急如焚,什么招数都使了,仍无济于事。后来,一名经验丰富的兽医出了个主意,每天在附近放飞雄鹰来激发狼犬的斗志。这一招果然见效:只要雄鹰出现,狼犬就会双目炯炯、咻咻狂吠,进入紧张兴奋的作战状态,与雄鹰斗智斗勇、腾挪斡旋,没多久就激情焕发、精神抖擞,如先前那般威猛无敌了。端木林认为,自己需要的就是一个像雄鹰那样充满生命活力、能够激发自己能量的女人,也始终在等待这样一个女人出现。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为是个大画家的缘故,他的眼光过于刁钻挑剔,别的男人看来十分出色的女人,都入不了他的法眼,他下意识里把女人“艺术化”了,这是艺术家们的通病,而艺术化就等于妖魔化。用艺术家的眼光来打量,绝大部分女人都脱不了一个俗字,于是就造成了十分悖谬的局面:他规避女人们的俗,女人则讨嫌他的老。“老”对他来说成了致命的硬伤:冷铁难打、老竹难弯,人老无能、神老无灵,他也只能像姜老太公那样,徒然地“独钓寒江雪”了。
就在端木林等得绝望的时候,张笑雪这个小林妖出现了,她青春得就像挂在枝头的荔枝果,美丽如同魅人至惑的荼縻花,俏俊娇嫩、卓尔不群,十足就是一只凌空展翅的小猎鹰。把这个超凡卓异的小尤物娶到手以后,端木林喜欢疯了,恨不得把她咬烂嚼碎,连骨头带渣地吞进肚子里去。他也不知道自己哪儿来那么大的能量,夜夜春宵不虚度,仿佛要把以前的亏缺全都弥补回来似的。潜意识里,他也在用这种奢靡无度的方式向他的小新娘、更向他自己证明:自己非但十分“行”,而且非常“棒”!得知他娶了个娇嫩得如同水蜜桃的小姑娘时,老友们话里话外都在表达同一种疑惑:“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那讽刺的眼神如同带毒的钢针狠狠地刺激着他的自信。怀着受伤的逆反心理,他那般喜欢自己的小新娘,却又不肯怜香惜玉,每一次在床上做爱,他都恶狠狠咬牙切齿,像在玩命般,恨不得生吞活剥了怀里的小女人。起初张笑雪不理解他何以如此,像个粗鲁贪馋的“暴殄者”,慢慢地才明白,他是在努力地证明自己,唯恐笑雪嫌弃他因衰老而不够生猛。殊不知,这证明背后隐藏着的,却是更深层的恐惧:恐惧衰老,恐惧死亡。笑雪终于明白,为什么男人总是愈老愈变本加厉地荒唐,原来,表面上他们在贪恋女色,实则在逃避抗拒衰老与死亡。女人的衰老呈阴性隐匿状,可以模糊和掩饰,拿化妆品和花花绿绿的衣服就可以遮羞,男人的衰老不折不扣、无遮无挡,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一张小小的床就会把他们逼到无可转圜的死角。床是他们的战场,亦是他们最终的滑铁卢,没有哪个男人能够打败小小的一张床。然而,他们天真而又可怜地相信,只要还能和女人做爱,死神就不会近身,他们就能挣脱自然的律令逍遥于上帝的“法规”之外,长命百岁、雄风永存,女人是他们逃避死亡的挡箭牌,而性则是他们砥砺生命的磨刀石。
把张笑雪这个俏娇妻娶回家的那刻起,端木林就开始担惊受怕、如履薄冰。他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妻子,这鲜嫩得如同荔枝果般的小娇女迟早会落入他人的怀抱,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山中自有千年树,世上难逢百岁人。”明摆着,张笑雪鲜花着锦、生机无限,如同三月小阳春,井深绳正长呢,自己却如同深秋之寒蝉,迸出全身的气力也鸣叫不了几日了,就算能活到八十岁,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妻子才刚刚接近不惑,正是女人的生命之花绽放到最浓最艳的时候,如同酿到至醇之境的茅台酒,色香味俱佳,且劲道十足。然而,上天注定,这坛自己亲手酿就的佳肴甘霖却要由别个男人来坐享其成。他爷爷和父亲都没有活到八十岁,他们的家族不具备长寿基因,现如今这个年月,想让年轻女子为死去的丈夫守节至终老,等于天方夜谭。他是,而且仅仅是妻子生命长河中一个匆匆的过客,他必须拼命地攫取和占有,恨不得每一次做爱都汲干妻子的骨髓、榨尽她的汁液,想把她压榨成空空如也的干果壳子。
娶了张笑雪以后端木林才意识到:自己真真是老了。就像俗话说的那样:有牙时没有花生仁儿,有花生仁儿的时候没牙了。夜里在床上折腾一次,他需得整整一个白天才能恢复元气。最糟糕的是,他失去了连续作战的能量。年轻的时候,他创下的最高纪录是一个夜晚冲锋六次,每一次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生命的弹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炸药”刚刚排空,立刻又“秣马厉兵、粮草充盈”,力量之泉滔滔无绝、源源不断,连续冲锋陷阵多个回合,只需休息短短几个小时,第二天依然精神抖擞、耀武扬威。现在不行了,养精蓄锐地攒足了气力,一个夜晚也只能冲锋一次,这仅有的一次还把自己累得如同烂泥。仿佛眼睁睁地看着满汉全席,却只能享用几片青菜叶子,拼尽全力也吃不动了。就像女人们关注化妆品一样,他留心起保健补品来,“女人老在脸、男人老在肾”,此话不假。不过,他无比痛心地发现了一个常识:无论怎般恶补,都达不到年轻的火候了,勇猛有余、元气不足,这已是铁定的事实。很显然,无论多么天下无敌的男人,最终都要被时间打垮。端木林发现,潜意识里,他把张笑雪当成了时间的化身。仿佛是,只要征服了张笑雪,他就打败了时间。与其说他是在和张笑雪做爱,不如说他是在和时间这只恶虎进行最后的负隅顽抗和殊死搏斗。他痛心疾首地体味到,上帝的最大残忍体现在时间上,最大公平也体现在时间上。一个人可以通过努力攫取到比别人更多的财富、权势和荣耀,唯独无法攫取到更多的时间。时间对每一个人都是定量的。然而,正因为如此,端木林认为,多占有女人多做爱,就是多攫取时间,也是从上帝手里多讨取到一些岁月和生命。
死亡和衰老多么的顽固不可抗,占有和攫取的欲望就有多么的强烈。端木林不肯对时间服输,他要找到别一种武器来永久占有张笑雪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青春、生命和美本身。天助自助者,最后,他找到了一件最强有力的武器:画笔。身体部件虽已衰弱,但他手中的画笔还很硬朗。他开始手握画笔,不厌其烦地反复描画妻子张笑雪。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正面的、背面的、侧面的,这一幅刚刚完成,马上又开始下一幅。多画一幅,他就觉得多攫取了一分。他白天在画布上描画妻子,夜里则在床上吞食妻子,这样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在妻子的胴体上耕耘,端木林才觉得够本。仿佛是,只要把妻子闲置起来,自己就吃了大亏。
然而,端木林绝望地感觉到,自己越深入和逼近妻子,妻子距离他越遥远。在他和张笑雪做爱的时候,张笑雪参与的仅仅只是身体,她的灵魂像捉摸不定的小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置身事外地栖息在别处,眼睁睁甚至幸灾乐祸地看着他独自徒劳地拼命折腾,这从她的眼神里暴露无遗。以端木林既往的经验判断:和男人做爱时,绝大部分女人都闭着眼睛。闭着眼睛的女人给他如痴如醉的感觉,那感觉是全身心地投入和沉溺。仿佛是,只有闭上眼睛把外部的物质世界干干净净地屏蔽掉,才能专注于灵魂的感受,也才能让灵魂展翅高飞、翱翔长空。所谓做爱,难道不是让灵魂挣脱羁绊、打碎枷锁,凌空而起、脱壳出窍,翼翼生风、气贯长虹地飞至云端吗?端木林也不知道自己和多少个女人做过爱了。活到这般年岁,阅历过无数女人他才体味到:所谓做爱,实质上就是肉体对灵魂的剥离和穿越。人的肉体如同一座牢房,灵魂则被死死地囚禁在里面,做爱就是:拿锤子去不顾一切地敲碎和打破那森严壁垒的“牢房”,把灵魂从肉体的束缚桎梏中剥离出来,让灵魂且歌且舞、热辣酣畅地引吭鸣唱、展翅翱翔。许多时候他觉得,人的灵魂就像高贵的天鹅,这天鹅被死死地囚禁在肉体的“蛋壳”里,所谓做爱就是,男女双方配合默契、齐心协力,采用一切办法和措施,不顾章法、不讲节律和不择手段地,手足并用、唇齿合力,无所不尽其极地把全身的能量众志成城地调动激发起来,攻城略地、冲锋陷阵,相互撞裂和破碎那肉体的“蛋壳”,让两只天鹅呱呱鸣叫着飞向自由自在的无极之境。
端木林曾经创作过一组题曰《做爱》的作品。第一幅画面上呈现的是两只静卧草地的浑圆坚硬的天鹅蛋。那两枚天鹅蛋以静制动、蓄势待发,象征做爱男女双方的肉体之城堡。这是做爱的序曲:彼此合作,默契而又成功地预备把对方的城堡攻下,从而把对方也把自己从围困中解救和放飞出来。身体有局限、灵魂无疆域,无限的灵魂试图挣脱有限的身体桎梏,这是人必须面对的悖谬和困境。正因了这困境的存在,男女双方才要联手作战,通过解救对方来超度自己,这“交战”就是做爱。做爱的双方既是对峙的敌手,又是合作的伙伴,就像是冰与火的遭遇、雷和电的激发,天与地的共鸣、阴和阳的融汇。
第二幅:山雨欲来、风满竹楼。被围困的灵魂蠢蠢欲动、跃跃欲试,它们在密闭的肉体蛋壳里大声地号叫着:我要活,我要飞!我要飞翔啊,我要活!我要飞越高山、飞越海洋,向着云端的最深处冲锋,去寻找我的故乡。向我撞击吧,以最勇猛的力量撞击我,让肉体碎裂、让屏障解除,让我翱翔让我飞!在飞的力量感召下,两只静卧的天鹅蛋开始相互惨烈悲壮地撞击,就像子宫里的胎儿拼尽全力冲向这个世界一样。
在端木林的感觉里,做爱的过程和胎儿诞生惊人的相似。不同的只是,女人生产诞出的是个肉体的生命,而做爱诞生的是灵魂的天鹅。事实上,男女双方做爱的主要动作也就是撞击。这种撞击代表着进攻和占领的搏杀,就像拿机枪去扫射、拿大炮去轰炸,或者拿刺刀直截了当地搏击,要么干脆把身体当坦克去攻城略地、倾覆碾轧。做爱的动作无论怎般千变万化、花样翻新,本质上都是击打和碰撞的变体。那击打的对象表面是肉体,实质上绝不仅仅局限于肉体。那时那刻,肉体乃是一切羁绊、围困、阻碍、压迫和桎梏的象征,灵魂如同蓝色的精灵,必须能够披荆斩棘地冲出重围,才能石破天惊地脱壳而出、傲然凌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端木林认为,人终其一生都在为灵魂的解放而战斗和反抗。灵魂的力量太无限太可怕了,上帝深知这一点,于是,他煞费苦心地把灵魂挤逼在有限的肉体“壳子”内,使肉体成为潘多拉魔盒,死死地钳制和桎梏着灵魂之魔。灵魂怎么可能甘于束手就擒?从出生那一刻起,灵魂就在培育和凝聚自己的“力比多能量”,那能量以生命的本源方式潜滋暗长、蓄势待发,如同地下被镇压的火山熔岩,一俟时机成熟,立刻锐不可当地燎原破竹、冲决而出,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做爱。做爱不是肉体的交合,而是灵魂的燃烧。这燃烧噼啪作响、可歌可泣,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
第三幅:在惨烈勇猛的相互撞击之下,蛋壳绽开裂缝,灵魂的天鹅从蛋壳缝隙里挣扎着探出脑袋,初生婴儿般惊喜地望着这个世界,但其翅膀和身子还在石头般坚硬的壳皮里面束缚着。天鹅的脑袋拼命摆动,绷足全力想要挣脱锁链般的桎梏,就像胎儿竭尽全力穿越产道、冲出母亲的子宫那样,那“胎儿”就代表着做爱男女双方的灵魂之生命,那“生命”凝聚着男精女血、天地精华。
第四幅:交战的双方进入白热化阶段,男女厮打在一起不分彼此、不讲章法。“鼓角声声连天起,呜嘤鸣镝已离弦。时到关节何惜身,奋起旌旗去杀敌。”晨曦初现、霞光万道,胜利的号角在耳畔奏鸣,最后的火拼即将打响,刀光剑影、战旗猎猎,蛋壳彻底碎裂,两只天鹅凌空而起,穿云破雾、飞越长空。
第五幅: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空。邈远无际的天空中两只天鹅翩翩起舞、且蹈且歌,用血液、用生命、用全部的热爱和激情对歌唱和、鸣嘶呐喊,来欢庆生命、欢庆爱情、欢庆自由、欢庆飞翔。
在端木林看来,高品质的做爱就是两个灵魂的和鸣二重唱,那是一种高难度的美声唱法:什么时候用什么声部,什么时候需要舒缓的铺叙,什么时候又需要高亢和激昂,那声情并茂、幽微婉转的呼唤应答极有讲究,那是心与心的默契、情与情的呼应,灵与灵的对歌、魂与魂的旋舞,是一曲回肠荡气、高贵典雅的男女美声二重唱。意大利文称美声唱法为“Belcanto”,中国在开始引进这种唱法时,把“Belcanto”翻译为“美声唱法”,其实“Belcanto”这个词在意大利语里的真正含义是“完美的歌唱”,其含义与“美声唱法”不尽一致。“完美的歌唱”不仅包括声音,还应该包括歌唱的内容及歌唱者的风度、仪表、气质,尤其是感情的内涵,而“美声唱法”很容易被顾名思义地理解为具有“美好声音”的唱法。把“完美的歌唱”理解为“美好的声音”非常褊狭,同样,把做爱理解为纯肉体和物质的交合也存在极大的偏颇。表面看上去做爱是肉体与肉体的搏击,而真正穿越的却是灵魂。如果做爱的双方有一方灵魂缺失,做爱这件事情都不可能真正圆满酣畅地进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而言,端木林发现,从理论上讲,也许任何一个男人和任何一个女人都可以进行肉体的交媾,而且都可能抵达生理的高潮,但,要真正灵肉合一地完成做爱这件事情,却是沙里淘金般极难遭遇,如同“千金易得,知己难求”那样,寻觅和遭遇一个能够彼此在灵魂上旗鼓相当、高度默契的做爱搭档绝非易事。很显然,他与自己的妻子张笑雪之间所进行的床上运动只能叫作“交媾”,而远远谈不上“做爱”。换句话说,自己从来不曾攻破过妻子那铜墙铁壁般的肉体之“蛋壳”,她灵魂的“天鹅”始终龟缩在自己的硬壳里,事不关己、心猿意马,这一事实在她的眼神里昭然若揭。
每一次和端木林上床时,张笑雪都大睁着两只眼睛,茫然无措地盯着天花板,那目光涣散冷漠、游弋不定,怎么都无法凝聚和专注。面对大睁着两只眼睛,漫不经心地躺在身下的张笑雪,端木林总是既恼羞成怒又充满挫败的羞辱,就像那则日本俳句描写的那样:“厨房炉灶上,开水自沸腾,无人理睬好伤悲。”每一次跟笑雪做爱,端木林脑海里都会浮现这则俳句。这俳句看似平常,却悲哀和绝望到骨头缝隙里。他觉得,自己就是那独自沸腾的一壶开水,他这厢金戈铁马、锣鼓喧天,笑雪那里万马齐喑、按兵不动。于是,华贵的婚床上,便成了他一人的独角戏。端木林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婚床上的独角戏让人感觉更孤独更寂寞了,但他不唱却又不甘心。
有时候,他会突然恶狠狠又意味深长地直视着张笑雪的眼睛,仿佛要用锐利的目光洞穿她的心,使她无处躲藏。每逢此刻,张笑雪都会逃跑般死死地闭上眼睛,不敢去正视端木林那炯炯喷火的目光。不过,那闭上的眼睛里面没有沉醉和投入,而是无声的抗拒,如同一扇从里面上了锁的门,她的灵魂被死死地锁在那扇铜墙铁壁的门扉后面,那门上连半丝缝隙都没有,无论端木林怎么用力都无法打开。他可以把张笑雪的身体搂抱在怀里百般折腾,还可以把她的裸体描摹在画布上恣意玩味,唯独捕捉不住她那只灵魂的鸟儿。那只小鸟扑朔迷离、忽远忽近,令他捉摸不定、惴惴难安。他不去捕捉时,那只鸟栖落枝头、恬淡娴静,只要他伸出手来试图捕捉,甚至企图靠近半寸,那只鸟“咻”的一声就飞远了,永远躲着他、避着他,跟他玩着捉迷藏游戏,无论他怎么努力都不肯跟他亲近半寸。这使得端木林既无奈又绝望,甚至抓狂,于是,只好变本加厉地占有妻子的身体,仿佛要从她的身体里拼命敲击出她藏匿在骨髓最深处的那只灵魂之鸟,就像从果肉里挤压出果核来那样。他不知道,张笑雪在婚床上比他还要绝望和抓狂。
每一次躺进端木林的怀抱里时,张笑雪总是提醒自己:快乐吧、燃烧吧、飞翔吧,你是在和自己的老公做爱!然而,她的身体仿佛是一条结了冰的河,她越着急要融化,那条河越不肯解冻,更不要说惊涛拍岸地沸腾了。无论她在内心里怎么用想象来给自己鼓劲热身,她的血液都无法燃烧。端木林的身体就像沉重古旧的破骡车,不管服用什么灵丹妙药都不可能再轻灵曼妙地辗转腾挪,只能像笨拙的推土机那样,沉重地匍匐在她身上,使她感到像压着装满粮食的麻袋,既懊恼又索然,半丝半毫飞翔的感觉都没有。而对她来说,做爱就是灵魂出窍,就是翱翔长空,不能够振动双翼欢快地鸣叫和起飞,让自己的感觉脱离地面,怎么可能算是做爱呢?许多时候,她甚至忍无可忍地想要把那沉甸甸的“麻袋”不管不顾地掀翻到床下去才解恨。也是到了这时候她才晓得,做爱并不是身体的事情,而是灵魂的激荡。身体就像冰冷黑暗的房屋,而灵魂是那把房间烛照得金碧辉煌的“热”和“电”。灵魂不到场,身体无论如何都玩不转,就像油箱里没有油,汽车便发动不起来那样,她哪怕费尽心力,也无法把自己的灵魂召唤至婚床上来。端木林勤奋而又绝望地在她身上拼命折腾,而她却无动于衷、毫无感觉的时刻,她就会觉得,女人的身体就像是电源的插座,而男人的阳具恰恰就像充电器,女人的灵魂若是不来电,男人再怎么插也都是白费气力。她什么都可以做,唯独没办法让自己对端木林来电,这是老天爷也无奈的事情。
最要命的是:她总感到端木林的身体里有一种很难忍也很奇怪的气味。尽管她知道,端木林每次和她上床前都要认真沐浴,但她还是能够嗅到那种莫名其妙的气味。那气味说不清道不明,却挥之不去、欲盖弥彰,毒药样败坏了她的灵魂。后来,她慢慢明白,那是老年人所特有的气味,一种年深月久的朽腐之气息,就像百年老屋或废弃枯井里发出来的霉气一样,那气息像雾瘴弥漫在她的感觉神经里,使她无法燃烧、亦无法激情,于是,只好让自己的灵魂金蝉脱壳般逃逸在别处,又于是,夫妻两人的做爱就成了心照不宣的捉迷藏游戏,要么就是你死我活而又不动声色的鏖战和博弈。不过,对端木林来说,他博弈的对象不是妻子张笑雪,而是时间这只魔兽,这只魔兽别名叫作“老”。
2.裸
“瞿塘嘈嘈急如弦,洄流势逆将覆船。”因为老的缘故,端木林如同逆水行舟,穷冬急风水、逆浪开帆难,拼尽全力也无法抵达妻子张笑雪,到了此刻他才知道,张笑雪处心积虑地嫁给他这个老朽,仅只是为了报复儿子端木春阳。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这真相残酷到令端木林难以面对。面对这残酷的真相,端木林最初感到巨大的震惊、愤怒和羞辱,随之而来的便是不可遏制的失意、落寞和绝望。失落感像汹涌澎湃的潮水,先是漫过他的胸口,然后一寸一寸地淹没了他的头颅,覆盖了他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并吞啮了他的每一个细胞。被耍弄的屈辱倒在其次,对他打击最大的还是衰老这个坚硬的事实。
老了,老了,老了啊!
这是他愈来愈深切的感触,令他痛心疾首、万念俱灰。满脸青春痘的男孩和满脸老年斑的男人,本质上没有区别,尽管端木林挖空心思在衣着上装扮自己,穿大红的时髦上装,戴西部牛仔的骑士帽,从外表上把自己弄得像个火力四溢的小年轻,然而,他的头发几乎全部脱落,头上戴的是假发套,嘴里装的是烤瓷牙,再加上满脸的褶子和老人斑,再怎么武装都拯救不了衰老萎颓的残局。他从未想到过,自己的生命会如此地依附于一个可笑而又可怜的假发套。那假发套几乎成了他须臾不可离弃的救命法宝,不戴假发套,他就会觉得自己像鬼影子般难以出头露面,只要去见人,他必戴上假发套,那假发套仿佛他的隐身衣,他甚至自己都没有勇气面对不戴假发的自己。只要是不戴假发的时刻,即便是洗澡的时候,他也绝不让自己照镜子。在某些特殊场合偶尔无意间猝然看到不戴发套的自己,他会惊得魂飞魄散,他必须用假发套把那残酷的真实掩饰起来才有勇气面对这个世界。那假发套就是他的面具和隐身衣,他对它依赖到病态的程度,这极端的依赖又演化成了极端的排拒和抵制,他愈离不了“隐身衣”,愈想摆脱它,只要情况允许,他就迫不及待地立刻摘掉假发套,如同卸下千斤重担或该死的紧箍咒,以让自己得到片刻的喘息。
自从娶了张笑雪这个青嫩的俏娇妻,能够放心大胆地摘下假发套的机会就少之又少了,连晚上睡觉对端木林也成了极大的考验:若是摘下发套他担心自己的模样会吓坏妻子,并可能会影响妻子与自己做爱的兴致;如果二十四小时都不摘下,又如同戴着个魔咒,令他不堪重负。他只好采取折中的方案,凡是跟张笑雪在一起,哪怕夜里躺在床上也决不摘下假发套。当然,戴着假发套睡觉让他感觉百般不自在,既担心把发型弄坏,又担心睡着以后不小心蹭出光脑袋。夜间他会多次醒来下意识地伸手抚弄自己的假发,或习惯性地梦到假发套从头上脱落,然后惊出一身冷汗后醒来。尽管千般谨慎,那假发套也只能掩盖光秃秃的脑袋,掩盖不了他身上松弛的褶皱和老人斑。白天身穿冠冕堂皇的衣服还勉强可以遮挡些微的老态,到夜晚脱下衣服全裸呈现,那老态便原形毕露,怎么都掩不住了。做了张笑雪的新郎以后端木林才意识到,“老”原来竟是如此的丑陋和难堪,丑陋到令人羞耻。为了照顾张笑雪的视觉感受,他只要一踏进卧室就习惯性地关灯,卧室的窗帘也特意换成了最厚实的专用遮光布,并借口自己眼睛怯光,不允许轻易拉开窗帘,哪怕在大白天里,他和张笑雪的卧室也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他的衰老需要黑暗,只有隐身在浓稠的漆黑里,他才会找到稍许的安全感。不过,这种时时刻刻严防死守、高度戒备的状态,令他紧张的神经随时濒临崩溃的边缘,由逆反而产生的抗拒力也在时时升级加重。
端木林用的是最高档的假发,逼真轻便、透气性能良好,但如果二十四小时须臾不离地戴在头上,他仍然感到泰山压顶般不堪忍受。他也弄不清楚,那无以复加的压迫感究竟来自心理还是源于生理,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哪怕片刻的机会,迫不及待地脱下假发,让自己能够自在舒心地顺畅呼吸。如果超过一周以上的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使自己能够安全地解除假发的武装和戒备,端木林就不得不去宾馆开个豪华套间,痛痛快快地摘掉假发套,并脱去身上的层层包裹,让自己一丝不挂地全裸呈现,否则他就会感觉要被压扼致死。宾馆里那封闭的豪华套间对他来说仿佛就是天堂,或者是他最后的伊甸园,他在“天堂”里面想要享受的唯一特权只是放开羁绊,像亚当那样全裸:裸出自己寸草不生的光脑袋,裸出自己胯下那半截破绳头样丑陋萎缩的男性“阿物”,裸出眼中钉样的老人斑,裸出小腹部堆积的脂肪和肚腩,裸出皮肤上不可救药的松弛和褶皱。那被裸出的都是衰老的铁证,同时也是“谋杀”的铁证。他知道,自己正在被时光和岁月谋杀,那闪着凛凛寒光的刀具已架上自己的脖颈。当他在宾馆里让自己赤身裸体的时候,仿佛是,他在拿这些衰老的佐证警醒自己:抓紧享受人生之盛宴啊,再迟就来不及了,利剑高悬头上,死亡在劫难逃。有时他会在宾馆里待上二十四个小时,有时则是四十八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在这几十个小时里,他就那么自始至终赤裸着全身,喝酒、用餐、看书、接电话,甚至坐着发呆也裸着。他觉得,只有裸着的自己才是真实的,也是自由和舒展的,他不能持续忍受那种“伪饰”和“羁绊”的沉重。让自己脱去武装和戒备轻松度过几十个小时以后,他才能像手机充足了电能,或是囚徒放了一次风那样,兢兢业业地套上装模作样的假发,穿上冠冕堂皇的衣服,打上锁链般的领带,人模狗样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和妻子的卧室里。也只是老到这般境地他才知晓,原来“赤裸”居然是如此美好和不可多得的特权。能裸时他不想裸,裸不起的时候,他才感知到裸着的微妙和奢侈。
专门去宾馆开房“全裸呈现”从而让灵魂放风毕竟太过麻烦,只有迫不得已、窒息到忍无可忍的时候端木林才会那样做,通常情况下,他选择自己的画室作为光脑袋“局部放风”的地点。在画室里“放风”时不能“全裸呈现”,他所能做的只是摘掉假发,露出秃脑袋而已。这样的时刻,假发套对他而言,仿佛成了全部武装盔甲和扼制压迫的象征,摘掉它也就基本上相当于全裸。当身体尤其是脑袋处于全裸状态时,他的灵魂也才能舒展轻逸的翅膀,自由地翱翔。不过,这“局部裸呈”也有条件,当他独自一人待在画室里创作时,先把画室的门从里面扣死,再把窗帘拉下,然后才敢把假发暂时地摘除掉,好歹让自己解放片刻。只有摘掉假发,脱去西装革履,换上佣人桂嫂做的手工布鞋,让头颅自由地面对空灵,让双脚踏踏实实地接触地气,让灵魂处于欢快鸣唱的状态,他才能更深邃地进入沉醉忘我之意境,创造出传神之作。
画得忘情时,也会有疏忽出现。一次,端木林工作得太过投入和沉醉,忘了把画室的门扣死,张笑雪忽然推门而入,无意间看到了他的光脑袋,居然吓得傻在那里,如同撞见了妖魔。也难怪,自从和张笑雪认识以后,端木林时刻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光脑袋,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从未让自己在妻子面前曝过光。哪怕洗澡的时候,也要把假发戴进浴室里,端端正正挂在墙后,沐浴完毕,一丝不苟地穿戴整齐,他才让自己“隆重出场”。这是张笑雪头一次面对他的庐山真面目,不吓坏反倒怪了。看到张笑雪吃惊得目瞪口呆,他急急忙忙抓起头套就往脑袋上戴,慌乱之中居然把后面套到了前面,出尽了洋相丢尽了丑。看到端木林如此那般的慌乱,张笑雪躲鬼般逃出画室,一边回想着老公触目惊心的光脑袋,一边暗自思忖:头发这东西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和用场,只是简单的装饰而已,谁能料到,没有头发的端木林看上去竟是如此那般的骇人呢?简直令人毛骨悚然。自己居然是嫁了那样一个衰佬,并且夜夜伴着那衰佬入眠吗?张笑雪不敢细思量,竭力让自己忘掉那秃瓢般的光脑袋,然而,适得其反,她愈努力想要忘掉,那光脑袋愈灼灼夺目。她进而疑惑地想:小伙子的光脑袋看上去酷酷的,性感而又另类,为什么老男人的光脑袋看上去那般狰狞恐怖呢?
因为在妻子面前出了洋相的缘故,端木林的心境好多天没能恢复,遭受这件事情的打击,他感觉自己又老去许多岁。“老”是一切屈辱的根源,“老”亦是一切的罪魁祸首,他在心里千万遍地感叹着:“年轻好。年轻真好。年轻就是好啊。再也没有比年轻更好的了!”时光如果能够倒流,他宁愿拿自己的全部财富去换取一段青春嘉年华,哪怕做个街头流浪者,他亦心甘情愿。可是此刻,自己无可救药地--老了!因为老,他不再能博得女人的青睐,即使知道妻子不爱自己,拿自己当报复儿子的砝码和道具,他也必须心平气和地忍耐并接受,忍气吞声、听之任之。每当沮丧情绪飙袭而来的时刻,他就会鬼使神差地想到杜甫的那几句诗:“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他觉得自己活脱脱就是那只能“倚杖自叹息”的老者,被怒号之风卷走的“三重茅”,就是自己那曾经青葱繁茂,今世永远不可再生的头发。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