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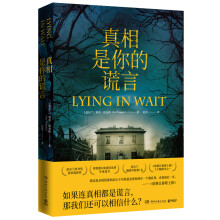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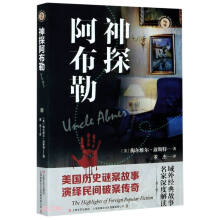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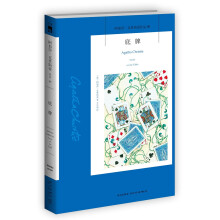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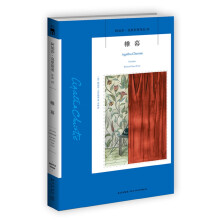


★ 诱惑力的元素
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比毒品更能蛊惑人心,这本书里充斥着大量充满诱惑力的元素:枪支、暴力、骚乱、犯罪、金钱……贴近生活,追本溯源。
★ 第一手资料zu后工厂,获取第一手资料。zui
这是一部关于可卡因前生今世的传奇,是对古柯种植和可卡因加工zui翔实的记载.从历史到人性,客观真实地描述了人类如何从世界的征服者变成被奴役者。
“它的香味近似于刚刚收割的稻草和巧克力混合起来的气味。”
听起来如此迷人的古柯,却可以引发战争、促成侵略,令政客蒙羞、让政府倒台,使监狱人满为患,造就亿万富翁,也夺去成千上万的生命。这一切只因为,它是地球上zui富含可卡因的植物。
在这本书里,大量的枪支、暴力、骚乱、犯罪、金钱,都与可卡因本身的魔力有关:
世界上第yi次反对服用麻醉品的战役是如何拉开的?
弗洛伊德如何在无意之中创造了世界上第yi个可卡因瘾君子?
仅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可卡因交易产生的现金如何渗透进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
可卡因又是如何染指那些富有的、引导时尚潮流的人,让它高昂的价格成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玻利维亚政府与可卡因贸易沆瀣一气,zui底层的古柯种植者有着怎样悲惨的生活境遇?
阻止可卡因的生产,就能解决哥伦比亚的暴力和贫困吗?
本书作者多米尼克•斯特里特费尔德,以惊人的胆识只身一人前往贫瘠、恶劣、血腥的蛮荒之地,与数名恶贯满盈的大毒枭深度接触,从而得到大量真实生动的第yi手资料,揭开古柯种植和可卡因加工的神秘面纱。
第6 章
春药?毒药?
19 世纪末受到可卡因引诱的医生,并不是只有弗洛伊德一个。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服用可卡因有上瘾的危险,它的销量还是直线上升。可卡因是当时唯一一种医用局部麻醉剂,各种新的应用方法一直在被不停地发明出来:1884 年威廉•霍尔斯特德完善了神经阻塞麻醉法;第二年,雷纳德•康宁发明了部位麻醉法;1892 年卡尔•路德维西•斯雷恩提出了通过皮下注射实施浸润麻醉的观点;1898 年奥古斯特•比尔发明了最危险的麻醉法:腰麻,即将可卡因直接注射到脊柱的椎管里去。
所有这些方法都很危险,有些极其危险。现在都很少用到,不过,要是你在牙医那儿打上一针麻药,就会对霍尔斯特德的神经阻塞麻醉法熟悉起来(今天,可卡因很大程度上已经由人工合成的麻醉剂替代,这种麻醉剂能达到同样的麻木效果,却不会产生快感)。
尽管可卡因的合法用途一直在增加,但真正赚钱的,还是那些药效平平的虚假治疗性专利药物。科勒发现局部麻醉剂后掀起了人们对可卡因的狂热,任何含有可卡因的东西都一定会有市场:不明就里的读者看到有关这种神奇的新药的报道后,就想让自己的药里也含有可卡因。《纽约时报》1885 年报道说,在其麻醉作用被发现后,可卡因名声大振,甚至“如果有人说自己牙疼得厉害,身边就会有人大叫‘抹点可卡因吧!’”。专卖这种骗人的药的商人注意到这一点之后,马上在他们的老配方里增加了可卡因,让这些药更加神通广大,还炮制出各种各样以可卡因为基础的产品来垄断新的市场。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古柯和可卡因药物的出现,他们不得不想出更加有力的推销方法。有秩序的推销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推销,没过多久,这些虚假产品的广告商就开始求助于一个能保证卖出任何商品的要素:性。他们用的这种方法也许是所有古柯神话中最古老的一个:可卡因能改善你的性生活。
古柯可以当春药的观点并不新鲜。印加人当然拿它当春药,有关它壮阳特性的报道在1794 年就打动了旧世界。当时唐•伊波里托•乌纳聂在他的航海日记里耸人听闻地报道说:“……这个嚼客已经是80 多岁的人了,却还能挥洒连正值壮年的年轻人都借以自傲的雄风。”正如1999 年“伟哥”在世界市场上畅销所证明的那样,任何能让人相信可以治疗性无能的药准保都能找到巨大的市场。再没有什么比期待能以某种方式改善自己性能力的药物更能驱动顾客往药房跑了。100 年以前也是这样。有些古柯药的推销策略更狡猾,例如古柯酒就宣称:“老年人会发现它具有足可信赖的壮阳作用。”就连可口可乐都开始采取行动,吹嘘说自己是“最棒的强壮剂”。
《英国医学杂志》以前也曾报道说古柯是春药,这一点上文中并没有提到。在美国,有关古柯在性能力方面的功效的报道也非常混乱。威廉•哈蒙德(William Hammond)哀叹说可卡因不能治疗手淫之类的病,即便是给只有四五岁的孩子用上10%的可卡因溶液也不行。美国医生维克多•维克在他于1901 年出版的课本上让人们注意到可卡因在治疗性无能方面的混乱,他指出“内服可卡因毫无例外地会在56 岁的老人身上产生性冲动……这刚好与美国海军方面H•威尔士博士的看法相反,因为威尔士博士声称他注意到可卡因有降低性欲的作用”。我们也许很幸运地看到,威尔士博士最终认识到,无论可卡因有什么样的功效,它都不会降低性欲——否则的话,美国海军也许现在还一面喝着加可卡因而不是加溴的茶,一面还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上航行着。
有关可卡因是否有壮阳作用的争论一直在继续。这也许没有什么好吃惊的,因为麻醉剂和性总是连在一起的:麻醉剂让你感觉好极了,性让你感觉好极了,这两者人们都只在特殊的场合才会纵情享用;二者都是儿童的禁忌。性让人快乐,麻醉剂让人快乐。即使不是人类学
家也能把二者联系起来。
然而,这种联系仅仅是道听途说,还是真有几分道理?有一种说法是,可卡因既然可以引起瞳孔扩大,那么就可以令使用者显得更加性感(瞳孔扩大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诱惑;19 世纪的维也纳女性在赴激情约会前常常把致命的茄属植物的汁液滴到眼睛里来扩大瞳孔。这种
植物因为能够以这种方式使女性更加迷人,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名字:颠茄,意为“美丽的女人”)。这种东西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但总比没有强。
尽管瘾君子同医生对可卡因是否有催情作用存在意见分歧,但是大家都同意,归根结底,要是服用的可卡因量过大的话,就一定会对性能力造成伤害。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化学上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不过从可卡因使用者的观点来看,最重要的原因只不过是对性本身失去兴趣。说简单点,可卡因能比性带来更多的快乐,尽管一开始使用可卡因是为了性,但最终渴求可卡因的强烈欲望会取代进行性行为的欲望。
对实验室动物进行的所有试验所得到的结果也是如此。给哺乳动物安装上仪器,可以让它们为自己弄到小剂量的可卡因,结果所有的动物都完全忽略了性行为,一心扑在可卡因上。重复过量使用可卡因,人类和动物最终都会变得性无能。
19 世纪末的人对这些都一无所知。可是他们知道可卡因能让人感觉好极了,似乎还能治疗许多其他药物都无能为力的疾病。大批的古柯和可卡因新产品开始出现在市场上。继古柯葡萄酒和补品之后,出现的是家庭常用的止痛剂:止咳滴剂、止咽喉疼的锭剂、止牙疼滴剂,所有这些利用的都是可卡因的麻醉作用。可卡因新药流行起来,药越新,就越能吸引前来购买的公众。接下来各个公司竞相提出各种奇特的使用可卡因的新方法。随着“古柯宝拉”(“一种用于咀嚼的膏体,能够强效滋补肌肉和神经系统,减轻精神疲劳和体力不支,为使用者补充额外的脑力和体力,没有任何不好的后效”)的到来,咀嚼可卡因也成为可能。早在1885 年,派德制药公司在给古柯香烟做广告时就保证说他们的产品可以缓解咽喉痛,减轻精神抑郁——这也是可卡因文学中第一次提到人们可以吸食这种药。他们还在散发给美国医生的广告单上引用了《治疗学学报》一位通讯员的经历:
在自己身上做实验的时候,他感觉有点精神沮丧——换句话说,有些忧郁,因为家人不在身边,家里空荡荡的。饭后,他吸了几支这种香烟,“忧郁”的感觉马上烟消云散……
该学报接着提到他们的古柯产品成功地治疗了消化不良、胃气胀、疝气、胃痛、肠痛、歇斯底里症、臆想症、脊柱痛、原发性痉挛、神经异常兴奋、严重的急性感染造成的肢体无力等。尽管这里面几乎
没有什么实话,但派德制药公司提出吸食可卡因的想法的确是个非常好的主意——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主意。但是,出于我们后面要谈到的原因,吸食可卡因的习惯在这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还是不太流行。专利药制造商开始炮制复杂的以可卡因为主要成分的药物,然而不久他们就意识到根本没必要用古柯叶子。简单得多的办法,就是直接把一定量的可卡因倒进产品里。值得指出的是,治疗鼻窦和黏膜问题的药物里的可卡因含量特别高。把可卡因当作治疗呼吸系统问题的灵丹妙药来卖,这简直就是天才的想法:正如弗洛伊德发现的那样,可卡因能很快(但只是暂时地)令鼻窦干燥并打开呼吸通道,似乎是治疗过敏症和鼻塞的理想药物。骗人的江湖假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大做广告说自己能治疗从哮喘和花粉症到流感,从咳嗽和感冒到一般的呼吸不畅甚至打鼾的各种病症。塔克医生牌特效药、阿格钮牌药粉、盎格鲁•美国人牌黏膜炎药粉、比尔内牌鼻烟、瑞诺牌花粉症与黏膜炎用药以及阿兹玛牌膏药,只不过是一些鼻烟和喷雾剂。因为制造商知道可卡因开始的时候会使患者的各种症状消失,所以他们大可放心地为这些产品打包票。
出售治疗黏膜炎的药时,通常会附有说明,要求病人继续服药直到病愈——这种建议十有八九会产生问题,因为药里的活性成分是什么都治不了的、只会让人上瘾的兴奋剂。这些药的药性还非常强:后来人们分析了“塔克医生特效药”,发现含有1.5%的可卡因;“古柯宝拉”更厉害,含2.5%的可卡因。“奈尔牌复方达米阿那精”含3.5%,而“阿兹玛膏药”则大大一跃,含量达到16%。“阿格钮牌黏膜炎药粉”里的可卡因含量高达35%,但无可非议的冠军当属瑞诺牌花粉症和黏膜炎药。它由密歇根的恩•瑞诺医生研制,含有高达99%以上的药用纯可卡因(尽管包装上并没有提到里面含有任何可卡因成分)。这些药物售价为大约50 美分一包。令人毫不吃惊的是,这些药卖得好极了,刺激了唯一目的就是扩张的新的可卡因产业的诞生。
最初世界上只有两家公司生产可卡因:阿达姆斯丹的默克公司(供应弗洛伊德的那家)和底特律的派德制药公司(后来买通弗洛伊德给他们的产品写书面证明的那家)。继科勒的发现之后,可卡因的价格扶摇直上,两家公司都意识到,要想赚大钱,就得尽快生产出大量的可卡因来。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由于古柯叶子在从秘鲁运来的路上很容易腐烂,甚至连派德制药公司和默克公司都发现不太可能保证有大量的古柯供应。
与此同时,这个星球上的其他药物公司都在试图得到可卡因,很快情况就明朗起来:谁控制了古柯贸易——能保证得到大量高品质的古柯叶子,谁就能赚大钱。首先意识到这一点的是派德公司。他们认为,显然必须派个人到南美洲去把事情打点妥当。
因此,当“阿卡普尔科”号邮轮于1885 年1 月10 日从纽约港向着智利出发时,它的上甲板上站着一个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亨利•赫德•鲁兹比。尽管鲁兹比刚刚大学毕业,对古柯并不精通,以前也从来没有去过南美,但最后证明他是派德制药公司理想的人选。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合格的医生和多才多艺的植物学家,而是因为他具有另一种更重要的品质:创新精神。
最终到达了玻利维亚之后,鲁兹比马上就发现了问题的本质。他从自己的植物学研究中了解到,古柯无法在北美生长,但是需要运输的古柯叶子数量巨大,而且价格昂贵,常常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发霉了。他开动脑筋琢磨这个问题。很快,在拉巴斯城一家肮脏的旅馆里,他灵机一动,有了主意。
鲁兹比的主意是在玻利维亚把古柯叶子加工成粗制的可卡因,然后再把这种产品运到美国去进行最后的精加工。这个主意很有前途,不过有一个关键的缺陷:可卡因的提炼过程非常复杂,必须在正规的制药工厂进行,但是玻利维亚没有合适的设备。鲁兹比又想了想。要是能找到更简单的从古柯中提炼可卡因的方法,那事情就容易多了。他对这个主意感到非常激动,于是决定自己来找到它。
在这个想法的刺激下,他马上开始着手实施这个计划,从当地的市场买来了几大袋子古柯叶子,在旅馆二楼的空房间里进行试验。正如他所愿,计划进行了几天后,和鲁兹比同居一处的人吃惊地听到几声歇斯底里的叫声,接着就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他一直在进行一种复杂的提炼过程的最后一步,需要把古柯叶子溶液放在纯酒精里蒸馏。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仪器,他只好自己进行改进,把一个铜制的蒸馏器放在敞开的炭火上,再把酒精倒进蒸馏器里。可是这个蒸馏器不是用作这种用途的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裂开了,里面具有爆炸性的混合物泼在下面燃烧的火苗上。一眨眼的工夫,所有的东西都烧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鲁兹比抄起仪器——呼呼冒着火苗的酒精和所有的东西,径直从窗户扔了出去。火球从两层楼上坠落,落到了大街上,点燃了旅馆的走廊,最后才在地面的鹅卵石上燃烧殆尽。谢天谢地当时没有人从旅馆前面走过。
经历了一番艰苦的准备工作之后,鲁兹比很快又开始了,这一次用了改进过的化学方法,再加上运气好,他找到了一直要找的东西:从古柯叶子里提炼可卡因的新方法,可以得到状态稳定的可卡因。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非常简单。他发明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今天的制药工业所用的方法。它的基本步骤是,把古柯叶子放在硫酸溶液里浸泡一段时间,泡出里面的精华,然后把叶子舀出来,剩下的便是一种暗棕色的汤。接下来把这种汤同酒精充分混合摇匀,让酒精滤出溶液里的生物碱。然后在里面加上诸如小苏打之类的碱,便会沉淀出一种白色的浮渣样的物质。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原始膏体,再对这种膏体进行过滤干燥,里面便含有40%~65%的可卡因。
在南美,这种膏体便是可卡因交易的标准单位,而不是可卡因氢氯化合物本身;可卡因巨头们很少购买古柯叶子——他们成公斤地购买古柯膏。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同鲁兹比发明这种方法的原因一样:因为古柯膏很稳定,容易运输。别忘了,100 公斤的古柯叶子(足以装满一辆普通汽车)可以制造出大约1 公斤的古柯膏(刚能填满一品脱的瓶子),它的优势太明显了。
鲁兹比的新方法很快导致古柯叶子贸易崩溃:做古柯膏生意要便宜得多,根本就不值得再去进口古柯叶子。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古柯种植地区附近冒出了许多制造可卡因的小工厂。很快,除了古柯生长的地方,在哪儿都很难找到古柯叶子。这样一来又有了一种反弹:由于找不到古柯叶子来进行试验,科学家们便认为古柯叶子和可卡因本身是一回事儿。古柯叶子当然同可卡因一样危险,除此之外便没有什么其他的内在特点了。就这样,当可卡因的形象在公众的意识里发生了改变,被视为洪水猛兽时,古柯也与之同命运。对嚼客而言,他们的祖先历代都嚼着这种无害的叶子,可是他们现在发现自己被归类为瘾君子。不过,最初的时候,古柯贸易的繁荣曾令南美人极为兴奋。
秘鲁在早期的可卡因贸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直在这里种了几千年的古柯,所以他们不光有种植园,还真正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有一点,从1860 年尼曼分离出可卡因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一直在扩大生产来满足国际上对古柯激增的需求,25 年后,秘鲁终于等到了机会。
可卡因粗加工工厂纷纷出现在胡安诺科山谷附近(这里是500 年前的印加古柯产业的家园,现在仍然是古柯贸易的所在)。看起来,这个十分落后的国家似乎第一次可以真正赚点外快。有一段时间的确如此:市场需求非常大,致使秘鲁的古柯产业扶摇直上,到1900 年,秘鲁每年可出口一万公斤的可卡因膏——由100 多万公斤的古柯叶子制成。
不幸的是好景不长。秘鲁和玻利维亚的专家们认为他们可以无限期地赚到钱,因为古柯除了南美哪儿都生长不了。他们错了。尽管鲁兹比是可卡因进入医界后第一个进军南美的医药公司代表,但是其他更加大肆声张的来访者已经在探索古柯的潜力,在南美洲浓密的热带雨林中劈出路来,从所到之处窃取了大量的植物标本。
在园艺偷盗领域遥遥领先的是英国人。直到19 世纪头10 年,世界上最贵的药一直是奎宁——已知的唯一治疗疟疾的药,英国殖民地印度真正的灾难之源便是疟疾。奎宁来自于金鸡纳树的树皮,当时这种树只有南美洲有。毫不令人吃惊的是,英国皇家植物园急于伸手弄到一些,于是派出一系列探险队进入南美的丛林以便获得种子进行培育。
金鸡纳树的种子和枝条很快被送到伦敦,人们研究之后便把它们送到锡兰和印度。一旦新的金鸡纳树种植园结出果实,奎宁的价格便一落千丈。这对英国人是个好消息——但对南美洲的奎宁产业来说可就没有那么好了。几年之后的1876 年,英国人还对橡胶故伎重施(从巴西偷来橡胶移植到锡兰)。他们此时已经把这一招儿用在了古柯身上。1870 年,英国皇家植物园把古柯树苗送到锡兰、牙买加、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英国殖民地圭亚那和印度,希望它们能在某个地方生长得不错。事实上,它们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长得很好,英国人的古柯很快开始同秘鲁古柯争夺世界市场的注意力了。在锡兰,古柯作为商业作物的兴起得益于另一种主要作物——咖啡
所遭受的打击。一种毒性特别厉害的菌类15 年内横扫了大约40 470 公顷的咖啡。显然,人们需要一种能够抵御咖啡枯萎病的新作物。古柯成了这种作物。英国杂志《新商业植物》颇有见地地指出,“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欧洲市场将主要由东方供应”。到1912 年的时候,单是锡兰就拥有近1 600 公顷的古柯。然而就全球范围而言,这简直不算什么。英国人从来都没有真正生产过这么多的古柯,原因很简单:其他产品利润要大得多,种植起来也要容易得多,例如鸦片。也许带头从秘鲁盗窃古柯种子的是英国人,但是秘鲁人真正要提防的却不是他们。真正欺骗了秘鲁人的是荷兰人。
同英国人一样,荷兰人在19 世纪60 年代晚期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古柯种植园。他们最初在雅加达东南部建立的“土地庄园”(“政府植物园”)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不过等到一家比利时公司赫曼•林登公司于1876 年发售一种新品种古柯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改变。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杜拉群岛都开始种植这种新品种的古柯。这一点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这种古柯就是贾瓦高卡属的图克西里古柯。图克西里古柯的不同之处不仅体现在它具有很高的生物碱含量(含量高达1.5%),而且因为它的可卡因提取过程很特殊,这一点使得它在欧洲古柯叶子市场上不那么受欢迎。
这都是德国人插足这一领域之前的事情。1898 年,一家名叫费博沃克的德国化学公司偷偷摸摸地找到一种从图克西里古柯里提取可卡因的新方法。他们马上对这种提取方法申请专利,有谣言说这种方法可以提取出荷兰人的种植园中“含1.5%可卡因的植物”里所有的可卡因。荷兰古柯叶子里的可卡因含量比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古柯叶子含量高一倍——这使它在世界市场上所向无敌。
唯一的问题是,由于图克西里古柯的提取过程非常复杂,必须把古柯叶子而不是粗制的可卡因膏送到欧洲去,这使得它很难受欢迎——也给秘鲁人赢得了一些时间。然而,一旦运输上的问题得到解决,它便垄断了市场——可以将它装在巨大的容器里从印度尼西亚运到费博沃克进行加工,然后再运到世界各地。但是,正当德国人以为他们把整宗生意都打点好了的时候,荷兰人显然并不受德国专利法的约束,在爪哇建立了自己的图克西里古柯加工工厂,开始生产出他们自己的可卡因,把德国人完全踢出了生意圈。加工商最终在1900 年同印度尼西亚的古柯种植园主一起成立了一家名叫荷兰可卡因工厂的公司。爪哇可卡因大量涌入了世界市场。
国际上的制药公司购买初步加工过的可卡因进行深加工,然后把产品运送出去——数量多得越来越离谱儿。而且,当德国人的提取方法专利于1903 年到期的时候,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都参与了进来,亚洲的可卡因生产便一发不可收拾。到1920 年,单是爪哇一个国家一年就生产出了1 650 吨的古柯叶子。默克公司从1887~1913 年生产出了超过75 吨的可卡因,从1906~1918 年平均每年生产4 吨。
所有这些发展都导致了欧洲和美国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可卡因,结果造成价格崩溃,可卡因在市场上更容易买到——因而上瘾的人就更多。问题几乎马上就暴露了出来。早在1885 年,弗洛伊德的同事埃伦梅尔就指责他“释放”了这种药。很快,另一位直言不讳的医生路易斯•莱文也加入了声讨的行列。莱文接着写出了他这一时代对麻醉品的权威性论述《梦想国》,他在文中记录了早期可卡因瘾君子们的命运:
一个瘾君子吸入了3.25 克的可卡因,便把自己武装起来,免受想象中的敌人的攻击;另一个瘾君子急性癫狂发作,从船上跳进了水里;还有一个瘾君子把家具和陶器打得粉碎,还袭击朋友……这些不幸的人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的有生之年完全由不得不服用的下一剂可卡因来测量,每服下这样一剂药,他们生与死的悲剧就朝着不可避免的结局前进一步……只有比率非常小的瘾君子能恢复过来,其他的人都会旧病复发。
这些不幸的人中的大多数要么是医生,要么是想要戒毒的吗啡上瘾者。人们很快都认识到,用可卡因来治疗吗啡上瘾是个严重的错误——弗洛伊德自己最终也承认这种方法就像是“要撒旦来驱除魔鬼”。到1887 年年底的时候,《纽约医学记录》总结道:“没有哪一种历史这么短的医学方法能像可卡因这样使这么多的人受害。我们担心可卡因上瘾只能带来凄惨的未来。”如果不是出于其个原因的话,这种警告也许本会使得上瘾的人停止使用可卡因,让它不再出现在公众的意识里,这个原因就是:人人都注意到,可卡因会带来快乐。尽管早期的人员死亡大多是因为“医疗原因”(不论这种说法有多么误导人)上瘾而致,《纽约医学记录》1885 年11 月的一篇颇有预见性的报道已经指出了以后的发展方向:
对一些人而言,再没有什么比沉溺于可卡因更令人心醉的事情了。可卡因能减轻疲惫感,消除精神压抑,产生愉悦的美妙感觉。一开始的时候,药物的后期效果非常轻微,几乎无法觉察出来,但是不断沉溺于可卡因之中最终会产生一种不得不满足的渴望;个体接下来会变得紧张、发抖、失眠、没有胃口,最后沦落为严重神经衰弱。
到1900 年,由于娱乐目的过量使用可卡因而导致死亡的病例超过了因医疗事故而死亡的人数。显然,一种新的药物上瘾问题即将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成立了一个“毒瘾成因委员会”,这个机构比较了它所收集到的1898~1902 年所有有关药物上瘾的资料。该委员会指出,美国的人口数量4 年间上升了10%,而可卡因进口量则上升了40%(这还不包括诸如派德之类的公司在美国生产的可卡因)。与此同时,外科手术中使用可卡因作为麻醉剂的情况也迅速减少,因为人们发现了诸如普鲁卡因之类更安全的人工合成麻醉剂。
1890 年,随着可卡因最初的繁荣,美国对可卡因的需求大约为每年一吨。15 年后这种需求达到了7 吨多。然而市场很容易就吸收了多余的量。委员会给美国的制药商发出了调查问卷,结果发现每家公司平均有5 个瘾君子,据此估计美国总共有20 万个瘾君子。同年,《英国医学杂志》报道说光是辛辛那提就有大约1 万人染上了可卡因瘾。
美国人那时才明白可卡因上瘾是个严重的问题。尽管还没有针对可卡因的联邦立法,美国各个州已经开始自己采取行动。奥尔良在1887 年开始行动,禁止销售没有处方的可卡因。蒙大拿州于两年后,纽约于1893 年都紧随其后采取了行动。接近1900 年的时候,许多美国本土地区都禁止可卡因。
然而,仅仅限制可卡因销售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人们从专利药里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它。此外,各种惩罚措施也执行得不严格,人们很容易就能够贿赂药剂师买到可卡因。而且,由于美国各州在药物立法上没有达成一致,可卡因在一个州是非法的,而在另一个州则非常合法。有些规定可卡因合法的州干脆进口更多的可卡因,然后穿越边界运到另一个规定可卡因不合法的州去。当地的执法人员很快就发现,随着上瘾现象不断蔓延,要控制可卡因供应简直不可能,所以干脆听之任之。只有医学界似乎还是对此十分关注。
医生一度认为需要对可卡因和鸦片的销售加以管制。医学界认为可卡因的害处尤其大,因为他们在它身上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到1901 年的时候,美国30%的可卡因上瘾者仍然是牙医)。医学协会对含有可卡因的江湖假药的持续热销,还有它们使用虚假的广告手段,尤其感到愤怒。为了追求越来越高的销售量,这些生产者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引用著名医生为他们的药做担保时说的话,然而这些医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药,或是虚构一位根本就不存在的医生。被治愈的病人也同样都是虚构的。就连医学行业本身也被这些大众制药行业当作了目标:据说医生嘲笑专利药是因为人们生病的话,就能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
第1章 印加人的可乐
第2章 德•加希耶疯了
第3章 从古柯到可卡因
第4章 人类第三大劫难
第5章 弗洛伊德的渴望与恐惧
第6章 春药?毒药?
第7章 黑人、苦力、英国人
第8章 好莱坞的宠儿
第9章 卷土重来
第10章 泛滥与恐慌
第11章 “死亡未婚夫”的报复
第12章 提纯可卡因——人咬狗
第13章 中情局引火上身
第14章 《可卡因骑士》
第15章 墨西哥往事
第16章 玻利维亚惊魂
第17章 秘鲁的无奈
第18章 建在毒品上的哥伦比亚
第19章 可卡因游戏
斯特里特费尔德是一个极其会讲故事的人,读这本书是一次非常伟大的阅读体验。”
——《西雅图时报》
一次穿越异国领土的冒险之旅……斯特里特费尔德的写作风格跳脱而生动,让人产生兴奋刺激的阅读快感。
——《 ―Time Out New York》
一个迷人的、细节丰富的故事……斯特里特费尔德坦诚直率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与它表面的样子并不相符的、不为人知的世界。
——《出版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