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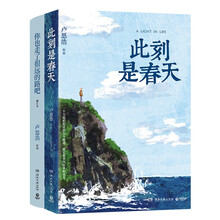








法国作家泰松76天走遍法国乡村
幽暗的小径,古老乡村国度的网络,它们指向空隙,被遗忘,只有寂静环绕,你一走过,荆棘就在身后合拢。
“他喜爱一切掩饰人世的东西:云彩、距离、伏特加。”
步行横穿法国需要十六天,纵越需要二十五天。但那是以拿破仑行军时的速度而已,不能欣赏沿途景致。西尔万·泰松在幽暗的小径之中徐徐前进,不仅完成了法国的徒步旅行,也记录下了许多只有通过用心和细致的观察才能得到的旅行体验。
受伤之后,泰松决定通过徒步旅行来缓解伤痛。他从法国的南端、与意大利临界的唐德县一路向北,来到能眺望英吉利海峡的科坦登半岛。这场他称之为“我的大游戏”的徒步旅行一共耗时七十六天,目的是发现法国的“超级乡村”。
糟糕的开始
火车上
为什么高速火车以这种速度开行?旅行速度这么快有什么用?让风景以时速300公里飞逝,然后再花几个月重走一遍,多么荒唐!当速度驱走风景时,我想到我爱的人们,我所想的比我能对他们表达的感情更好。事实上,我宁愿想着他们,而不是接触他们。亲近的人总是想“见面”,好像这是绝对必要,但思想却能提供如此美好的亲密关系。
8月24日,意大利边境
这是行走的第一天,从唐德火车站开始。从尼斯出发的火车把我带到这里。我迈着虚弱的步子攀登山口。金色的禾木扫过晚间的空气。这些屈膝礼是友谊的第一个意象,具有纯粹的美。经历过这些悲伤的月份以后,就连阳光中的飞蝇也提供了幸福的征兆。它们在淡金色中形成的阴影向孤独发出信号,或许组成了字迹。它们可能对我们说:“停止你们对自然界的全面战争吧”?
雪松站在路旁,显得十分严肃:它们的根紧围着路堤——树木常有一种确信自己理所当然的神气。一个牧羊人以比我更加大胆的步伐走下山来,他关节粗大,出现在转弯处,样子像吉奥诺笔下的一个主人公。一个本地人。我呢,却总像一个外乡人。
“你好,去城里吗?”我说。
“不是。”他说。
“山上有羊群吗?”我说。
“没有。”
“你下山休息吗?”
“不是。”
我得摆脱这种喜欢攀谈的市民习性。
唐德山口标志着梅康图尔山脊线的一个凹谷,把意大利和法国隔开。我决定从那里开始,从法国的东南角走到科唐坦半岛北部。按照传统,俄罗斯人在出发旅行前要在椅子上、行李箱上、遇到的第一块石头上坐几秒钟,放空,想想自己离开了什么,焦虑自己有没有关上煤气,藏好尸体——我还知道什么?于是,我像俄国佬一样坐下,背靠一座木制小礼拜堂,那里有一尊圣母像面朝意大利的景色沉思。突然,我起身,出发。
在路堤上,我受伤的眼睛把母牛当成了在斜坡上滚动的圆石。密立黑色松树的山脊让我想起二十岁时见到的山丘,它们给中国云南的蓝天轧出花边。但我在黄昏的空气中把这些念头赶走。这些杂乱的类比堵塞了我的头脑。
我不是在佩索阿《异教徒诗歌》的支配下发誓,要坚持几个月吗:
我说了植物,“它是一株植物。”
我说了我自己,“它是我。”
而我不再说。
还有什么东西去说呢?
哦,我怀疑“不安之人”佩索阿从未忠于他的计划。如何能够相信,他会满足于这个世界呢?人们写下这类宣言,然后背叛自己的理论,度过一生。在这几周步行途中,我将试着以纯净的目光看待事物,不透过分析的面纱,也不经过记忆的过滤。至此,我已经学会把自然和生物当作一张记录印象的纸页。现在我急需学着享受阳光而不召唤斯塔尔夫人,享受风但不背诵荷尔德林,品尝新鲜葡萄酒却不会看见法斯塔夫在杯底胡闹。简言之,像一只狗一样生活:它们品味着和平,垂着舌头,似乎将要吞下天空、森林、海洋,甚至是降临的夜晚。当然,这一决心必将失败。欧洲人本性难移。
海拔两千米时,我在一座混凝土掩体旁发现一块草丛茂密的山肩。我点起火。木头潮湿,我拼命吹着火炭,导致被摔陷的头晕眩起来。热气把大蜘蛛逼了出来,我已经不害怕了,因为之前已经看过很多蜘蛛逃出我的视线。宿营布勉强保护我不受黑暗吐出的湿云侵袭。我有些惶恐,这是坠楼后第一次在露天过夜。土地再次迎接我——这一次没那么剧烈。我重回珍爱的花园:星空下的森林。空气凉爽,土地高低不平,地势倾斜:这是个好兆头。只要我们珍惜、期待户外的夜晚,当它们使徒步的一天圆满结束时,就该写入功劳簿。它们顶开盖子,膨胀梦想。没听见欧洲城市里的吵嚷越来越响吗:透透气!透透气!一年前躺在医院时,我梦想在枞木下伸展身体。现在,宿营的时光回来了。
8月25日,鲁瓦亚河谷
这一晚很奇怪。大约从晚上十一点开始。第一声枪响回荡在两、三百米外,然后是第二声,后来,爆炸声就没停过,每次间隔一分钟。有时间歇缩短至三十秒。谁在夜里射击?是一个怨恨黑暗的东正教疯长老吗?
我刚上路时心想,如果成功穿越法国,那将是一场宽恕。如果不成功,我会把失败视为又一次跌落。病愈的前景如此遥远!像科唐坦半岛一样远!我把救赎放在行动之中。
早上,我瞥见山坳里有个羊圈。一个皮肤光滑、呈粉红色的女人在门口忙碌。她有着弗拉芒人的大脸颊,露出二头肌。她从勃鲁盖尔的画中走出,刚挤完奶回来。
“我昨晚听见枪声。”我说。
“是台燃气机,为了把狼赶跑。砰!砰!”她说。
“啊?”
“你想要点什么?”她说。
“有什么就要什么。”
“牛奶奶酪。干奶酪。”
“来三百克。狼害怕吗?”
“谁知道呢?三欧元。”
情况还是变糟了。人类繁衍生息,包围世界,给土地浇上水泥,占领山谷,群居高原,杀死神灵,屠戮野兽。他们的一代代后人和食草的转基因畜群遍布大地。三十年前的一天,狼经由阿布鲁佐大区回到梅康图尔。一些有智慧的人想保护狼。牧人对此火冒三丈,因为有猛兽在,他们就得加强警戒。“狼的朋友倒是在城里暖暖和和地睡觉”,养牲畜的人抱怨。现在,高山牧场必须配备机器,模仿枪声,保护食草动物不受回家的猛兽侵害。如果我是狼,会这样想:“进步?笑话。”
1 前言
1 糟糕的开始
9 废墟与荆棘
52 幽暗的小径
73 阴郁的暗影
97 走向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