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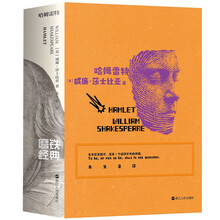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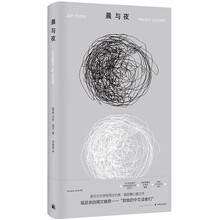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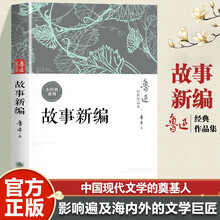
我理解这套专辑的意图在于,尝试记录共同思潮中个体的历程。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时有跌宕起伏,但就像洪水开闸,直流三千尺,再无回转的可能。新时期文学可称弄潮儿,乘风乘水,且推波助澜。倏忽间,已将半个世纪。中国社会走入现代,大约从未有过如此久长的时日,从容扩展精神领域。身在其中并不觉得,抬头看,却是一惊诧。如我这样的小说者,是从体验出发,理性的概念化往往成为负累,压抑了感官的自由。所以,我想这大约是专辑的第二个意图,让写作人隐形的思想浮出水面,呈现足迹,纳入历史的进步。
因循这一解释,着手选择文字,同时,也给自己一个机会,检点以往,总结经验。
我设计以散文《茹家溇》开篇。那是1986年的行旅,去到浙江绍兴,拜文友协助,查访母系祖居。从背景看,正是寻根文学发起,大家伙纷纷投奔“文学的根”。有的入径地缘,向山川河流进发;有的倒溯时间,访问古城古镇古村。大到宇宙历史;小至家庭起源,两头都是虚空茫然,正合小说窃意。回到《茹家溇》内文,则有着话说从头的意思。从1986往回算,写作约有七八个年头,还在情绪的主导下,世事与青春都在平息骚动,渐趋安稳。其实是个迷茫阶段,经验被过度地挥霍,来不及积蓄能量,开发新世界。同时呢,也意味着形势要有转折。《成长初始革命年》和《魏庄》可视作延伸和继续。于是,就让这一辑起句,比兴出下文。
第二部分由四个短文合成,分别于1989、1995、1997和2003,应稿约而成章。《我的同学董小苹》已想不起事由,写的是儿时小伙伴,放在第二辑篇首,正与上一辑交集,像是过渡。《重建象牙塔》是替陈思和的文论集作序,我够不上了解他的思想,熟悉的是他这个人,我们同龄,同届,住同一条街,俗话叫做“街坊”,但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方才照面,进行《两个69届初中生的对话》,算得上以文会友。所写“序”很可能与他书中文章不贴,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也是借他的题说自己的话,不期然处总有碰头的地方。《接近世纪初》是因病歇笔一年之后,有换了人间的心情。具体什么样的要求想不太起来了,可能是指定的议题,也可能是自定。跨世纪的人,有一种嬗变的焦虑,造物似乎也是有安排,给时间刻度,好范约洪荒,比如竹的节,树的年轮。所以,就是社会的普遍性暗示,算一个坐标吧。第三篇《英特纳雄耐尔》,又要涉及一个人,陈映真。倘若真有思想史这一说,在我,便是贯穿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天。中国大陆迅疾走完资本经济前期、中期以及后期,从孤立进到全球体系,再又回归中国国情,他,一个亚洲后发展地区的预言人,国际共产主义理想的明日黄花,引领着我,走去无可望见的希望。这样,就来到第三部分,以《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承上启下,然后四次发言,分散在二十一世纪的十几个年头。一个小说者,在文本以外的声音,可能最具思想的外形,但也最可能露怯。以虚构为职业的人也许不该在现实中多说话,因为我们常常混淆真伪,“想当然”错成“所以然”。就像说禅,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就是错。
第四部分是占全辑篇幅半数以上,写作时间比较接近现在,实是多年学习与实践的感想心得,文学和艺术的观点,对于思想来说,未免太过具体。可是,我们这样的人,不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思想的吗?我们做的活计,堪称莫须有,好比《红楼梦》太虚幻境的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思想本来应该让存在更明晰,我们却相反,让世界变得模糊,暧昧,摇曳不定,仿佛物体在光影里的边缘,也许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史。从这里说,这部分应是专辑的主体,之前则可作附录。
与传统文人的书斋生涯不同,与现代的教育的规训不同,他们的经历有着类似的“身份”——当过工人、农民或军人,每个人都和土地息息相关,和底层社会息息相关。那么,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时间表”:沿着轴线,穿越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从九十年代一路走过来,直至今日——当然也可以反向检查一步步的印迹,追溯到青少年和童年,再从路的尽头转身——构成他们的“写作”的真正的含义。
——北岛
(丛书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