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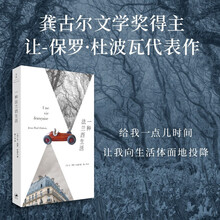

优雅、高贵、黑暗、飘忽,阿瑯是如此令人着迷也让人捉摸不透,当夏天走向结束,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法国作家格拉克在《阴郁的美男子》中的文字流溢着窒息之美与彻底的破败。
自他和爱人到达优雅的海边旅馆的那一刻起,阿瑯就在其他客人中引起了骚动,他们为他着迷。他是那么的捉摸不定、若即若离、美丽迷人,他赌博、游泳、跳舞,他们陶醉于这一股陌生的疯狂中。不久,他甚至出现在他们的梦境中,萦绕不散。
一个接一个地,每一个客人都被阿瑯致命地吸引着。当八月的薄雾退去,夏日走向尽头,他们走向了自我毁灭。
这部饱满的诗性小说《阴郁的美男子》是住在深渊边缘的生命的梦幻般的写照。
在秋日悄然流逝的最后几天,我想起了那片小沙滩边的林荫小道,我对它有种特殊的偏好,在这季节更替时,更是寂静一片。小旅馆勉强维持生计,闲散的游客如迁徙一般,随着春分秋分的潮涨潮落,人潮即将散去,再也不见穿浅色衣裙的女人和傲慢的孩子。猛然发现,混凝土砖石岩洞,洛可可风格的钟乳石,充满童趣的迷人建筑,还有受海风侵蚀、多次修葺的像干枯的银莲花一般的花坛,如同九月海上破碎的浪花;大凡留下来独自面对空落落的大海的人,由于没有了令人安心的琐事,大白天也不可避免地感到自己如同一个幽灵。海滨上,毫无生气的平台都装有落地玻璃,上面的铁饰斑斑驳驳,布满盐霜,如同遭到抢劫的珠宝店一样让人焦虑不安。窗户上的百叶帘紧闭着,透出磨损、破旧的青蓝色,不经意回流着过去时光中生命的衰竭。然而,十月的这个清晨,阳光有点刺眼,寂静中冒出了些声音,像睡梦中的人做了个一本正经的动作一样奇怪——白色的木栅栏嘎吱作响,铃声在一整条空空荡荡的小路上久久回荡。我在做梦。谁会在这里如此郑重其事地通报自己的到来呢?这里没有人,再也没有人。
沙滩的别墅整齐地排列成阶梯状,此时,我一头钻入这些别墅的后面,走在绿树成荫的褐色土地上,地上覆盖着沙子和松针,软绵绵的,几乎没有声音。转过沙滩的拐角,一片难以描述的寂静。在林荫道的洼地中心,隐约传来大海动人的喧闹声,就像在郊外沉寂的花园深处隐约传来暴动的声响。在松树和雪松暗绿色的土地上,桦树和白杨忽然冒出火焰般的光芒,化为一抹金色的轻烟,红色的火花蔓延,如同烧着的纸上火舌的缓慢移动。天渐渐亮了,灰蒙蒙的大海渐渐成为主色调,阴沉的色调一点一点微妙地沉淀。海风的盐分使墙体的颜色愈加暗淡,铁栅栏的锈红愈加鲜亮刺眼,沙子穿过门缝,铺满了地板;这突如其来的奇特的海侵,如沙石和珊瑚一般坚硬灰暗,已说不清楚是怎样的轨迹,如冷却的火灾,干涸的海啸,浸透这座小城。
也有的时候,某些阴沉的下午,天空灰蒙蒙的,一动不动,如同罩在毫无生气的冬日花园的玻璃窗之下,阳光的照射已消退了其多变的表面,但勉强透着生机,想到某些事物可能蕴藏的无限的潜能,这种感觉涌上心头,让人产生厌恶之感。同样地,有时我会想象某场演出结束后,半夜溜进空空的剧院,第一次发现黑黢黢的放映室里的布景,而不会将自己置于一场游戏之中。夜晚空旷的街道,重新开启的剧院,淡季里只属于大海的海滩,一起交织着一份静谧,如同五千年的树木和古老的石头交织着埃及的秘密,解开坟墓的魔力;漫不经心的手,拿着钥匙,摆弄着戒指,抚摸着墓志铭,转动戒指,我变成了幽灵般的盗墓贼,轻轻的北风从海面飘来,潮汐的声音突然变得越来越清晰,太阳终于消失在一九××年十月八日午后的薄雾里。
热拉尔的日记
六月二十九日
今天早上,散步走到了克朗塔克。小港口的堤坝周围,荒凉一片,左面广阔的沙滩,空空荡荡,边沿是沙丘,上面覆盖着干枯的灯芯草。海上天气很糟,天空低沉灰暗,青灰色的巨浪像瀑布一样强有力地打在沙滩上。但是堤坝之间,巨浪打在石壁上,不发出一点声响,令人诧异:巨大的浪舌来去匆匆,粗鲁、令人不安,但又不失灵巧,就像食蚁兽的舌头,忽然跳起,还来不及喊小心,就已经到了堤坝,在空中碎裂成冰冷的水柱。中午在餐馆里吃了饭,餐馆位于沙丘中间,偏僻冷清,吊脚楼式的地板发出沉闷的声响,宽敞无比的餐厅( 大概每逢周日本地的年轻人就来这里跳舞 ),装饰着彩纸制作的花环,透出一分凄凉,锃亮的杉木地板,在我看来,不像节日的气氛,更多的是像船员的休息室,水手的掩蔽所,所有这些景致,在本地区随处可见( 沿街的各类储物间都放置着救生艇 ),并给人一种凄凉、贫瘠、受约束的感觉,给整个布列塔尼地区的风景罩上了忧郁的气氛。
沿着沙滩回来的路上,我碰到克朗塔克的成双成对来跳舞的年轻人,神情严肃,近乎沉重,女孩儿的头发在狂风中飞舞,男生们则双手插在口袋里:天气并不热。一条僻静的小路,从那儿可以看到海滩上凸出的沙丘,海水拍打在“渔民归来”餐厅的屋顶下沿,水沫飞舞。真是个与众不同而又有趣的地方。接着,在海浪低沉的拍击声中,一抹短暂的阳光下,听到碟片机的哼唱,在海浪拍岸隐隐约约的低音衬托下,回响在水天之间,超凡脱俗。一个女孩,逆着人潮,独自走在沙滩边,闲适、缓慢、慵懒。时而俯下身拾贝壳和海中的漂流物,时而蒙眬地注视着远方的大海,此时,她笨拙地双手叉着腰——这个质朴的脑袋在想什么,只有她自己知道。在正午或黄昏时分,这些散步的人,在某一隅听收音机、扔石子、单脚跳或者掏乌鸫窝,就这样不断地把我卷入如画的风景之中,有的时候,整个角落里也有我完全看不懂的手势或行为,景色因此显得暗淡。
散步回来后,我一个人吃了晚饭——整个直前一族的伙伴都已经出发去赌场了。
晚饭后散步在沙滩上。海滩壮丽,忧郁又充满光辉,海滨的玻璃在夕阳下发出熠熠红光,像烧着了一样,又像灯光闪亮的客轮。这片空旷的沙滩,还留有余热,软绵绵的,忍不住想要踩压它、堆砌它,天真地糟蹋它的完美。然而,空气却如此贞洁、透明,冷得纯粹,如同被看不见的细雨不断地冲刷过一样。沙沟里轻柔的汩汩声( 低潮时 )将这雨后的风景嵌入大地,水流的声音仿佛伐木工的斧头在开垦。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啊!何等舒适!沙尘轻轻地飘落沙丘上,空气的舞动就像无数的旌旗迎风飘扬飞舞。而地平线上,波涛翻涌,白浪掀天,起落跌宕,云彩中夹杂着浪花与阳光,波涛汹涌的海岸,绵延的大海渐渐消失在远方。
六月三十日
“浪花旅馆”出航了,如同一艘海轮准备出发迎接夏季。眼下旅馆里的人越来越多,摩肩擦肘:这个度假小世界中似乎出现了一个灵魂人物。今早,从我的窗户看到,雅克带着他的船员们去了海滨浴场。他的房间就在我的正上方,每天早上都是一阵忙乱的声音:就像船员的休息室,大家随意进出,放声大笑,如同睡一个吊床的伙伴,亲密无间。但是这种毫无顾忌的喧哗,到克里斯黛尔的房间前总是戛然而止。这位穿着浴衣的小公主在她正式出门之前,或者在她发出特定信号之前,是没有人敢去敲她的门的。大凡都是这样,每个小团体或每个自然而然构成的小组中,总有一个核心人,凡事找他商量,就好比俗语所说,在打猎开始时会先瞥一眼狩猎首领再放开猎狗。
克里斯黛尔一直自上而下地俯瞰着这个小群体,低垂着眼帘,非常性感,仿佛浸润于青春之浴,完美无瑕,就连她的下颌也如量身定做,不偏不倚嵌于其中( 下颌对一般人来说要么太长要么太短,常常不到位 ),一旦她闭上嘴巴,从她嘴里就再也听不到一个字,表现出极强的分寸和控制力,给人安宁、沉静的本质。
我对克里斯黛尔很感兴趣,之所以感兴趣,因为她在表演,并且乐在其中。在沙滩这样随意的地方,有时,我发现她眼中闪现着克制。多美的词!这种克制——在我看来,我希望对她而言也是如此——不是受制于良好的教育,而是缘于某种反常的消遣,对自己扮演角色的自我欣赏。有点类似于在小剧院中,巴尔扎克笔下《 贝阿特丽丝 》中的康迪说的一句话:“对他们而言,我是神吗?”对这个人物,天才的作家巴尔扎克极尽赞美之词。
然而对我来说,她不是。我打算明天和她聊一聊,让她有机会显露自己的聪慧。
七月一日
很久以来,我都没有像现在迫不及待地打开日记,如此渴望写下一些东西。打开窗户,对着晚风,我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转了很久,充满了精力,脑袋像刚洗完澡一样清楚灵敏,装满了飞来飞去的各种清晰的想法,沾沾自喜。今晚,我刚刚和克里斯黛尔进行了一次极其不寻常的谈话。
我已经感觉到了,我无法描述出晚上谈话的色彩,在我记忆中,她一直沉浸在夜幕和月光的氛围之中。此时借助爱伦·坡的诗句描述新生和追忆的氛围,或迷蒙或可转换——如同旱季时的一片绿洲:
这是我最难追忆的一年,
一个荒凉的十月的夜里……
格拉克在法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源于他独特的风格。他是20世纪伟大的文体家之一,他的作品有一股非同寻常的、幻觉一般的激发力。
——英国《泰晤士报》
格拉克是文学这片领地中非常优秀的庭园美化师,比夏多布里昂更加细腻,比司汤达更有韵律,比普鲁斯特更具情感。
——法国《电视全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