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码头”读库·辽宁舰:更多的光线来自黄昏》:
白桦树上的诗篇
穆格敦是我在图瓦认识的猎人,他自称是诗人。
他灰胡子灰眼睛,说话时眼睛看着你的一切动作,好像你是随时可以飞出笼子的小鸟。
穆格敦会说十分流利的蒙古话,他说是小时候背诵蒙古史诗《江格尔》时学会的,用词文雅体面。
他住的房子是用粗大的松木横着垛成的,在中国东北,这种房子叫“木刻楞”。
他说:“你是作家,我是诗人。我们两个相会,像天上的星星走到一起握手一样让人感动。你会向我学到许多珍贵的学问。”“是的。”我回答。
“唉!”他叹口气,“我要让你看一样东西,一首诗篇,它的题目叫《命运》。”穆格敦从木床下面拎出一只桦树皮做的箱子,放在桌子上,刚要打开却停下来,走到窗边,指着远处一棵树说:“就是它。”“它也是诗人吗?”我问。
“你的问话很愚蠢,但我原谅你。它是一棵树,这个桦树皮包里装着它的子孙的命运。”那是一棵白桦树,独自长在高处,周围没有其他树,地上开着粉红色的诺门罕樱花。
“回头。”他说着,打开了箱子。箱子里装满了金黄的桦树叶,上面写着字。
“每片叶子上都写上了字,是我作的诗。”我等他说下去。
“你为什么不问后来呢?”穆格敦说。
我问他:“你在桦树叶子上写满了诗,后来呢?”、“这些诗是用岩山羊的血写上去的,一百年也不会褪色。你知道我写这些诗多不容易!”“创作是艰难的。”“不对,我越看你越不像个作家。创作很容易,创作诗最容易,比吃蔓越橘果实还容易。”“后来呢?”我问。
“那时候,这些叶子还长在树上。我不能为了方便我写诗就让它们掉下来。我搬了梯子,在每一片叶子上写满了诗句,我的腿站肿了,胳膊比酸浆果还要酸。”我仿佛看到金黄的桦树叶在枝头飞舞的场景。我问:“你为什么这样做?”穆格敦很高兴我这样问他,说古代的诗人都这样。他左手握一把干枯的树叶,右手拿出一片,念:“德行就是你把喝进嘴里的酒运到身体里的各个地方。
”他抬眼看我。“好诗。”我说。
他念:“羚羊的气味在岩石上留下花纹。”“野果因为前生的事情而脸红。”“人心里的诚实,好像海中的盐。”“都是好诗。”我说。
他瞟了我一眼:“叶子背面还有字呢。这个——‘下雪前一日,在三棵榆树的脚下,离家一公里。’这个——‘已经穿皮袄了,独贵龙山顶的石缝里。’”原来,穆格敦在白桦树的每片叶子上写诗并做了记号,秋天至,风把这些叶子吹走后,他走遍大地一一找回来。他在找回来的树叶的背面再写上地点和天气。
我不得不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你为树叶找回它们的孩子,找回来后,用树叶在树干上蹭一蹭,它就知道它回家了。”“在霜降的大地上,你眼睛盯着草地,当你发现一片有字的桦树叶时,就知道那是我写的诗,是我要找的叶子。”“有一片叶子飘进了水里,我游过去,10月份,水已经很凉了。但它不是我找的树叶,是楸树的树叶,但我也把它带上了岸。”“最远的地方离这棵树有五公里,我不知道树叶带着我写的诗怎么会走了这么远的路。”“可能有一些树叶被鹿吃掉了,有一些埋在雪里已经腐烂,我还在找它们。”“你题诗的叶子一共多少片?”我问。
“九百八十九片,我找到了二百六十一片。”穆格敦笑着说,“如果我在死亡之前能找到七百片树叶,已经很不错了。”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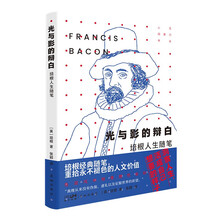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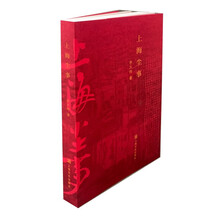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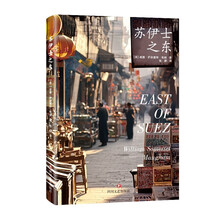
★我愿像儿童一样重新体悟大自然,记录岁月流进我心里的清水和蜜,如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说的“做一颗星辰的兄弟,或者儿子”,单纯地生活,在平静中获取力量,保持罗丹所说的“工作与耐心”,并随时准备接受自己的失败。
——鲍尔吉·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