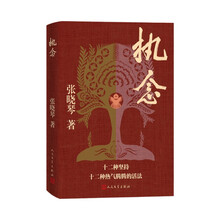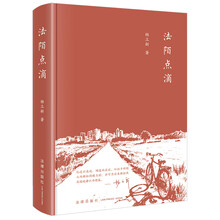在时间的荒原
一定有什么缘由我才能再次重返稻城。
起初之前它只悬挂在地图之上作为我人生必须要到达的远方被圈上记号摆放在那里,尽管离开已20年之久,我依然固执地认为它会如旧的在某片云朵的下方静静伫立。而我是只纸鸢,长久地穿行在别的云朵中,久了便不知道身体的某处悬着一根细如蛛丝的彩线,线的那头拽在一个地名手中,任凭我努力试图飞行,穿越千山万水、衣衫褴褛却依然不能变作鸟儿,于是在时光中我逐渐明白了关于故乡的概念,无论离去多久多远我必须回到那里,回到最初的来路上去……
其实,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清晰完整地将稻城描述出来,它像一只冬眠的虫子隐藏在我的记忆里、睡梦中,自离开后,有关于它的所有影像就变得不再确定起来,仿佛极熟悉忽悠间又陌生到了极点,仿佛很明晰刹那间又模糊不堪起来。
或者,它一直在原地等我归去,不停步行走着的只是我,二十年的时间我越走越远,当它再也望不到我时,我已不再是那个扎着羊角辫在青杨林中荡秋千的小女孩,人生的人与事在时间与时间之间变得不再熟悉,它分割了我和一个小城的关系,让我们离开如同分别的恋人。
胡塞尼说“记忆会爬行”,我对此深信不疑,蜿蜒过20年,稻城犹若一株爬山虎不动声色、不着痕迹沿着时光爬行于我的记忆,慢慢长满了整个人生。
我从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状态在什么时间再次回到那里,二十年的分离后,我对那个给予自己生命的地方陷入了无数种猜测,而这反反复复的猜测让我的心在旅途中不断地煎熬又不断地患得患失着。
车在高原上行进,进入理塘境内道路开始变得笔直而了无边际,当这笔直中偶然出现某个起伏,我的身体就会陷入失重后的痉挛中去,这让长时间刻板的呆坐变得既刺激又愉快。
七月的高原天高云淡绿草如茵,阳光与云影在阡陌纵横的大地上交相辉映、此起彼伏。偶尔一只鹰伸展着巨大的双翼舒缓地划过天际飞向云深处,一瞬间又咻得从某个山谷凌空而起。漫无边际的高原上,鹰独自在每个山谷寂寞地重复着相同的姿势:高飞或俯冲,藏人的岁月也在鹰的飞翔中变苍凉变悠远。此外,旱獭和鼠兔摇晃着肥硕的躯体流窜在花草之间,高原处处盎然勃勃生机。
我不知自己是怎样到达稻城的,康定-雅江-理塘-稻城,432公里的路途,我用去足足20年才得以走到目的地,短暂人生这样的行走显得过于冗长了一些。
而今,当我重新坐在电脑前企图用文字去记录稻城时,我便会惊异地发现自己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中去,我无法沉静下来面对排山倒海的往昔,我无法淡定的用记忆去触摸那海洋般密实众多的土地,二十年后,当我再次站在那座魂牵梦萦的小城中四顾张望时,我突然发现我依然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由康定出发400多公里的途中我只在反反复复忐忑的思考着同一个问题:我用掉二十年时间分别的地方究竟变成了怎样一番景象?直到我再次站在那条熟悉的丁字路口时,我依然为这问题困惑着。
越野车穿过桑堆河谷缓慢进入县城北郊时,夕阳正安静地给稻城涂抹着颜色,它缓慢绵长的动作如同一个唐卡画师,专注地把金粉倒入色盘中再细致地晕染到稻城的每个角落去,先是远方的藏房、飞鸟、屋顶的炊烟、接着是青杨林、稻城河、草地、花朵、牛羊和人们,视线触及的所有就这样依次慢慢变成了画卷,直到最后连我也在余晖的缓慢呼吸中一同被描入画里。
如果,记忆是有颜色的。
稻城应该是以这样的色泽出现于我脑海中的,那束厚重而玄秘的金色光芒如一轮小小的太阳跟随着我的脚步一刻不曾停留。
成年后我时常陷入深深的孤独中去,人声鼎沸、杯盘交错时节尤为严重,对于浮世,心总是沉疴难愈。彼时,那轮金色光芒如同太极中的阴阳鱼便会周而复始地照耀我蜷缩冰冷的心脏,更多时候我习惯用回忆美好时光来治疗伤痕,稻城便成了唯一适用的偏方。
越野车跨过河流驶向城西高处的草坡,傍河村如同一幅画卷安静地舒展在人眼前,身体在高处风光在低处时眼睛便可以自由地俯瞰世界,微风拂过密林顶端那茸茸的绿毡,层层绿波缓缓荡漾开去。夕阳懒懒穿过枝柯间,大地陷入魔幻般婆娑的光影交织中。我热爱的山河如旧,时光如旧,旧年在草地上翻滚嬉闹的孩子依旧……
亦或,记忆是有温度的。
我确定将稻城放置于我人生的任何阶段都是温暖的。黄昏的斜阳穿过东义区老瓦屋的窗棂照耀母亲的手,手指间水滴晶莹剔透金光灿烂,我等待被洗干净的小脑袋、窗外的瓜蔓、风中的儿歌,稻城河中的游鱼、水井边的洗菜盆、温泉边混浴的男女、学校、老师、同学、林中的秋千、家等等等等。
更多时候,记忆那张干瘪的海绵突然渗满水分无限地膨胀开来时,每个嫌隙就充满了若干相关的烙印,我的印记关联着稻城。分别若干年后在海拔3750米的高处我第一次回归,时光犒赏于我一幅金色的唐卡,不经意间我与同行的人们也在流光中变为了画里的某个细节,生动而明朗。
我安静下来,不再追究沿途的山水是否符合曾经的记忆,我惊讶于第一眼景致的饕餮,在“山谷口的开阔处”(稻城原名稻坝的藏语释义)的地方,稻城河遵循着我的记忆缓慢流向远方,那远方之下是时间给予我的关于一个城市往昔的全部,我企图怀揣着它们去向更远的远方。
写到此处我突然发现对于稻城我运用了大量与时间相关的词语,似乎我们都在时间的流逝中责怪着彼此的遗忘,于是我想停下来,或许以更加简单的方式回到这里,我们才能彼此原谅这姗姗来迟的相遇。
人生总是不断重复着两件事,出走与归来。这是两两相对着的两个方向,然而最终,我们却只能拿时间来证明它们是永远无法重合的两条平行线。“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车停靠在叫做云贵的酒店,终于有人在这样那样的介绍中认出了父亲的女儿我,相形于父亲我理所当然应该被人们的记忆忽略,毕竟十年与大半生的光阴永远无法相提并论。父母是跻身于这块土地最早的创业者,如同当年的牛仔们驾驭马车意气风发地奔向美国的西部荒原。
本世纪七十年代,一匹瘦削的老马,驮着年轻美丽的母亲来到陌生的雪域高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