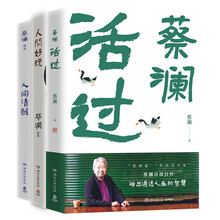第一章古人的宫殿
每个人的生命都像一封匿名邮寄的信件,我的信件上盖着三个邮戳:巴黎、伦敦和威尼斯。这是命运对我的安排,这样的安排常常发生在我不经意间,但并不是贸然而至。
威尼斯在它有限的空间里囊括着我在尘世的一生,它也处于虚无当中,介于胎儿的羊水与冥河的河水之间。
我感觉整个地球对我都没有任何魅力可言,威尼斯和圣马可广场除外,那里清真寺的地面倾斜鼓胀,好像并置的祷告地毯。因为我幼时婴儿房的墙上悬挂的一幅水彩画,我一向就知道圣马可广场这个地方:那是我父亲在1880年前后创作的大水彩画——画作使用了茶水墨、乌贼墨、中国墨——具有晚期浪漫主义风格,画中祭坛上灯光的红色穿透了投射下金色影子的拱门,夕阳照亮了铺着台布的讲道坛。我还从父亲那儿继承了一幅小油画,这是父亲以少有的敏锐眼光描绘的安康圣母教堂的阴天风景,这幅画一直在我身边。
“要在雨后欣赏威尼斯”,惠斯勒①反复说道。
沧桑过后,我回到威尼斯回顾自我。威尼斯在我的岁月中留下标记,就像柏油头的圆木在礁湖上设置路标,这些圆木只是众多的视点之一。威尼斯,并非我生命的全部,而是其中彼此没有联系的若干片段。水的涟漪渐渐散去,而我的皱纹却不会消失。
对于书写威尼斯的荒诞可笑,我一直无动于衷。
甚至是在伦敦和巴黎的至上权也化作记忆的时代,世界的神经枢纽成了那些野蛮地区:雅加达、西贡、加丹加①、金门,那时候的欧洲不再有人关注,唯有亚洲才排得上号。而威尼斯早就明白了这一切,它偏安一隅,其影响波及中国。应该是圣马可尽忠于马可波罗,而不是反过来。
在威尼斯,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上了在这个星球上的第一课,而在课堂上我什么也没学到。学校对我而言不过是一段长久的烦恼,我应得的惩戒使它更加烦闷。即便我的手指上沾满了墨水,脑袋里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那些书本,多么沉重啊!把纪西拉②的拉丁词典从香榭丽舍大街背到蒙梭就要把我这个城里人窄窄的双肩压碎了,况且对于那些没有每天早晨攀登古尔塞勒路的人们而言,蒙梭可以叫做平原了。我脚下的碎石路面无比坚硬,我已经想念威尼斯了。我曾听人称颂这座睡莲之城,那里的每一条街道都是塞纳河。
古典主义作家们并不跟我说话,他们的作品都是写给另一个世界的,是写给凡尔赛宫的朝臣或是学校老师的。在我们那些伟大作家的作品中,没有什么让我好奇,让我迷恋,让我愤慨的。施利曼①最近发掘出的金面具的阿特柔斯人②,与17世纪戴假发的阿特柔斯人,有什么关系呢?我的生活从《贝蕾尼斯》③开始!13岁我就爱上了《贝蕾尼斯》!我首先应当爱上一个喜欢拉辛的人,谁为我讲解拉辛,讲解这个女儿心男儿身的人?没有人为我解释那些词语的要旨,两个词中就有一个与今天的意思不一样。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误解:荣耀?国家利益?一位哭泣的国王?那些细微的区别,绝非孩童的玩具。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既温柔又粗暴呢?而莎士比亚的作品则截然相反,我可以毫不困难地理解他笔下的罪行和鬼魂。马塞尔·施沃布④和我父亲一起为莎拉·伯恩哈特⑤翻译了《哈姆雷特》,这个译本远比纪德的译本更有味道。
我曾经听他们在英语文字中寻找到古老的法语词,就好像在新近的临摹画作中发现文艺复兴以前的艺术家。莎士比亚的戏剧如同一场大型木偶剧,一切都不会四分五裂,而是和谐一致,实现超越。
我从未学过语法⑥,这没什么好夸耀的,只是我觉得如果我现在学习语法的话,我可能再也不知道如何写作了。眼睛和耳朵是我唯一的老师,尤其是我的双‘眼。好好写,与写得好是相反的。“没有足够的词汇来表达我所思索的内容……”:你不是在思考而是在寻找词语;应当让词语来追寻你,找到你。人们应该能够说出你的每一句话:“他跟他父亲长得一模一样。”一个作家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声音。
我年轻时代的哲学不过是一个悲惨精神病院的附属物。地理只丢给我一份海湾和岛屿的目录,一张最高峰和河流的清单,还有一份关于山峰的索引。每座山峰都贫瘠得如同月球上的山脉,好像从未有人在这些山上居住过。至于历史,那些人为划分的分期,了不起的“转折点”,还有对统治期的随意划分让我只能看见一些战役,或是一些注定要挑起新的战争的条约。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