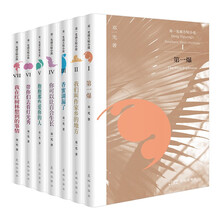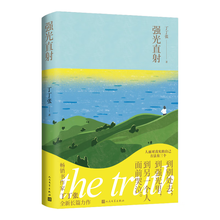那年我尚且是位勤工俭学的大学生,虽无须支付学费,但生活在巴黎,生活费也是笔不小的开销。
这一日天气晴好,我与几位同事坐在露天咖啡座里聊天。天气炎热,来来往往穿着暴露的美男靓女即是我们聊天的话题。
突然,一片阴影遮挡在我面前。阴影的主人很不客气地问我邮局在哪里,我头也不抬,目光继续追逐街上移动的美景,伸手遥遥一指,算是完成了回答。
阴影却不满意,坐了下来,对我说,嘿,你很不礼貌,不苛求你面带微笑,至少要讲句话吧。
我终于转头看她。这是一位很美丽的西欧女子,眼睛很大,栗黄鬈发,有几分漫画人物的风采。即使此时一副愤怒表情,也难掩她的姿色倾城。
我皱眉,答道,你既未说您好,又没讲对不起、打扰,我为什么要对你的不礼貌而礼貌?
我们两个,一个怒目,一个皱眉,互相盯着看了几十秒钟,情势一时紧张。法国人少有这种街头争吵,就连讲话声音都小,因此四周顾客紧张地看着我们,甚至有人拿出手机,考虑要不要请来警察。
对峙了一会儿后,她的唇开始上弯,眼睛也随之充满笑意,我也再忍不住,笑出了声。
她伸出手,说,我是Iciar,西班牙人,很高兴认识你。
我与她一握手,说,夏奈尔,法国人。
喏,这就是我与Iciar相识的过程,到今天已经有七年多。她现在已经回了西班牙,在一所学校当法语老师,工资蛮丰厚;一时兴起,还会搭夜班机来看我,与我狂欢一夜再坐飞机赶回去上课,下午回家倒头补睡——标准的西班牙人的作风。
喝完咖啡,我与同事回邮局上夜班,她呢,则来邮局面试。面试的结果,当然是OK。现代邮政业都已机械化,我们的工作,只是守在一排吵得要死的分拣机前,哪个信筐装满,我们即将它拖出来,贴上标签,丢上传送带。这实际上是一项需要体力与耐力的工作,我们的优雅与学识在这里根本毫无用处。
Iciar来上班时穿了一身紧身弹力牛仔衣,鬈发束起,再戴一双工装手套,腰间斜挂了一个简易包,里面装有巧克力与手机。行走之间,恰似《古墓丽影》中的女主角再现。
她极擅用外交手段,上班后的第三天,她即成功调班,与我上下班同时段且分到一组。从此,我的耳根不得清静,左耳要听机器噪音,右耳要听她诸多的离奇又荒诞的经历。
我被迫成为她的闺密,也同时成为邮局众多单身男士的公敌。
眨眼即到七月,巴黎几乎空城,而满街满巷皆被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占领——他们说着各种语言,拿着各种版本的地图,寻宝似的挖掘景点。
巴黎人要么跑到山上或海边的度假村消暑,要么去了这些游客的国家或地区,好像每个人都觉得风景总是别人家的好。许多商场、餐馆甚至医院都关门歇业,唯独邮局全年无休,一天运作二十四小时,以保证无论远近,国内信件两天内送至顾客手中。
大多同事也选择在此时休假,学生理所当然地申请全天制。这样我们可以多赚一些,邮局也不用请替代工人,双方皆大欢喜。
只是因为太多公司放假,邮局的工作量锐减,大半的时间我们坐在关闭的机器前喝饮料聊天,主管见了也当作没看见,有时也会坐下来和我们闲扯。
一旦闲暇即显得时光漫长,我们望着窗外骄阳,看它一寸一寸艰难地挪动脚步,恨不得帮它一把,一下子将它推去西边。
又一日无聊地看窗外艳阳,Iciar同我说,我们逃跑吧,出逃一周再回来上班?
我只当她在说笑,随口应了一声好。谁知第二天早晨,我在上班途中被她劫持,她拽着我去见她的家庭医生,要他给我们两个各开一张一周的病假单。
那位文质彬彬的医生得知我们在同一公司上班且同一班组,颇为难地皱眉搓手。Iciar提示医生,我们两个形影不离,整日私混在一起,同时患病完全有可能,不如写一种不打紧的传染病,要在家中静养。毕竟社保中心也不会为这一周的病假登门查证,况且黄金般的七八月,他们也都出了门去度假。她软磨硬蹭,将这位医德严谨的医生诱得终于犯了错,给了我们人手一份病假单。我们出门即将它们一联寄去公司,一联寄去社保中心,而后各自回家取行李。
到了宿舍,我却心血来潮,打电话给Iciar提议不如我们什么都不带,不带身份证,不带钱,不带手机,不带银行卡,只带一套换洗的衣服。
Iciar在电话中没有声息,我以为她不愿意,正想说放弃,她却很夸张地哇哦一声,说,你真有天才创意。
为了方便,我们都是T恤短裤,见了面互相检查包。我发现Iciar除了换洗衣物,还带了一条大裙子——真的好大,裙摆展开足有两米。
第一日天神与流星雨
我们从奥尔良门出城,十几分钟后即来到外环城,本想在那里拦顺风车,可是外环城车速等同高速,哪有车敢停下。我们只好穿越外环城线,进入与巴黎相邻的94省,在省级公路上拦车。
我们并未定方向,更无目的地。两人分站马路一边,伸出左手拇指,看哪边的车先停,我们就去哪个方向。结果我大胜,一位红衣女子停车让我上去,后座有一位小女孩抱着小熊睡得香沉。Iciar穿过马路跑过来,很不服气,申明她那边的车都满员,否则定是她胜。
她就是这种性格,什么事都喜欢与我比高低。待红衣女子问我们想去哪里,我们一时过于高兴,很欠思量地说,去你家。
这让红衣女子着了慌,以为路遇女劫匪,“嘎吱”即将车刹停。我马上做解释,并再三表明,我们不去她家,只是去她家的那个方向。
我的长相纯洁无害,Iciar更是一副讨喜模样。红衣女子终于又将我们相信,告诉我们她要去Troyes,父母家中。
Troyes是个有名的名牌打折村,像我们这样的时尚人物不可能不知道。Iciar的大眼睛先是一亮,而后她无奈地叹了口气,转头去看窗外飞掠的景物。
巴黎到Troyes,走高速大约一个半小时,但交通台说高速上因出行的人太多,今天塞了七百二十四公里的车龙。红衣女子走国家公路,用了近三个半小时。她说即使高速上不塞车,她也愿意这样走,虽时时有红灯,但可以穿过不同的市镇,有种在旅游的感觉;况且此时麦田正黄,夏花灿烂,沿途又有许多巨大的雪白电力风车矗立原野中,一路皆是好景,错过太可惜。
我们听得微笑,很赞同。这是一位很懂得享受生活的女子。
与她道别,我们也不进入打折村,直接去了停车场——身上分文没有,实在没有必要折磨自己,毕竟女人大多都是天生的购物狂。
停车场里已有许多购好物正欲离开的顾客,我们上前询问可否搭载我们一程。中年人让生活教育得谨慎多疑,都不太愿意。有一辆车来自25省,车主是两位年轻男孩,看似大学生的模样。听到我们的问询,他们主动招手道,来这里啦,去贝桑松吧。
果然没有猜错,这两位均是孔泰大学的学生,假期在LU饼干公司打工。今日是他们的休息日,他们结伴出来购物。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