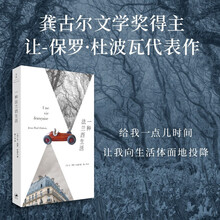我向德·多米尼克神父献上这个太灰、也可能太红的故事。
但是这些不纯的色彩,是儿童的血、冬天的雪、城市的乌烟瘴气搅混后,给它涂上的。
突然间,阿兰·罗贝尔看见一座城堡——他生平的第一座……可不是,在河的对岸,照在令其都显得渺远、高峻、壮丽的细尘般的阳光中,一座主塔、几堵雉堞、几座角楼,说不定还有“突廊”(虽然他并不知道什么叫突廊。)……哪家的骑士、什么样的马还会住在巴黎市中心呢?“我们快走吧,阿兰·罗贝尔?”押送的人有气无力地说。
清晨以来,四个钟点了;响过闹钟以后,经过荒凉的街道、车站、气味浑浊的车厢,他只是反反复复这句话:“我们快走吧,阿兰·罗贝尔!”“好啦!”押送的人又说了,“还没完哪?”他回转身,看到小孩文风不动,眉毛锁在一起,像船头的两个波涛,眼睛乌亮清澈,嘴唇微微张开,像要说话——不!像刚哭过!这个十一岁的男孩,眼皮从来不眨,在列车上两手插在口袋里,衣领往上翻,没有睡过一分钟,没有提过一个问题,这个小陌生人叫他感到怔忪。
“那边!”阿兰·罗贝尔问,还是一清早那种沙哑的声音,他举起手臂。(袖子太长,只露出两只手指。)“这是什么?“法院。过来吧!”“里面有什么?”“小偷、杀人犯……法官。哎,我们快走吧!”阿兰·罗贝尔马上联想到地下室的刑房、每层楼的绞刑架、穿红色套衣的刽子手、他们的手上……拖船一声尖叫把一切割断了。男孩跑到桥中心,赶上看到拖船钻人脚下的桥拱。他望见另一个孩子,跟他一样年纪,躺在一条驳船的后甲板,在几盆花和一只兔子笼之间。他们的目光无情意地一擦而过。“要是我也溜呢?”阿兰·罗贝尔想,肥长的袖管内拳头攥得紧紧的。
“你看!”押送的人已经跟了上来,“这是著名的巴黎一景:这里,法院……左边,商业法庭和市警察局……那边,在普济院后面,普济院是一家很古老的医院。”法庭、警察局、医院,这三个大人用的词给他建立了一个石头世界,小孩关在里面呼吸困难,感到腹中也空了。“哦!小船,躺着的孩子,已那么远了……”阿兰·罗贝尔抬起长满鬈发的头,凝视这个带着善意的微笑在说话的这个人:帽子、眼镜、风衣——浑然一体……一座道地的纪念像!他的手怎么还是热的呢?“花木市场,也是个有特色的地方,”那个人最后说。
孩子早已不在听他。从花木市场深处走出一条狗,朝他们奔来。
阿兰。罗贝尔没明白过来为什么心就怦怦跳。这条狗颈子伸得长长的,眼睛亮亮的,跨着灵活的小步子直往前跑,像船似的又盲目又固执。
在这闲人嘈杂的十字街头,走过这只孤独、没声响、行色匆匆的畜生,很触目,好像也只引起阿兰·罗贝尔的惊异。动物擦过他身边,没有放慢步子。狗的世界只限于鼻子前一条细细的气流。……它大跑了,张开嘴,舌头挂在外面。接着犹豫了一会,但没停步,像帆船要掉头。接着不顾来往车辆横穿过马路;法院门口站岗的警察,有一个开始注意它。
阿兰·罗贝尔发觉了,皱上眉头抿着嘴;这会儿干啦!他清楚听到自己的心跳,穿风衣的家伙怎么会没听见呢?狗在对面人行道上继续直线前进,像轻快地走在一条熟路上。在广场绕了一圈回到原地。这时停下步子,气咻咻的,头转向一边,又转向另一边,完全是垂死者的动作。阿兰·罗贝尔目不转睛盯着,发现狗没有带颈圈。
好一会儿,男孩忘了呼吸;这时深深吸了一口气,使他周身打了个寒颤。
“有什么事啦?”押送的人问,他正给他在讲沙漠中建立普济院的故事。
“没什么。”小孩声音沙沙地说。“圣路易①后来又怎么样?……”他要安静;孩子的安静,也就是当大人说话的时候。他刚明白这是条野狗,狗自己也刚发觉这一点;于是,他要安静。
“那么,在圣路易后……”畜生又朝反方向跑去。一条棕色白斑点的大狗,很瘦,全身是蓬松的浓毛——死期不远的老国王的华丽长袍。一架美妙的跑步机!“唷,”孩子希望,“该跑多久它会跑多久的!”但是不,狗刚才又停了下来,阿兰‘罗贝尔看清它站在那里四条腿发抖,接着有点屈了下来。它在哆嗦,还是风吹过它的皮毛?狗又突然走了,差不多从同一个地点穿过同一条马路。这次,一辆汽车险些把它轧着了;阿兰·罗贝尔举起胳膊,像要远远地阻止……狗弓着背,身子一起一伏的,露出卑怯的目光往后退。警察指指它,向他的两个同事做个手势。
“您说,”阿兰·罗贝尔没头没脑地问,“野狗会遇上什么?”“可是……这一点沾不上边!”另一个扶正眼睛架。(他正在讲巴黎圣堂②。)“会遇到什么?”“警察局把流落街头的狗抓来,关进狗房。”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