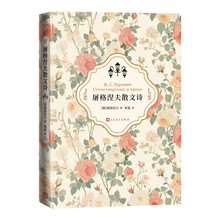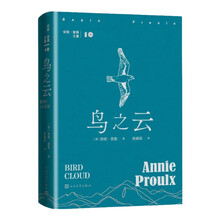1
在我生命中呈现出来的风景是由三股力量构成的,其中两股力量曾摧毁了世界的一半,但第三股力量却难以用肉眼察觉,它卑微而弱小,藏在离我胸口左上方一两寸的肋腔,像是只羞怯的小鸟。有时,在最不经意的瞬间,那小鸟突然醒来,抬起头欣喜地扑打着翅膀,这时我也把头仰起了,虽然只一刹那,我心里已经确知:爱与希望要比仇恨和愤怒强大得多。在超越我目力所及的地平线的远方,存在着一个顽强的、坚不可摧的生命,而最终胜利的,便是那生命。
第一股力量是阿道夫·希特勒,第二股力量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这两股力量使我的生命成为欧洲中部一个小国的历史缩影。那只小鸟,也就是第三股力量,帮我活下来向后人叙说我的故事。
过去的事情,我将它们像手风琴的琴片一样重重叠叠地折叠在心里。那些往事就像人们到国外旅游带回的一本明信片,小而精致,可是,只要将最上面的一张明信片的一只小角稍稍抽出一点,马上就有一条长长的、看不见尾巴的毒蛇逃出来,曲曲弯弯地爬着,将所有的相片都清楚地铺展在我的眼前。那些照片的图像在我的眼前久久地移动,轮廓变得愈来愈清晰,就像遥远的过去的某个瞬刻被楔进了我体内的时钟里。时钟停顿了下来,秒针轻轻朝前一滑,然后脱离了这个不可代替的、再不能重返的现在。
居住布拉格的犹太人被大批流放,最早发生在1941年的秋天,那时战争已经爆发两年了。运载流放犯的火车在10月份离开布拉格城,那时,我们都不知道火车要开到哪里,只知道传下来命令,让大家带几天的干粮和生活必需品,不许带其他东西,到市博展会大厅报到。 那天清早起床时,见母亲偎在窗旁。她转过身来,用纤细得像个女孩的声音对我说:“瞧,天快要亮了。我还以为太阳今天不会升起呢。”
博展会的里面就像中世纪的疯人院,除了那些最能保持冷静的,似乎其他人都在精神崩溃的边缘。有几个病重的人被担架抬进来,死在博展馆里。一个名叫陶希斯的太太发了疯,把她的假牙从嘴里掏出,朝当地负责长官福德勒狠狠地扔过去。几个婴儿和年幼的小孩不住地啼哭。在我父母的一侧,一个矮胖的秃顶男人坐在他的皮箱上,不顾周围的嘈杂和喧闹,径自拉着一支小提琴曲子。那是贝多芬的D大调协奏曲,他重复地拉,一遍又一遍。
我在数千名难民中漫无目的地走着,寻找着熟悉的面孔。我就是在那时和他头次见面的,直至今天,我仍然认为他是我见到过的最英俊的男子。他安详地坐在一只挂着银锁栓的黑木箱子上,腰板挺得笔直,白衬衫外面套着一件黑外套,系着一条灰色的领带,头上戴着黑色的宽沿帽。他长着一对灰眼睛,灰白的小胡须修得齐齐整整,优雅修长的两只手交叉地握在一把雨伞的木柄上。雨伞束得很紧,细得就跟牙签一样。周围一片混乱,人们都穿着毛衣和滑雪外套,脚上穿着厚重的靴子,他的那套穿戴,明显地与环境很不协调,仿佛是赤裸着身体在那里坐着。
我看到他的模样,吃了一惊,不由地停下了脚步。他微笑地站起来,朝我鞠了一躬后,在木箱上让出一个空位邀我在他身旁坐下。他早先是个古典哲学教授,在维也纳教书,纳粹占据了维也纳后逃到了布拉格,没想到德国人在这里追上了他。我问他,既然不知道旅途的目的地,您干嘛不穿实用些的衣服呢?他回答,一向都是这样的穿着,不愿因为环境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习惯。他说,不管如何,在这种无答案的困境中,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平静与沉着。接着,他向我讲开了古典文学和古罗马故事,我专注地听着,心中充满了喜悦。从那时起,我一有机会就去找他,每次见到我,他也总是微笑着,客气地欢迎我,很愉快的样子。
两天后我们登上了火车。虽然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们经过无数次疲惫不堪的迁徙,因为那是流放中的第一次迁徙,觉得还是最令人恐怖的一次。如果真的像人们所说的万事起头难,那么最初的磨难和困苦,也是最令人感到悲悯的。那时,我们还没有习惯听枪响,没有习惯听痛苦的呻吟,没有习惯忍受口渴饥饿,更别说在塞得满满的牲口列车厢里令人窒息的空气了。
P1-3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