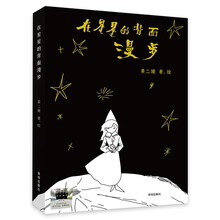大海处于平潮,海面光滑如镜,在多云的灰色天空下犹如丝绸。几天以来,雷雨远去,逃向外海。今天这里不会下雨,外海上有雨。上午十点钟。这里的天气将会晴朗。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因为有微风从陆地吹来,海面上散布着大片大片大小各异的纯净亮光,这光线有时呈黄色,给沙石与城市染上色彩。远处是昂蒂费的那一列黑色。今天早上又有了一艘白色大货船。饥饿再一次扑向非洲,这一次是乌干达。电视播出了乌干达的几个图像。电视总是十分真实地播送饥饿的图像。一些摄像队出发去拍摄,这样我们就看见他们在行动。我觉得看胜于听。于是我们瞧着乌干达,我们在乌干达身上瞧着我们自己,我们在饥饿里瞧着我们自己。当然这些人在饥饿的旅途上已经走得很远,但我们仍能认出他们,我们经历过这些,我们见过越南、纳粹集中营,我曾在十七天里奄奄一息地躺在巴黎的房间里看着这些。这一次他们在土地绝对贫瘠化的最后旅途上比别人走得更远,土地表层的生命薄膜正一点一点地消失。我们知道最初将是缺水,然后是植物变得稀少,动物变得稀少,最后完全结束,只有全体剩余的人类轻柔的绝望,我称之为幸福。这些人已经十分相似了。在这里,身体像木板、像手一样单薄。眼泪已经消失。恐惧已经消失。还有笑声,还有思想上的绝望都已消失。我们怀着激情瞧着他们。人的这种最后外形,人的最后状态,这就是我们。他们只剩下知觉和听力,听到他们身上发生的事,仿佛他们仍在童年,死亡的童年,没有话语。和那个注视的孩子一样,他们正在死去。大多数人仍然在走,当然走得很慢,但他们终于将身体挪到了分发点,去领取加有维他命的粥,挪到了水池旁。他们终于将身体挪到了阴凉处,有些人做到了。饥荒区的温度是命中注定的四十度。家庭关系再也看不到了。女人们仍旧抱着婴儿,但能走的孩子靠自己。他们如同流放者,彼此相似,惊人地类似。在皮肤的外壳下是同样的骨架,同样的手,同样的脸,再只有这最后的余渣,而它在最激进的抽象化中被称作生命。再没有儿童,再没有老人,再没有年龄,眼光是一样的,茫然,瞧着摄影机和瞧着地面一样。这是些泥人,最初的沙漠上的泥人,最后的沙漠上的泥人。有始有终。它们并不多样化,没有任何个性,而是彼此黏合在一起,如洛林高地的泥人,拉斯科在干旱期形成的泥人,也许还有戈兰高地的泥人,太巴列湖岸的泥人,他们共同期待丰富的雨,成群的鹿,天赐的食物。他们赤身露体。他们唯一的财产是那个饭盒,它或是罐头盒或是能盛稀粥和水的小容器。面对乌干达我脑子里空空的。同样,当我从集中营归来时,那时我的脑子也是空空的。如果说我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我无力表述。我看见。我躲避那些人,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或看到这些东西以后就已经知道思考,该想什么,该说什么,该如何下结论。应该提防这些人,因为他们首先想失去这个知识,用速成的解析使它远离自己;必须躲避这些人,他们谈论补救办法和原因,他们在音乐里谈音乐,当别人演奏大提琴组曲时,他们谈论巴赫,当别人谈到上帝时,他们谈论宗教。孩子还在。他在那里。黑夜在多变的灰色天空下过去了。今天早上天空蓝得发亮,太阳还在山丘后面。孩子走过木板路。海滩上几乎还没有人,只有几位散步者,他们转头瞧瞧走路的孩子。孩子一面走一面玩小球,扔起来又抓住。我盯着他直到他消失在海滩上的酒吧兼烟店后面。然后我闭上眼睛,在内心寻找那无边的灰色目光。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