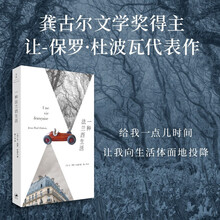是她关上了房门。
又高又瘦、两鬓灰白的男人在房屋尽里头看着他们走进来。
说话的是女人。
“这里是阿巴恩家吗?”他没有回答。
“这里是?”她等待着。他没有回答。
她个子矮小,穿着几件黑色长袍。他,中等身材,穿一件浅色毛皮外套。
“我是萨巴娜,”她说道,“他是大卫。我们是本地人,施塔特人。”男人朝他们缓步走来。他对他们微笑。
“脱掉你们的外衣吧,”他说,“请坐。”他们没有回应。他们仍旧站在大门边。
他们也没有看他。
男人走近他们。
“我们认识。”他说道。
他们没有回答,也没有动弹。
男人现在已离得很近,可以看清楚他们。他看见了:他们没有目光。
她又开始说话。
“我们找阿巴恩。我陪大卫来。我们是施塔特村的。,,她的眼睛非常大,直盯着男人。大卫的眼睛被厚厚的眼皮遮住,看不见。
“我就是阿巴恩。”她没有动。她问道:“就是大伙儿叫犹太人的那个人?”“是的。”“半年前来到施塔特的。”“没错。”“就一个人。”“正是。你们没有搞错。”她看了看周围:有三间房。
墙壁光秃秃的。里里外外,家徒四壁。房舍一面朝着冰冻得发白的道路,另一面朝着一座蓊蓊郁郁的大龙园。
她的视线又转回到犹太人身上。
“这是犹太人的住宅吗?”“是的。”大花园里,有狗在叫。
大卫转头,朝大花园的方向望过去。
狗叫声停止了。
重又静默下来。大卫不再朝大花园看。
“你们是格林戈派来的?”她回答说:“对。他说他晚些时候来。”他们不说话了,三个人都站着。犹太人走近大卫。
“你认出我了吗?”大卫往地上看。她回答:“他认出你了。”“你是泥瓦匠大卫。”她答道:“是他。”“我认出他了。”犹太人说道。
大卫仍愣愣地往地上看。
“他变成瞎子了。”犹太人说。
他们没有回答。
“他变成聋子了。”他们没有回答。
犹太人走近大卫。
“你在怕什么?”大卫的视线移到犹太人脸上,然后再回到地上。
“你怕什么,大卫?”犹太人问道。
他声音温和得竞让垂下的眼皮颤抖起来。她回答说:“没什么。他属于格林戈党。”犹太人沉默。她问道:“你难道不明白?”“大卫的事儿我原来不知道。”犹太人说。
萨巴娜第一次注视他。他则注视着大卫。
“别的事儿,你知道吗?’’“知道。”犹太人似乎感到疲倦突然朝他袭来。
“你一直在等我们吗?’’“是的。”他朝大卫迈了一步。大卫没有后退。他再往他身边挪。
他抬起手。他触摸大卫的眼睛。他说:“你已经变成瞎子了。”大卫往后一跳。他叫道:“别碰我!”大卫抬起他那被水泥弄得肿胀龟裂的手,他在保护自己的脸,他还在ⅡL{。
“别再这么干了!”她瞧瞧这个,再瞧瞧那个,没有动。她没有说话。
犹太人离开大卫。他回到他们进门时所待的位置,在桌旁重新坐下。
“你们别怕,”他说,“你们什么危险也没有。
脱掉你们的外衣吧。坐下。别走了。”他们仍保持原样,在大门附近站得笔直,浑身绷得紧紧的。
她平静地说:“你不明白,我们是来看守你的。”“那就看守我吧。”“你别设法逃走!”“我不设法逃走。”“别费那个劲儿。”大卫不吭一声。萨巴娜向大卫指了指犹太人。她告诉他刚才与犹太人间的对话。
“他知道设法逃走也白费劲儿。”“我知道。”犹太人说。
还是萨巴娜首先脱掉了外衣。她将外衣放在门边的地上。她帮助大卫脱掉他的外衣。
大卫的腰上挎着武器。
他们俩坐下。萨巴娜把一把安乐椅递给大卫,她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
犹太人保持沉默。
她直起身往外看。她观察着道路、大花园、寒冷。一切都沐浴在同样强烈的光线里,里边,外边。还没有什么被点燃过。她看看坐在桌子旁边的那个人。
“咱们等着天亮吧!”他说。
萨巴娜的眼睛是蓝色的,又深又蓝。
“你是萨巴娜。”“是的。”狗在黑黢黢的大花园里叫。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