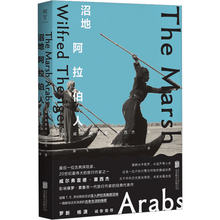直到今天,沃尔夫海姆的一些居民还坚持说,还没听到出租车进村的引擎声,他们就先听到了后座三个婴儿的哭声。出租车停在了拿破仑街一号医生的老房子前,村里的女人们立即放下擦洗前门廊的活儿,男人们走出特米纽斯咖啡馆,手里还握着啤酒瓶,女孩子们也不玩跳房子了,而在村里的广场上,高个米克斯丢了球,被先天聋孩冈瑟·韦伯接住,后者回传,从面包店老板的儿子塞佩眼前经过,塞佩的眼睛却正看着另外的地方。那是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三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钟楼里的钟敲了三下。
乘客下了出租车,所有人立即注意到了他的火红色的须发。
虔诚的基督徒贝尔纳黛特·李卜克内西匆忙画了个十字,也是这条街上,隔着几座房子里的年长的朱丽叶·布莱洛一下子捂住了嘴巴,喃喃道:“我的天哪,跟他父亲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这个比利时小村庄靠近三国交界处,它一边是荷兰的法尔斯,另一边是德国的亚琛,在它的全部历史上,都受到这二者的强力牵制。早在三个月之前,村民们就得知霍普医生即将返乡的消息。从奥伊彭的罗纳德公证处来了一个瘦巴巴的职员,到这座荒弃的房子前,搬走了那块发黄的“出租”牌子。他还告诉住在街对面的伊尔玛·努斯鲍姆,医生打算回沃尔夫海姆。这名职员并不知道更多的细节,甚至不能告诉她日期。
在离开近二十年后维克多·霍普要回到沃尔夫海姆,村民们觉得非常奇怪。关于他,大家所听到的最后一个消息是,他在波恩行医,不过这个消息可有些年头了。于是人们对他的返乡提出各种猜想。这个说他失业了,那个说他欠了一屁股债跑回来了;阿尔伯特街的弗洛伦特·科伊宁认为他回来不过是整修下房子,再把它卖掉,而伊尔玛·努斯鲍姆则暗示,医生有可能现在有家了,不想在城市里奔波忙碌。事实证明,伊尔玛的爆料最接近真相,尽管她第一个承认她跟其他人一样震惊,当她发现霍普医生现在成了仅有几周大的畸形三胞胎的父亲时。
那天下午,是高个米克斯发现了这件令人不安的事情。出租车司机下车,去帮维克多·霍普打开上了锈的大门,高个米克斯被不间断的尖叫声吸引,偷偷地溜到车窗那儿朝里面窥视。他往后座上看了一眼,这个瘦得皮包骨的男孩竟然吓得立马晕了过去。他也因此成了医生的第一个病人。医生突然打了他几记耳光,让他恢复了知觉。高个米克斯睁开眼睛,眨了眨,看看医生,看看车子,赶紧爬起来,跑回他的朋友身边,一次也没回头看。他还是有点腿软,于是把一只胳膊搭在他同学罗伯特·舍瓦利耶厚实的肩膀上——他们两个都是四年级,另一只胳膊垂在尤利乌斯·罗森博姆的左肩上。后者比他小三岁,矮两个头。
“你看见什么了,兰奇?”面包店老板的儿子塞佩问。他站在几个朋友的对面,皮球塞在胳膊下,脸朝着聋子冈瑟·韦伯,以便冈瑟能看懂他说的话。
“他们……”高个米克斯一开口,脸刷的一下变得惨白,话也说不下去了。
“哎呀,别那么没用!”罗伯特·舍瓦利耶用肩捅了米克斯一下。“对了,你说‘他们’是什么意思?难道那儿不止一个?”
“三个。他们有三个。”高个米克斯答道,同时伸出三根细长的手指。
“仨女孩?”冈瑟咧着嘴笑着问道。
“我不知道,”高个米克斯说,“不过我看见……”他蹲下来,眼睛扫了一眼霍普医生和出租车司机的方向,他们俩还在开那两扇门。他示意四个伙伴靠近点。
“他们的头,”他慢慢地说,“他们的头是裂开的。”他伸出右手,飞快地比划了一个向下切开的手势,从额头到鼻子,一直切到下巴底儿。“劈开!”他说。
冈瑟和塞佩吓得往后退了一步,而罗伯特和尤利乌斯则目不转睛地盯着高个米克斯那比例失调的小脑袋,仿佛它也有可能随时裂开。
“我发誓。你能看到那条缝一直延伸到脖子那里。这还不算什么,我向上帝发誓,你甚至能看见他们的脑子。”
“他们的啥?”冈瑟追问道。
“脑一子!”高个米克斯一边重复,一边用食指轻轻敲敲聋孩的额头。
“太恶心了!”冈瑟惊呼一声。
“他们是什么样子?”罗伯特问道。
“像一颗胡桃,就是大得多,也更苗条些。”
“耶稣啊!”尤利乌斯发着抖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