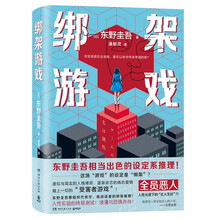情势已濒于荒唐的境地。他还从未遭遇过如此怪异的倒霉处境。他甚至揉了揉眼睛,咬了咬嘴唇,想要说服自己几个小时以来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一切确确实实只不过是场噩梦而已。
可是非也,他就在那儿,面对着这个根本不像入口的入口,站在与任何一家企业均无共同之处的企业围墙前,旁边就是与常规的安保处截然不同的安保处,他牙齿打颤,湿气浸到了骨子里,此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雪停了之后,雨水又蓄势而来,反复击打着他的脑门,无疑又为他麻木冻僵的状态雪上加霜。
他拖着手提箱,而不是拎着。里面已不再是衣服,而是石头、铁块、钢锭、花岗岩块。每走一步,他就会发出呼哧呼哧声,就像有人挤海绵时发出的那种声音。人行道已成一片泥潭。他的身体时不时地摔倒在一望无际的水洼里,不过,他也没什么好感到吃惊的了。可他忽然想起——j塞又让他燃起了希望——他在这么涉水而行的时候,曾注意到某条马路,就在他的右侧,他回想起就在他的右侧,但这样的征兆又能帮上他什么忙呢,他注意到有块发亮的招牌,他确信那是块酒店的招牌,可这时他又觉得没有把握,因为他并不准备用自己的性命去打这个赌。酒店,市郊肯定会有酒店,在嘈杂的远郊地区,高速公路网履行着自身的职能,在快速通道上清空繁忙的车流,施行性命攸关的放血疗法,将宿命和生命相隔而开。但此时此刻,靠步行去那儿,并不是问题所在。首先是,去哪儿?严格说来,他一无所知。
他万万没料到其实一个简单至极的动作就能让他摆脱如此尴尬的境地,如若当天早上离开家门前他想着给手机充电,这个时候他早已经睡在了暖和的床上,听着雨点敲击酒店的屋顶。他只要打电话问询一下就能毫不费力地找到一家酒店。可这小东西已完全瘫痪,毫无用处,在把手提箱从左手换到右手或右手换左手的时候,他有时还能感觉到雨衣兜里的那只手机,这让他觉得自己简直是太疏忽,太愚蠢了。
现在会是几点了?他没敢看手表。他已精疲力竭,浑身冻僵。他的喷嚏打得足有三米远,鼻子淌下了鼻涕,就像温水龙头打开后,出了故障,怎么拧都拧不紧。虽然如此,他难道就会愿意退而求其次,像那些流浪汉那样睡在车站的长凳上吗?再说了,他回想起以前车站晚上都是大门紧锁的,就是为了不让那儿变成宿合,况且,过了这么多年,公共区域的凳子设计成了那样,根本没法让人在上面挺直身体。
他漫无目的地走着,不辨东西。他经过了十字路口,沿着建筑物走去,穿过了窗户漆黑一片的独栋别墅区,看来这座城市没一个人是醒着的。没有一辆交通工具在马路上驶过。没有汽车。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