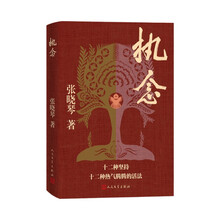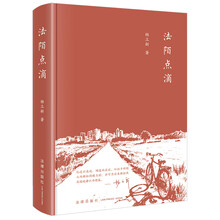穿火焰山而过的吐峪沟,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为“走不通的路”。如今,因有公路从旁边的山上盘旋而过,这个两千万年前形成的峡谷今天已很少有人再走了。
8月初当我们一拨人从公路下到峡谷中时,似乎就跌入了千万年前的时空隧道。峡谷深两百多米,层层黄沙土垒起的崖壁寸草不生,谷底中间河水蜿蜒而过,就连河边稀少而坚硬的植物也有着远古的色彩。
我们将随着河水,穿过这个峡谷,到达火焰山南麓的吐峪沟村。
这条河三四米宽,水流非常湍急。据说,河水是由天山北面的积雪融化而成的,它穿过火焰山,流向库木塔格沙漠。
身强力壮的男孩在前面探路,我们排成一列牵着绳子走,绳子成了将每个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成了我们的路。为了找到可以继续前行的路,我们不断地涉水再涉水,很多时候,河水甚至淹到了我们的腰。
强烈的阳光和复杂的路况迫使大家都低着头专注地赶路。有时,河水显得凶猛而深不可测,让人难以接近,大家只有向崖壁上攀援。
崖壁是一层层的浮土。脚一落上去,黄色的沙土就哗啦啦地流向谷底。
牵着绳子,渡河、攀山、走过低矮稀疏的灌木,我们互相搀扶,不言语,却多了共同行走的默契,似乎行走在这古老峡谷中的我们也回到了人与人最原始的情感中,面对着神秘莫测的大自然,互相帮助,共同寻找到达美丽绿洲的路。
据领队说,今年水量比往年都要大,因此以往可以走的道路,这次也变得扑朔迷离难以发现了。我们行进得很辛苦,也很慢。下午6点多时,渡过多个急流险滩,水位开始下降,我们索性趟着水走。脚下河底的淤泥,不断地“吃”住我们的鞋。岸边的植被也渐渐多起来,峡谷开始慢慢变得湿润开阔,显得温婉秀美起来。
岸边隐约出现了一条小路,离开温缓的水,我们上了岸,岸边的老桑树上结满了无人采摘的桑葚。
吐峪沟千佛洞在峡谷的出口处。远望去,对面黄色的峭壁上散布着石窟,在几乎无路可及的崖壁上,让人惊讶为什么当年会有人在这里凿洞绘下他们的信仰。
资料上说,吐峪沟佛教石窟是高昌故城文明的一部分,于十六国北凉统治时期兴建,并且在其后的几百年都保持着佛教圣地的地位,当时的佛寺和禅院密集,香火不断。
1200年后,15世纪,伊斯兰教进入东疆,严禁偶像崇拜的伊斯兰教视佛寺里的拜像行为为魔鬼行为,西域佛教石窟难逃一劫,吐峪沟石窟也因此遭到致命打击。
又过了700年,19世纪初,德国探险家格伦维德尔与勒考克,从这里刮走了最精美的壁画,拿走了沟东一间密室里满满两麻袋的文书和“惊人的刺绣品”,加上地震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如今,这里的多数洞窟都已经破败。
即使这样,在幽暗的洞窟里,透过玻璃看到那残损的佛像壁画时,我还是大吃了一惊。
佛像的头部尽管都已被刮去,但从余下的部分仍然可以看到那流畅干净的线条、淡雅明快的颜色及他们优美的姿态和飘逸的衣裳,看着他们,我不禁对那被刮去头像的面容和表情浮想联翩起来。
出了峡谷,是一个维吾尔族村庄,我们顺着小路仿佛直接走进了一户人家。宽敞的院落里,一棵古老的桑树增加了阴凉和惬意。黄黏土垒成的房子高大漂亮,据说这些古老民居,最久的已有四五百年历史。玩耍着的小孩、闲坐的老人、卖饮料的年轻妇女……这里真是一个古朴而恬静的村庄。
这个村庄有着所有远行者深藏于内心的家才有的亍静和温暖,真想就这样留下来。入夜后的村庄,应该更为宁静吧?村前的高坡上是著名的霍加木麻扎和村民的墓地。相传穆罕默德的弟子叶木乃哈等5人来中国传教东行至吐鲁番时,当地的一位牧羊人听其言成为中国的第一个信徒。他带着牧羊犬跟随圣人进入一个山洞听经,从此再也没有出来。它是伊斯兰教的七大圣地之一,被称为中国的“麦加”。在接近傍晚的金色阳光下,黄泥土垒成的古墓显得荒凉而神秘。
晚上10点,我们完成了穿越。在千年前的峡谷、佛窟、村落中,我们如同河水匆匆而过。但这山谷,有着驻留时间的魔力,我们这一天的记忆想必也会保存在这个古老的峡谷中。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