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村庄
村庄注定是属于父亲一个人的。他虔诚地守候在那里,像个称职的稻草人,守护着清香四溢的田野。而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或者学习;他的妻子也在异乡,为支撑这个家而辛勤打工。一家四口,竟分作四处。
一个人的村庄,总会显得孤寂,尤其是在漆黑的夜里。我不难想象如此的景象:田野里传来青蛙的“呱呱”声,凉风透过薄薄的窗纱送进屋来,没有人说话的声音,只有父亲日渐苍
老的呼吸和咳嗽,在老屋破败的四壁间来回游走。幸好,有看不完的书和报纸陪伴着父亲,有演绎别人的悲欢离合的电视剧感染着父亲,还有一只刚领养的小花猫也善解人意地周旋于父亲的脚前脚后。如果没有这些,漫长的日夜,我的父亲一个人该如何度过?我想,父亲或许还会感到孤独凄清,但却无可奈何,因为我们都在为我们所谓的理想而忙碌着,母亲更是为了我们,忘记了她的年龄。
父亲明显地老了,他一个人留守在乡下的家中,让我们越来越放心不下。我和母亲一般一个多月回家一次,看看父亲生活得怎样。母亲在忙着收拾清洗的同时,总不忘数落父亲的脏和“懒惰”,而我总替站在一旁微笑的父亲鸣不平:“一个仿佛单身的男人,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母亲便低头不再言语。其实我心里清楚:最放心不下父亲的,恐怕还是母亲吧。
我刚租了房子,便迫不及待地要父亲上来看看。于是,父亲第二天赶最早的一班车抵达了这个城市,那时我还在梦中。父亲带来满满的一瓶香油和家中所有的鸡蛋,我想起我曾在电话中不经意说过“这儿的香油难买”、“这儿的鸡蛋不新鲜”。父亲急着要走,我挽留了,并亲自下厨做了几样小菜,与父亲对饮几杯。父亲说房子很好,住起来肯定很舒服。我说这儿比乡下那老屋要好多了,父亲若有所思地笑了。
然而,父亲终究还是要回去的,回到那曾经淳朴的乡村去。在他上车的刹那,我突然想:当初父亲告别城市被下放到农村去的时候,怀着怎样的心情?我一直弄不明白:是父亲选择了这个叫“罗岭”的村庄,还是村庄包容了父亲坎坷不幸的一生?
鱼,飘在空中
很长时间了,我的脑海里总浮现出这么一句生动莫名的话,仿佛一条顽固而狡黠的鱼,时不时地钻出水面,似是引诱,又像是提醒,告诉我这样的一个真相:曾经或者将来,鱼,飘在空中。
飘在空中的鱼,是从母亲的竹篮里逃脱的那一条吗?从水里直接飞升到空中,再在空中完成难度高超的自由转体,像一只灵巧异常的风筝。我曾见过无数的风筝,挂在十月的高压线上,它们在春天里逃跑未遂。我也曾见过无数的鱼,它们都能侥幸地从渔网和我们的口中逃脱吗?更多的恐怕是成为鱼缸里供我们欣赏的活物,或是填了我们胃的狭小的一角了吧。我曾经满怀深情地描写过死去的它们:
鱼死在水里,肚皮朝上。
我从湖边经过,从它的身旁经过,它曾经是一尾活蹦乱跳的鱼,现在却是一具尸体。幸运的是,它最终死在水的怀里,水是鱼的情人,它应该感到幸福。
我不知道,这条鱼,是否从不远的老家游来,从母亲的竹篮里逃脱,选择在这里死去。
我准确地向它扔了一颗石子。石子很快沉了下去,浮起来的却是长久的思念。我想起跟鱼关系最密切的我的母亲。她在乡下日复一日地卖鱼。她对鱼充满感情。她的鱼从不轻易死去。
我能感受到的每个相似的冬天,都渗透着刺骨的寒意,和阵阵逶迤而来的鱼腥的气息。昏暗中的清晨,最先看见的是已坐起身的母亲,而在她看不见的几十里之外的养鱼场里,无数条鱼也在整装待发了。母亲把手伸进冰冷的水里,整个冬天便因此而奠定寒冷的基调。
母亲的鱼一个挨一个地匍匐在地上,母亲也就蹲在鱼的身旁。蹲得久了,母亲就随意地抬起头来,看来来往往的过路人,也只是随意地看。街道实在是太小了,跟大城市没法比。母亲是去过首都北京的,人多得就像整筐整筐的鱼。现在回想起来,我和母亲都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一向安分守己,谨小慎微的母亲,怎么敢在北京的许多街道上兜售空白的黄色录像带呢?母亲知道那是犯法的事,她也曾为此被便衣警察带到派出所,两次。有一次,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把她关在一间封闭的小房间里,手被铐在固定的桌脚上。夜深了,他们都去吃夜宵,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坐在黑漆漆的夜里,挨着饿。母亲并没有告诉那个年轻的警察,她有两个儿子,和他一般大,都在读大学,为了高昂的学费,她铤而走险。后来,母亲跟我们说起这些的时候,也总是轻描淡写的,就像是在天黑之前去了一趟菜地,顺便割了点儿韭菜而已。就在今年七月,我第一次去了北京。站在陌生的胡同街头,首先想到的便是若干年前我的母亲就是站在这样的地方左顾右盼,小心翼翼。我痴痴地立在那里,想象着母亲那谨慎卑微的笑脸,直想哭。
母亲拿起塑料瓶,不时地给鱼洒点水。街上的人越来越少了。浙江义乌的深夜好像也只有这么少的人。那一年,母亲跟老家的一对夫妇到那里打工,洗盘子,洗碗,洗菜,收拾里外。最让母亲难受的,是连续地熬夜。她们必须等,一直等那些从酒吧舞厅里散场的人,到她们那里吃点儿馄饨、水饺。母亲那时已经有四十多了。她的脚和胳膊都浮肿了。母亲累到极点的时候,就想家里的男人,想两个儿子,想着想着,就一个人偷偷地哭。坚持了大半年,母亲终于还是回来了。转来转去,还是卖鱼好啊,一回来,母亲就对父亲说。
在外奔波多年之后,母亲又重操旧业了,仿佛是一条漏网之鱼,在城市的大江大海中艰难游渡之后,最终又回归到乡村的小河小溪里。有时候,我喜欢胡思乱想,常常在心里完成这样的自问自答:为什么母亲的鱼从不会轻易死去?那是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鱼,就是她的第三个孩子。有一天从市里回来,远远地望见鱼市上的母亲,蹲在那里,就像是一条失去光泽的鱼。我能料想到母亲会继续这样的与鱼为伴的生活,却无法预料,是否有一天,我也会走出她以及村庄的视线,像一尾柔软的鱼,从她的竹篮里获得新生,或在寻找新生的途中悄然死去。
波纹层起,水藻繁盛,白色的鱼浮在其间若隐若现,然而我却能轻而易举地提起一条又一条鱼来。只是那一夜的梦里,风很大,鱼儿很小。咬在鱼钩上的轻飘飘的小鱼,我散乱的衣裳,塘埂上齐膝的野草,以及来寻我回家的母亲的发梢,都一起飘向我身后倾斜的天空。
花儿,花儿
是的,我决定要写一写那些花儿,虽然她们看不见,也听不见,但我还是要写一写我所看见听见想见的她们。此刻,她们正在开放。她们正在美丽。她们和我一样,正在年轻。
1996年的春风吹拂着田野、道路以及那个逆风骑车的少年,那时候的我比现在更加年轻,而所有年少的孩子都和风一样瘦弱,敏感,轻飘,但也像26式自行车的车轮,暗藏着继续延伸的未知希望,和不断向前滚动的余地。当我推着跟自己一般高的自行车出门的时候,我不会知道路上将要发生的一切,我只是为了省下从家到学校来回的车费,四块钱的车费可以好好地吃上几顿,而吃于我又是多么重要。这也就意味着我要从罗岭出发,穿过十五里外的练潭,再进入三十里外的双港,抵达终点。我给自己限定了时间,一个小时。所以,我只能低着头,靠着路边,狠劲地踩。而当我有气无力地抬起头,朝前方张望,便意外地发现了她们,那些金黄的花朵,那些与乡村贴得最近的平民的花朵,大片大片的,铺张得让人有些诧异,那些吹着我的风也正轻吹着她们。她们有着共同的朴素的一个名字,也都有着相似的腰身,高度,甚至面孔,而看那倾斜的神情好像也正等待着被风吹动,或是被像我一样的少年无意地凝望。我不得不把车停下来,立定在那里。我永远记得那个少年惊喜而迷惑的眼神,在她们中间肆无忌惮地穿行,沉沦,享受着无边的色彩和芬芳。现在想来,或许就是那一瞬间的凝望,让我遭遇了从未发现过的美,并由此而滑行到许多年后或深或浅的文字之中。
那是一个无法躲避的青涩的年纪,那是一群注定相逢并且值得留恋的花儿。
三月了,那些花儿又如期开放。金黄覆盖田野,势不可当,铺向遥远。池塘边,水沟旁,田埂上,东一簇,西一垄,到处都是开得正烈的她们。那点缀在花儿间的粉红的桃花,那桃花深处吃草的两头黄牛,以及骑在牛背上东张西望的乌鸦,还有那同样金黄的阳光,照耀田野,照耀人们的眼。我,那个曾经的少年,斜倚在3路公交车的后座上,望着窗外,窗外是大片大片的金黄,迷蒙而恍惚,时间的倏忽仿佛故意制造了这样的时空错觉。忽然就想起2001年的那个三月,也是在这样的车上,也是如此的姿势,望着窗外,一样的是窗外的她们,不一样的是欣赏她们的眼神和心情吧。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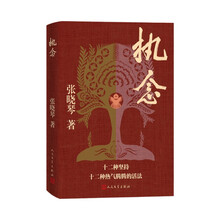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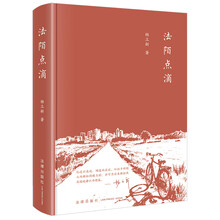
作为走出乡土的江飞,总是眷顾他的“罗岭”,在现代化的现实语境中,他以真情实感,以诗情画意,传递着自己与众不同的心跳、脉动和对故乡的感激,同时也呈现给我们一个贫瘠、落后的故土全部的温暖、苦痛和感伤。
——童庆炳(著名文艺理论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飞对故乡与亲人的书写,对生活与生命的体悟,都充溢着浓郁的诗意思索与“无处还乡”的现代焦虑。这本书是寻找“诗意栖居地”的自我想象之路,更是献给现代“异乡人”的精神慰藉之方。
——张清华(著名文学批评家,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时间于回忆之中漫长而充满隐喻,而故乡也因亲人、流逝和陌生让人疼痛。江飞用一种诗意的象征语言对生命、时间和情感进行叙述,万物或行进,或静默,都如谜一样优美,让人沉思。
——梁鸿(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我猜测江飞正在用文字建造一座博物馆,用以发掘和展示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经验和思考。
——徐则臣(《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