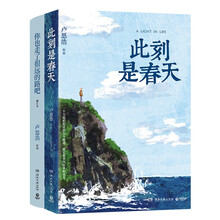阳光下不知怀念谁怀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内疚、惋叹、感喟,往心里用力,往心里烧,都是独自的,它只对一个人起作用。怀念也是轻的,飘着,无法栖枝、着陆,正所谓轻愁。但是只有自己知道,这愁,正一分一分揪紧着,怎么“轻”得了?!本是一个热闹的集会,爽声大笑、打闹和调侃是注定的,平日里散落四处的孤单个体,在这一刻,都主动褪去生涩、孤傲的外衣,变得孩子般单纯而快活。却往往在这样的时候,最容易感染上怀念的旧病。
然而,是什么令人怀念?是什么“值得”怀念?一直以为,四十岁是个不尴不尬的年纪,不老不少的,既不能耍赖又不能矫情。要瞻前顾后,要左顾右盼,自己就是发难的中心,总是不断地难为自己、谴责自己——为什么不成功、不出色、不优秀?为什么不能成为铜墙铁壁,为所有比自己弱小的草木花红、至爱亲朋遮风挡雨?这世界,正需要我来做个孤胆英雄,时时挺直腰身,不得有半点儿委顿、迷离,不得有一丝半点儿的偷懒。
可是,于暗处,“坚硬”的心,正瘫软如泥……而“暗处”,却也并不单单指明是在“无人”的时候。在人群中、在阳光下,它也会偶然惊现——仿佛“暗疾”,依附于貌似健康的躯体,跟随着晃动的外壳,游走西东。不过,这样的秘密只有自己知晓。
听说霜降就要来临,已有几分秋凉先期而至,于星夜兼程,悄悄收拾了原野的繁荣。是谁催促着“快快成熟”!又是谁催促着“快快结束”!一个完满的轮回。其实,大自然的伟力历来从容舒缓如水,注定伤到的,是我们还没有彻底结痂的心。
时辰不到,什么都不会呈现。
那种树,不高,也不纷披婆娑,以我的能力,除了简单的杨柳松柏之外是叫不上名字来的,却并不影响我的喜爱。它们不喊叫苦、累,也不休息,走了几程,就从绿走到了黄?像渐凉渐浓的枫,往深渊里走,往深刻里走。在一地的清霜铺展之前,它们就那么倔强地烧起来,烧起来,想把自己完全彻底、干干净净地挥霍一空。像莫名的情绪,忽然就来了,忽然又去了。穿行于这样的场景中,忽然就悲从中来——万万是不敢说出“悲秋”的,这样的时日,未免还没摸到秋的底里——但是,忽然无语,忽然沉潜,沿着并不确切的路,悠悠晃晃地往回走。那些已然离开、正在离开或活得正旺着的,都一起怀念起来。谁说怀念只把一张苦脸朝向以往?一个熟知的生命,在度过了少年的好奇、青年的青涩之后,很快,便步入了生命的下坡。然而,他下得太快了。还没调匀步伐,还没开始,就已经完结。匆促潦草地,那个圈儿画得并不团圆。他十几、二十几年前的模样,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小动作、怪毛病、连腮胡子,他的易经、闪光的镜片、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腔调,都还记存着。人却已远在红尘之外、憩园之中。本无所谓好恶,也无所谓悲喜。但对“一个生命”的回环竟是如此草率,心存不甘。那不正是一个例证和药引子吗,或者排毒、发汗,或者昏厥、休克,与具体的肉身无关,但又明明有着不明不白的炎症。
或早或迟吧,谁都逃离不脱。灿烂的秋阳舍得花费它的慈爱之心,大把大把的金币抛下,却不幸作了谁的祭祀?融融的阳光隔着玻璃会更暖几分,正好配合了我微微眯起的眼睛。仿若曾经百事缠身、万水千山走遍的沧桑老者,安然倚于断墙,心中的波澜早已一一掀过,一一抚平。
在秋冬之间仅有的好日子里,忽然想起一个早早退场的人,算不算突兀?我轻轻地摇头,谁也没有看见,三四下而已,自己给出自己一个正确的答案。回忆和怀念都是好的品质,与清晨雅洁的残月似有所同。有点冷,但不会把你冻伤。它不肯离去,正说明它的崇高而昂贵的美。不管怀念谁,都是回头,都是想起一种生活,一种有自己影子、有幼小的自己和年轻、盎然的色彩参与过的生活。以此开始怀念,是保险的,也是容易的。
金光大道在眼前如水流展开,让出空位,为一个上午的光阴送行……这一条路是否走过?几天之前,也是谈笑风生地走过。如今,怎么却变成病灶,恍惚、晕眩。明明是明晃晃的艳阳,却让我胃凉、心寒,需要找些什么来暖一暖。
两个相爱的中年人,善良得不忍心最先动手拆散现有的格局,看似那么幸福的哦;却又无法排解心中亦步亦趋的“接近”。两个“体面人”在若干个城市之间走走停停,像两个贫困交加的无助弃儿,四处流浪;在灯火阑珊处,相顾两茫茫,无语断肠。能够静静地坐在少人的河畔,望望流水、看看落花,都是最大的奢望,更别提亲手做一顿柴米油盐的早餐了。——就那么安静、规矩、毫无念想地坐着,什么也不用说,向身右那对深情相牵的耄耋老者投以钦慕,目光柔软、含情。
最好就那样坐下去吧,日升、月落,倥惚之间,华年老去,一夜白头……他说:再等等,等安顿好孩子、安顿好父母、安顿好对方的……可是,什么时候才能安顿好自己虚寒、脆薄的内心?况且,偌大世界,何处安放?两个多么奇怪的人啊!聚首时,热血沸腾;分别后,便是暮年……早起的雾气一下子就被金灿灿的阳光洞穿,万箭穿心地疼!一次次否定,终归会被一次次确定修正。关于这个,我是知道的。然而,正在进行的一切也阻止不了我对未来的怀念。我不文艺,不是伍尔芙,但一间自己的屋子是我怀念的全部。它在哪儿呢?我不绝望,它肯定是在地球之上吧。记得初识诗文的时候,见过红线穿孔的一帧细窄的书签,因为两个坐在地球上缱绻的男女而分外珍爱,最下面,还有一行小小的字:幸福到极点。还记得他们的衣着和眼神,朴素、大方而年轻,一点儿也不招摇、也不暖昧。正是我喜欢的那种。谁会想到,两个可能并不存在的黄发、高鼻、深眼的异域青年,却影响、左右了我的前半生。或者,还将继续引领执拗的、渐渐萎缩的后半生——恒久的信仰鲜亮如浴,不改初衷。是的,苍苍茫茫的宏廓世界不足畏惧,它从来就是我们微缩的心脏。看呵,大地之上,生命无处不在,从大象、巨鲸到草履虫、蜉蝣、蝼蚁,都在过着津津有味的一生。天地之间,盛得下空前的繁华和绝后的毁灭,却容不下一个深爱的人……阳光下,大片的田野已经收割,或正要收割。钢铁的履带之后,一丛一丛的稻谷应声倒地,决绝而悲壮。而稻米服服帖帖地伏在大地的胸脯上,水分依然紧锁着,死死的,留住一丝活气儿,为了去换谁的性命?听说霜降就要来临,清辉如许的晨间,遥远的米香缭绕,有尘世不易察觉的细小而巨大的幸福。我亲爱的不知名的秋树们,会不会怀念这个夏天,怀念这个夏天里发生过的一切?阳光刺破云层,还在闪、还在闪,曲折地降下波光来,落在暗黄的苇叶上,一跳一跳的,却也并没有多少亮度。不过,断枝的芦苇的暗影,在细瘦、白亮的长水中,留下清浅的往日的光景,一时半会儿还不会走失。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