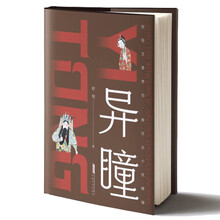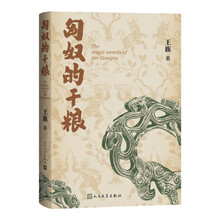儿媳毫不留情地责备我。
“父亲大人,”她道,“您为什么不穿我为您缝制的丝绒服呢?莫不是媳妇针黹退步了,做出来的衣裳上不了您的身吧,嚯?”
这声漫不经心的轻哼把她的缺乏教养暴露无遗,我不禁在想自己是否当真为儿子挑了个合适的老婆。
“你如此有心,可算尽责,”我回道,“不过儿媳最好的绣针是她的利齿。”
如此还以厉害,让她安静了一会儿。她在琢磨我究竟是什么意思。
“父亲大人,您早饭没吃多少黍子,这会着凉的,您的肠胃也得受罪。您到时像那潺水溪似的泄个不停可别怪我!”
“把黍子给我,女人。我天生就跟溪流一样爱嘀咕个不停,你不知道吗?”
大儿子干咳几声。除了笔直的背和高挑的身材,他并没有遗传我多少特点。我的脸富于表情,许多情绪都写在脸上,他的脸则有如满月,圆而清淡。有时他烦躁不安的时候会微微皱起眉。今天也不例外。
“安静点,老婆,”他警告道。这一次,她闭了嘴。
我们听着卫村上方树林子里的猿啼声。
“父亲,您今天去钓鱼吗?”他问道。
我不禁逗逗他。
“去不去潺水溪我都已经当了一辈子渔夫。记得我教你《渔歌子》吗?你那时还只是个孩子。”
他清了清喉咙。他记得。只是可能不是以我喜欢的方式。
“您收到的信里有什么消息吗,父亲大人?”儿媳追问,“您答应会告诉我们的。”
“啊,”我说,“那信就像一朵花儿。谁知道它何时会结果呢?”
我用筷子挑起黍子的时候,感觉到他们受挫的目光。我有时可能太过疏离冷漠了。
“信是我的老朋友裴泰写来的。他说很快要来造访。”
“原来如此,”儿子不安地说,心里掂量着自己得为这样一位访客作何准备。
儿媳则兴奋难耐。她不愿被人瞧出来,所以我帮她一把。
“你得准备些酒。对老头儿来说,不需要别的什么了。我们喜欢以酒为饮,以往事为食。”
“只要酒,嚯?这个裴泰尊贵吗?”
“那还用说!”儿子斥道,“你没听父亲提起过他吗?裴泰大人是当朝右丞相,可是当今圣上身边的红人!”
“只要酒,”我温和地说,“接下来的事就不用管了。”
在心里我并不这样肯定,而且暗自为此处的简陋生活感到羞愧,枉我顶着“邑主老爷”的头衔。立在篱笆墙头的公鸡也同样让我难为情。在自家门口迎接像裴泰这样身份的人可不是件小事。
我们家的宅子当地人唤做三叠山庄,依着村子上方山势而建。宅子由三栋单层大屋构成,各屋之间由嵌入山边的砖砌台阶相连。最下方的屋前是一个带围墙的庭院和门房。所有房屋均以枫木和松木搭建,上覆红砖瓦屋顶.陶制狮子、螭吻和凤凰如守护神般装饰着屋檐。小时候我总认为它们会在我睡着时活过来,在梁间上蹿下跳,窃窃以八位风神之言密语。
接下来的一周,三叠山庄成了儿媳所统领的香味大军的地盘。她正在为客人的来访准备吉祥酱汁。八角带着尊贵的气息;酸橙的尖酸一如挑剔的媒人,那所向披靡的气势也同样毫不逊色。儿媳决心不让自己丢脸,直忙活到瘦削的双颊发红。她的婢女和一个村里的女孩充当她的帮手。
酒铺老板瘸子付送来十二坛子酒,我坚持要先尝上一尝,确定他没有以次充好。那夜,我取下了我的琵琶,在儿子来服侍就寝前吟咏了半部《诗经》。他不理解,我是在为月牙儿吟唱,她并不在意我是否不成曲调。我甚至可能将我此时的想法作成诗赋。但仅此一回,萦绕脑际的幽灵被驱散,我睡得极香,什么也没有梦到。
醒来时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裴泰今天就会到。我把这个感觉告诉了大儿子。他严肃地点了点头,然后就退出去吩咐下人们去了。稍后,他带上小弓到沿河的苇丛打鸟儿。儿媳焦急地盯着从卫村上来的路。她特别悉心打扮了一番,头发堆起足有一尺高,以牡丹和飞燕造型的发梳固定。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