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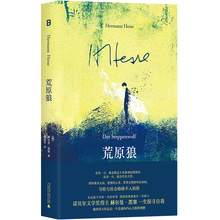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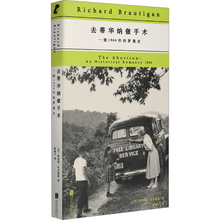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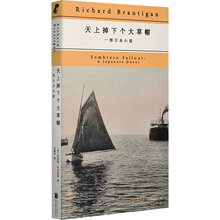

《玫瑰的性别》----
《华盛顿邮报》年度最佳小说
大英联邦作家奖最佳新人小说
英国《卫报》首作奖提名
台湾诚品选书,中国时报开卷推荐佳作
身世如谜的弃婴,被体内雄激素不断干扰情欲的贵族小姐,穿着女装娶妻生子的玫瑰伯爵
她不是“她”,她是“他”,“他”是最真实的自己
他是玫瑰,你即将展开的,是玫瑰的传奇,玫瑰的“变形记”
——知名民谣歌手约翰·韦斯利·哈丁将他创作的Miss Fortune一曲扩展成小说,汇集古堡传奇、贵族秘史、性别扮演与身世追寻等诸多元素,挑战姓氏、家族、血缘、性别等最大禁忌。
——女诗人神秘诗稿、流浪歌手的歌曲、忠诚家仆的密码、希腊神话故事的隐喻、性别的认同与自我认同、如迷雾散去般层层揭开的弃婴身份,交汇成一部情节庞大的小说,剧情辗转,谜底揭开,抖出的是让人瞠目结舌的秘密……
《玫瑰的性别》讲小镇的富豪领主洛欧伯爵沉溺于失去胞妹的痛苦中无法自拔,无视自己在城郊垃圾堆救起的弃婴性别,执意将这名男婴当作亲生女儿收养,并为之起名为玫瑰。
玫瑰麻雀变凤凰成为洛欧山庄唯一继承人,但在严格的淑女教育下长大的他,进入青春期后却表露出日益明显的男性特征,这深深困扰着他,也令洛欧伯爵忧郁成疾,不久病故。伯爵死后,玫瑰的弃婴身份及真实性别被揭露。野心勃勃的亲戚借机赶走玫瑰一家,霸占了城堡。
玫瑰在性别错乱的矛盾中挣扎,彷徨于男与女之间,在一连串颠沛流离的“变形”后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也逐渐得知了自己离奇的身世与洛欧山庄的秘密。当密码逐一破解,埋藏于流浪歌手之歌与忠仆日记中的真相被一点点拼凑起来,惊人的秘密改变了玫瑰的命运……
2
我学刮胡子时,问题更严重了。
史蒂芬十二岁生日时收到一支刮胡刀。这是我们见过的印象最深刻的礼物,太真实太恐怖了,即使当道具都不敢。他父亲教他如何将木钵里的皂霜磨出泡沫,再用一支小巧玲珑的刷子涂在脸上,然后丢下愚蠢的史蒂芬自行处理。史蒂芬的上嘴唇刮下稀疏的微毛后,还没来得及闭上嘴巴便吃了满嘴泡沫。他咬紧牙齿微笑,下巴冒出红色的小斑点。我同情史蒂芬,但我觉得可以做得比他好,假如有什么不同的话,也许我更需要刮胡刀,但我知道女孩子不需要刮胡子。
我接受了很多表面价值,但有些事情教我迷惑,那些是我渴望了解自己的事情。我隐藏这份好奇与疑惑,连母亲也不知道,因为我要维持快乐女孩的形貌让人人高兴,我知道假如我有什么异样的感觉,那必定是我的错。我告诉自己,假如我用心一点听话,就不会如此不明就里了。我不愿想起自己的体形,尽量不去碰或看下面。有时候,它很丢脸地唤起注意,我试着下结论时差点没被恐慌吓垮。于是,我成了一名隐藏老手。母亲让我觉得,那事不能谈论也不须忧虑。和莎拉说起这事更让我觉得尴尬,即使作为我们之间的秘密也令人难为情。她比较明智,从不谈起这话题,我也不应该谈。
不,要谈也必须是母亲,否则就什么都不要说。那是规定,但我太尴尬了。我害怕有什么差错,父亲会恨我。我能告诉别人吗?有一天我必须说吗?届时,有多羞耻啊!光想到这个,就让我掉入忧郁的漩涡里,因此,我尽量什么都不想。有一天,我必须揭开这个神秘面纱,但现在应该隐藏、忘记,或更加严守秘密。
还有另一件事让我对莎拉难以启齿:既然我们如此相近,为什么变得如此不同?
我长得没有她快,不禁羡慕她。当我们穿同样的衣服时,挂在身上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她的骨架轻盈,有棱有角、瘦骨嶙峋,但身体发育得非常优雅,和我简单平板的线条相距甚远。她的肌肤是鲜明的橄榄色,我的肌肤因未见阳光而依然苍白。我们的头发同样柔软、微卷,但我的头发还长在别处,手臂上的毛发更粗。我看到了她裙子底下、宽松的袖子上、领口下的体态。
她叫我尽量拉紧她的束腰。我闻着她的秀发芳香,手滑入她的衬衣与肌肤之间,感觉她的腰部曲线。我将束腰拉得半紧,然后用食指从上往下拉,让束腰紧绷不动,最后,拉到紧绷得引出她一声小小的惊叫为止,如同史蒂芬与我跌落河里时,我一直往下沉、往下沉。
解开束腰是更好玩的事,更不需要什么技术。我一点一点地松开她,看到她的身体迸开花边,手一放开,带子就从铜环滑落,她身体自然移动,完成了我的工作。她发出感谢的呻吟。我感受到她的愉悦。
我往上长,现在比她高个几英寸。她则全面发育。当然,我比她小两岁,但这就能说明所有的差异吗?或许我要为自己的缺失负责,也许是我太过男孩子气,导致身体发育成男孩型。因此,我尽量花同样多的时间与莎拉在一起,并且试着模仿她。
我的最大发现是在某些幸运夜晚,我们关在小屋里,狂欢喧闹到天亮,只有我们两人。我们半寐半醒躺着聊天,身体几乎没有接触。她躺在我的肩窝下,我的手臂环着她。这些秘密夜晚纯真无邪,直到有一次我临时起意,故意降低声音。
“我,欧塞,希望夫人今天没有被救援行动弄伤。”黑暗中我在她的发边轻轻说。
莎拉假装昏厥,乐得笑呵呵,动一动脚指头表示赞许。
“不,伯爵。”她克制住微笑说,“我没有受伤,您行侠仗义救了我。”
“我很高兴,放心,我没有受伤,夫人。”
“真是太庆幸了,伯爵先生,这应该归功于盔甲吧?”
“当然,盔甲。”
两人无语。她别过脸去,我像欧塞一样吻着她的后颈。她没有阻止我。我们的身体越磨越近,床也跟着移动。渐渐地,我靠近她的嘴巴,终于两人唇碰唇,但没有动作,直到嘴唇非常干燥为止,仿佛我们都忘了胜利之吻的学习,又仿佛不知道如何面对横躺着的场面。她尴尬地笑一笑,润一润嘴唇,以免两人的嘴唇粘在一起。我们只有嘴唇接触,但我可以感觉到她的身体召唤,唤我靠近。我不敢再多碰她一下,只“嘘!”一声便匆忙回到自己床上。我重新回味一遍,想象屈服在她的热情中。
这些兴奋夜晚很快成为一种仪式:秘密、温暖、刺激。每次行动,我们不断变换虚构的角色,但高潮仅止于嘴唇接触。还有什么可以想象的吗?我睡觉时,有了想象的材料。
烦恼随着阳光回来。
“天生我才必有用。”母亲说,“我们都长得很漂亮……”然后又说,“但没有人像你的普鲁登丝表姐那么漂亮!”
有一次欧斯本家来访,我们目睹了普鲁登丝经由她母亲之手打扮得漂漂亮亮,让人觉得恶心。而她父亲,那位上帝大人,看一看四周,为她们的虚荣嘀嘀咕咕说着抱歉。诺拉背诵了一段又臭又长的陈词滥调,说普鲁登丝是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女孩,头发又柔软又浓密,眼睛明亮,肌肤晶莹剔透,她的艾瑞伯父非常以她为荣!被戴绿帽子的牧师困窘不安,为我们掩饰道:“以上评论不是针对在场所有人……承蒙夫人允许。”诺拉依然絮絮不休,终于,她女儿问:“我是不是比玫瑰漂亮?”她母亲正要肯定回答时,艾格举起手,像对着老天似的大叫一声“不!”然后冷静下来坚定地说,“我不准你回答这个问题,不准。”
现场没人再多说话。不过,诺拉必须违背自己不说“是”。普鲁登丝是很漂亮,十七岁,令人羡慕的柔弱之姿,身材玲珑有致,莎拉也渐渐发育成这种身材,而我不是这个样。她的全身肌肤和手臂一样光滑,美丽得难以形容。我渴望那种柔软细致,藏在我衣服下的肌肤毛发耸立。普鲁登丝走来走去,摇曳生姿,衬托得体态更优美。后来,我描述给莎拉听,莎拉也立即学起摇曳生姿的走路姿态。我也试了一下,我想,看起来像一只猴子吧。史蒂芬不待我问他便说是。
性,大字典如此解释:“任何生物的男或女的特质。”后来,米尔顿如此陈述:“生物在他的手中捏造成形,像男性,但不同的性。”所以,是男性或女性。第二种定义是:“女性,经由重点强调。”所以,是女性。百科全书如此定义:“用此区别男性与女性。”所以,是完全不同的意思。我一直被教导要完全信赖这些东西,但我觉得这灰色地带和我一样混乱。其实,也难怪。如果性可以区别男孩与女孩,关键却非常不明显,因为我与史蒂芬的差异甚小。当然,我们是不同,但不是非常不同,譬如:我们两人的声音都变得越来越粗,若要讲差异,可能我的声音稍微高一点吧。我无须努力声音就这副样子,但要像莎拉那样的声音却得费好一番力气,而我想要像她那样。史蒂芬的声音变得低厚,最后落在悦耳的男高音。我呢,经历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阶段,在粗嘎刺耳的高音与约德尔女低音之间交替轮回。我希望我的声音是其中一种,不为什么,只因为这样比较不会那么滑稽。最后,在我十三岁生日前,声音突然落在女低音。经过一番练习,我无须集中心思便能发出更高的音调。
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在父亲眼中看见除了爱之外的其他眼神。我觉得那是因我而尴尬以我为耻的眼神。或许他了解我有许多无法想象的紊乱,又或许他知道我所有的秘密。有一次我和他隔着餐桌四目交接,我看到一种厌恶的眼神。他明白自己表现了过于强烈的情绪。虽然我已忘了他的眼神,也忘了他脸转向哪一方向,但那个情景历历在目,我唯一能做的是,不要想起它。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很沮丧。那晚,我问母亲到底怎么回事,她告诉我没什么,她说所有小孩在成长过程中都在乎父亲的爱。我知道事情并非那么单纯。现在一个可信的权威,也就是我自己,告诉我每个“吾家有女初长成”的父亲都有一种隐约的不安,因为那激起了他们内心的矛盾。但父亲不是这样。我没有发育,他避开我。
此时,我嘴唇上与脸颊附近的毛发越长越浓,越来越失去稚嫩,柔软毛发一绺一绺消失。莎拉微笑的唇边仍有若隐若现的绒毛,而史蒂芬与我的这块区域却越长越粗糙,我甚至比他更需要刮胡刀。让我惊讶的是,母亲竟然同意。
我的刮胡刀与肥皂钵也出场了。
“所有小孩都担心自己的发育有问题,亲爱的,你发育得很好。”她这么说,但又告诉我如何把自己打点得更漂亮的新技巧。首先,她提到钳子,还有刮胡刀。她教我如何使用刀片刮唇上的须毛,之后在上面抹了一层粉,那让我打了个喷嚏。我们的盥洗时间更长、方法更复杂,比抹蜜粉、睫毛膏与胭脂更耗时费力。终究,女孩也需要刮毛。
一开始,我觉得很新鲜,虽然挑起破皮与刮伤自己时痛得不得了。母亲帮我买了刺激性强的香水,芳香多少减淡了一点疼痛。先是玫瑰精油,继而是野蔷薇香水,这两者我比较喜欢野蔷薇,最后是馥丽仕的铃兰百合香水,至今我仍在使用。有毒的铅块粉、醋与马粪调制的香水(吓死我了)让我的肌肤窒息、暗沉,每晚我拿母亲的杏仁油胭脂以鲸脑油与蜂蜜软化后,涂在脸上缓和疼痛,直到隔天早上的冲击。
没多久,我开始思索刮胡子的用意何在。我只见过一次长胡子的女人,真的胡子,那个女人和马戏团一起来,看起来并不太差。她相当臃肿,从头至尾过于肥胖,与其说她是女人毋宁说她是男人,但我觉得她挺优雅的,人人都赞赏。刮毛是一件痛苦、无聊、浪费时间的工作。为什么女人不长胡子?我看到母亲的唇边有微微的绒毛。她帮我梳头时,我想象着她长小胡髭的模样,镜子里浮现出来的是勇敢活泼的影像。
随着我的成长,越来越多使用化妆品,莎拉觉得这样最迷人。她的肌肤比我的自然美丽,无须使用刮胡刀。不幸的是,刮胡刀的援助让须毛越长越快,我得忍受这些折磨,越来越频繁。
闷闷不乐的讨论渐渐变成一种日常事件。我记得曾经被匆匆忙忙带离房间,似乎,有某件我不能看的事情,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发生了。我觉得自己被遗漏,仿佛他们藏着秘密不让我知道,我日渐感到不安。这是我第一次有自觉意识,开始更亲近地监看自己的行为与怀疑自己的冲动,也懂得说话之前先三思。
母亲终于说出父亲病得相当严重。他的神经崩溃,高烧不退,唯一的希望是好好休息。我们为他祈祷。我害怕我的愚昧会加剧危机,没想到情况更糟糕。
有一天晚上,安丝黛丝结束了沉默的不安宁期,出现在图书室门口。母亲独自在图书室工作,抬头看到安丝黛丝,惊讶她走出自己房间那么远,急忙问她有什么事。安丝黛丝晃着身子摆出尊严的架势走近,仿佛踩着高跷。她沉默地站在桌子边,望着自己的鼻子,鼻孔紧绷,变得有点半透明。
母亲又问一遍什么事。安丝黛丝冷静地说,她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朱利叶斯·瑞克雷,另一封给亚瑟斯登·欧斯本。信的重点有两个:一是我不是女孩;另外……更糟,我是弃婴,不是父亲与母亲的自然结晶。当时的马车夫菲利普和父亲与傅德一起发现我,现在被调至遥远的庄园工作,可以证实她的说法。她可以销毁这两封信,但只在一种情况下,那就是,我归她看管。
“我应该叫傅德与汉密尔顿过来。”母亲相当镇静地说,惊愕地走向钟索。
“不要。”安丝黛丝举起枯槁的手臂,“我只想跟青春伯爵说话,为了尊重,我通过你传达这件事情。”
“因为我丈夫生病,‘哈哈帮’需要……”
“‘哈哈帮’……哈!够了,这些文字游戏!该结束了,我来结束它。假如你不愿告诉青春伯爵,我亲自跟他说,或者寻找另外的公平渠道。玫瑰也喜欢听故事,是不是?他喜欢吧?”
母亲站着,气得不小心倾倒墨水。墨水沿着书桌漫向纸张。吸墨水纸放得太遥远,母亲拿不到,遂就近抓起可用的东西止住四散的墨水。安丝黛丝望着她抓起她的裙子。
“我应该擦干净吗?安诺妮玛。”她并没有伸出援手之意,“或叫管家过来?我知道什么对玫瑰最好,也知道洛欧夫人的想法,她活着时我完成了她的每一个心愿,是不是?现在我也应该这样。除非玫瑰归我看管,否则我就会寄出这些信。”
“你不是洛欧夫人,安丝黛丝,洛欧夫人死了。我才是现在的洛欧夫人。”
“你是一个十指沾满墨水、想法僭越分寸的图书馆员,不过,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与你的怪异哲学如何,都与我无关,我已经表达完我的意思。”
“你休想和我丈夫或小孩说上半句话。”
“你的丈夫?你的小孩?”
“休想!”母亲大吼。她愤怒到极点,安丝黛丝稍微平静下来。母亲用沾满墨迹的手压住嘴巴,强迫自己住嘴,然后抬头看,“你要杀了他吗?”
……
导读:玫瑰有性别,但依旧芬芳
无名
再生
变形
梦土
溯源
剧终
附录
这是一个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不一致的人的故事。世界上有一大群这样的人。他们的生命与众不同,而常常是比一般人更加精彩的。他们的存在方式发人深省,使人窥见人性的复杂、奇异和多彩多姿。
——著名社会学家 李银河
这本书宛如一根魔法棒,挑战着两性间那条神秘的河界,也革新了读者对性别的想象,扩充了性别的灵魂厚度。
——作家、性学博士 许佑生
显而易见,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人类以性器官及第二性征被分为两类,若非男性,即为女性,男性与女性透过性行为繁衍后代,当然,后代还是那单纯的两类。伴随着此显而易见,某些理所当然接着成型,男性与女性各有其专属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判别,某些符号只能在某一性别上看到,否则即是异常。然而,《玫瑰的性别》里的主角玫瑰?洛欧伯爵则彻底颠覆了这些理所当然,“异常”在他/她身上随处可见,而这些“异常”也正是他/她最真实的自我展现。
——媒体评论
一个身世如谜的弃婴,如何被卷进洛欧家族玫瑰与石南交缠的图腾,进而发现家族的阴暗历史,和他(她)自己真正的性别……在指尖翻阅书页的同时,我仿彿也跟着书中的主角“玫瑰?洛欧伯爵”走过一段青春的旅程,重新去思考、感受,什么是女性特质,什么是男性特质,还有,什么叫作真正的“爱”。
——读者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