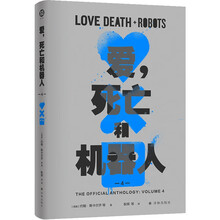节选1
我拿着去巴库的头等车厢车票,走上月台,跨进车厢,按习惯把自己安顿在舒适的靠窗座位上。只有几位旅客跟在我后面进入了头等车厢,大多数那些四海为家的人则进了二等或三等车厢。查票员查完票后,把车门紧紧地关了起来,接着一声哨响宣布列车准备出发。
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发出一声嚎叫,一种绝望的嚎叫,我听出来他说的是德语。
“等等!等等!”
我放下窗户,望了望窗外。
一个矮矮的胖子,手里提着一个包,头戴旅游帽,身穿一件宽大的外套,外套下面两条细小的腿格外显眼,与整个人极不相称。他跑得气喘吁吁,原来是晚点了。
几名车站搬运工试图拦住他,如同竭尽全力拆除铁轨中的炸弹一样。结果一次次阻止都以失败告终,他还是强行上了车。
这位德国“炸弹”快步冲上了车,钻进了一位乘客原先强行留着的车厢门,在我们隔壁的隔间里坐了下来,乖乖地蜷成一团。
此时,火车发车了,车轮开始在铁轨上滑动,徐徐地驶出了车站,不久便提高了车速。
我们离开了外高加索。
节选2
这时,搬运工已扛着那口木箱到舷梯上来了。
我看到那搬运工脚步蹒跚,很吃力的样子,摇摇晃晃,好像刚喝了一瓶伏特加似的。
“等一等!”埃费瑞列尔大声喊道。然后,又用标准的俄语大声喊,以便让他听得更明白些:“当心!当心!”
建议不错,可为时已晚。说时迟那时快,那搬运工一不小心踏空了脚,木箱从他肩上摔了下来。不过,不幸中的万幸是,箱子落在“雅丽莎”号的栏杆上了,只是摔成了两半。无数个纸包散开了,纸包里面的东西散落在甲板上,满地都是。
埃费瑞列尔怒不可遏,大吼一声,接着朝这位不幸的搬运工猛击一拳,嘴里带着绝望的口吻,不停地唠叨:“我的牙,可惜了我的牙!”
他弯腰屈膝去拾那些散落在甲板上的乳白色人造假牙,而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对头!正是纽约布尔布尔集团斯特朗分公司出品的假牙。该公司一个月为全世界五大洲生产5000箱假牙。够多的了,供全世界新老牙医使用。这批货是运往遥远的中国的。该工厂生产这些假牙,需要有1500匹马力的大型机器,每天需烧100吨煤。美国人就是这样!
如果全球总共有1400万人口,每人平均32颗牙,每个人都将原来的真牙换成假牙的话,布尔布尔集团斯特朗分公司要向全球提供四亿多颗假牙。
最后一次钟声已敲响了,乘客都上了船,“雅丽莎”号已开始起锚,准备起航。我们不得不留下埃费瑞列尔,让他继续收捡他42号箱的宝贝——假牙。
节选3
大约航行了1/4海里后,海水沸腾起来,像开了锅似的。海面上波涛翻滚,这表明海水深处有情况。这时我正好站在靠船右边角落的栏杆边,嘴里叼着一支雪茄,遥望着刚刚离开的港口在阿克隆角后面隐隐约约地逐渐消失,同时,高加索山脉突然出现在西面的地平线上,显得十分美丽壮观。
嘴上的雪茄只剩一点点烟蒂了,我轻轻地吸了一口后,把它扔进了海里。
刹那间,轮船周围冒出一片火焰。原来海上沸腾,喷出的是石脑油,雪茄烟蒂一扔进去就点燃了。
伴随着一声尖叫,一束火焰朝“雅丽莎”号扑了过来。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舵手将舵一转,避开了那股喷出的火焰,躲开了一场可怕的灾难,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船长立即跑来船尾,很严厉地把我训斥了一顿。
“你真蠢!”
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如平常那样回答说:“对不起,船长,我不知道…… ”
“你应该知道,蠢货!”
说后面这句话的人离我有几英尺远,语气恶毒尖刻。
我转过身看看是谁。
原来是一位英国女子也想教训教训我。
节选4
时间已是晚上10点半了,我还坐在“雅丽莎”号船尾的椅子上,但海风越来越大,实在待不住了,我便起身前行。在驾驶台下面、明轮罩之间,狂风呼啸,因此,我不得不在帆布包中找个能避风的地方。我躺在一口箱子上,用毯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头枕在油帆布上,相信很快就会入睡。
过了一段时间后——具体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一种奇怪的噪音吵醒了。这噪音究竟是从哪儿传来的呢?我仔细听了一会儿,仿佛是有人就在我耳边打呼噜。
“大概是坐下等客舱的旅客吧。”我心里说,“难道有人钻进油布下面的木箱之间睡觉去了?不会有人轻易找到这样安逸的地方吧?”
我想借助罗盘柜下面射出的光线查个究竟,可什么也没发现。
仔细听了一会儿,嘈杂声又停止了。
我环视四周,这边甲板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二等舱的乘客都已上前面去了。
难道我是在做梦吗?我又恢复原来的姿势继续睡觉。
没有错,鼾声又响了起来,声音正是从我头靠着的方向传来的。
“天啊!”我说,“原来是一只动物在那里打鼾!”
是一只动物吗?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是只狗,还是只猫?他们为什么在这口箱子里藏一只家畜呢?或者是只野生动物?是一只黑豹、老虎,还是狮子呢?
原来这口箱子是个兽笼。我现在来个跟踪调查!十有八九是从某个动物园运到中亚苏丹动物园去的野生动物。不过,这笼子一旦开了,动物就会跳到甲板上,那后果不堪设想。这事值得我记录下来。大约出于职业的缘故,我兴致勃勃,一定要把这事弄个明白。这头野兽是运往何处的?是运往乌尊·艾达还是运到中国去的呢?要花多少运费?箱子上应该有地址。
我点燃了维斯塔蜡火柴,用手遮挡着风,稳住火焰。
就着这点光我又能看到什么呢?
装运野兽的箱子上面确实写有地址:
中国北京岔口街曾卡·科萝克小姐收。
小心轻放,谨防野兽!防潮,小心狮子!的确如此!这位曾卡·科萝克小姐又是谁呢?她一定长得很漂亮,因为罗马尼亚人一般都比较漂亮——她肯定是位罗马尼亚人,她干吗要用这种方式运野兽呢?
我们来假设一下吧,而且尽可能现实些。不管怎么说,这头野兽它得吃、得喝,不吃不喝是不行的。从乌尊·艾达跨越中亚到达天朝帝国的首都需要11天。如果整个旅途中都把它关在笼子里,从不放出来,那么,他们给它吃什么、喝什么?如果把它说成是一箱子玻璃而不是什么野兽,跨大中亚的官员自然是不会如此小心翼翼,高度注意了。话说回来,没吃没喝,它会虚脱致死的!
这一切的一切不停地在我脑海中盘旋,真纠结,令人困惑不安。
节选5
“怎么不信呢?目前火车在天朝还是一种十分新型的交通运输工具,由于它跑得较快,这样就保证了它的安全,不会有人袭击。不过,有一个名叫吉昌的人,他专门进行拦路抢劫。这人总是独来独往,神出鬼没。”
“他是谁?”
“一个胆大妄为的土匪头子,他有一半汉族血统,一半蒙古血统。他曾经在云南搞过一段时间恐怖活动,中国政府一直在追捕他。他已经逃到中国北部来了,在北部一些省份活动频繁。据说他目前正活动在跨大中亚公司管辖的地区。”
“哦,是这样。他应该可供我写好几篇报道了。”
“要写吉昌,很可能您得付出一笔很大的代价。”
“没关系,少校先生,《二十世纪报》很乐意支付这笔费用。”
“要拿到这笔钱,或许我们得先付出性命。幸运的是,车上的乘客没听到您刚才说的那席话,不然的话他们会一拥而上,马上把您从车上赶下去。小心点儿。作为一名追求冒险的新闻从业人员,您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别乱讲话。还有,千万别跟吉昌沾上边。多多为乘客们的利益着想,考虑一下大家的安全。”
“少校先生,我的意思不是说在火车上……”
节选6
跨大中亚列车要跨越高原,困难重重。这是天才的人类向大自然发起的挑战,胜利总是属于天才的。人们筑建高架桥、堤防,凿峭壁、开隧道,打通了这条缓缓的斜坡通道,柯尔克孜人称之为“贝尔斯”。急转弯接二连三,斜坡不断。需要有动力强大的机车才能开过去。所以一路上到处设有固定发动机与电缆,帮助把火车拉上去。总之,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比美国工程师在内华达峡谷和洛矶山脉修建的工程艰难得多。
这儿一派荒凉,到过这里的人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他充满着遐想。随着火车爬上更高的高度,这种印象更深刻、更鲜明。这里既没有城镇也没有村庄,只有零零星星的几处小屋。帕米尔高原上的人们带着自己的家人和牧群——马、牦牛、一些羊,以及他们那厚厚的毛皮大衣,孤独地生活在这里。他们冬天穿着长皮袍子,夏天换成白色裘皮大衣。我们可以这样描述:他们更换毛皮外套都是因为气候的变化。狗也如此,炎热的夏天,它们的毛也会变得更白。
随着道路海拔不断地上升,视野越来越开阔,可以望得更远。到处是一片片的白桦和桧树,这是帕米尔高原上生长的主要树木;在连绵起伏的平原上生长有柽柳、莎草和艾蒿,盐湖边的芦苇极其丰富,还有许许多多的矮唇形科植物。
少校给我谈及了帕米尔高原上的某些动物,它们成群结队,在高原上游荡。我们有必要注意一下列车的平台,以防一些流浪黑豹或狗熊不经许可上来乘坐一、二等舱旅行。白天,我们的同伴会时刻观察列车的前后,当一些踯行动物或猫科动物沿铁路跑来跑去,乱吼乱叫时,的确值得注意,因为你不知道是什么家伙在叫唤。有时,平白无故会放上几枪,不过,他们是在逗“旅客”玩,保证不会伤害它们。不过,那天下午,我们亲眼目睹了轰的一枪,一只大黑豹正跳到第三节车厢的踏蹬上,立即被打死了。
节选7
“我绝对相信,亲爱的卡特拉先生。我们还是先到车站餐馆去看看吧,告别了突厥斯坦食品,我们现在开始吃中式饭菜了。”
卡特拉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因为少校告诉我们说,喀什噶尔的厨师比较出名,他不愿错失良机。
卡特拉夫妇、少校、年轻的班超和我都感到非常惊讶——餐馆提供给我们的饭菜太多了,而且十分可口,真是美味佳肴。有烤肉、吊烧,甜食随意吃。卡特拉夫妇不由自主地又联想到了在苦盏吃的那些美味的桃子。这餐馆里有些菜式是长期保留的招牌菜式,比如糖醋猪脚、扣肉、甜酱炒腰花,还有油炸饼等,他们后来总是念念不忘。
第一道菜卡特拉就要了两份,其余的要了三份。“哦,我们得注意了,”他说,“谁知道火车上会有什么好东西给我们吃呢?说不准是已经变硬了的鱼翅,或是放了太久的燕窝!”
10点钟了,一声锣响后,海关开始办理入境手续。大家一起喝了一杯绍兴酒后,离开了桌子,没几分钟就到了候车大厅。
节选8
大家依次走到海关办公桌前办理过境手续。那里有两名身着制服的天朝海关官员,其中一位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另一位则是德语、法语和英语翻译。前者约五十出头,秃顶、八字胡、长辫子,戴着副老花眼镜,披着一件华丽的长袍,胖乎乎的,活像某个国家杰出的领导人。他那副嘴脸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好感,好在他只是查验一下我们的护照。既然所有的旅客都整整齐齐地排着队,依次接受检查,他看起来如何令人厌恶也就无所谓了。
“瞧他那是什么态度呀!”卡特拉夫人小声说道。
“中国人的态度!”他丈夫说,“实话说,我也不喜欢这种态度。”
我是第一个接受检查的,我有第比利斯领事的签证和俄国在乌尊·艾达当局的签注。那名海关官员仔细地查看了一下我的护照,没发现什么问题,于是给我盖了绿色龙章,表明我一切正常,可以入境。与清朝官员打交道,必须时刻小心谨慎为宜。
两位演员也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在检查到卡特拉的护照时,他表现得很滑稽,故意装出一副罪犯的样子,露出遮遮掩掩的眼神,皮笑肉不笑,似乎在乞求检查人员大发慈悲,或者说恳求他的恩惠。然而,那冷酷的中国海关官员一句话也没有跟他说。
节选9
中国的官员已经在运载财宝的车厢周围部署好了兵力,共20人。还有一些乘客,不包括妇女在内,加起来差不多有30来人。波波夫将武器分发给了大家,以防那些强盗真的发起攻势。诺尔提兹少校、卡特拉、班超、埃费瑞列尔、列车司机以及司炉,每人都发了一支枪。所有的乘客,不管他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都齐心协力,决心为我们共同的安全而战斗。
就在铁路的右边,大约100米以外,毫无疑问有一群强盗隐藏在阴暗而密集的灌木丛深处。他们正在等候信号,准备发起突袭。
突然间一阵吼叫,一伙蒙古人杀出丛林,朝我们扑来,他们大约有60来人,都是这戈壁滩上的流浪汉。情况万分危急,如果我们被这群流氓打败了的话,他们就会抢夺火车,天子的财宝就会被夺走,而且我们每个乘客都在劫难逃,他们会毫不留情地将所有乘客杀死。
节选10
客人们一一入席。埃费瑞列尔在有限的条件下将酒席办得如此丰盛,非常不简单。婚宴用的食品是早在恰克勒克就采购好了的。厨师是中国人,而不是俄国人。说实话,我很钦佩中国的大厨,他们烹饪技术高超,做出的饭菜十分可口。
在跨大中亚列车的餐桌上,大家可以用筷子也可以用刀叉,不会有人责怪你。我被安排坐在埃费瑞列尔夫人左边,诺尔提兹少校坐在她丈夫右边,而其他客人随便就座。那德国男爵是个从不会拒绝美餐的人,他也成了嘉宾。弗朗西斯·忒维昂爵士是个接到邀请后连话都没有一句的人,冷漠无情。
我们首先喝鸡汤,吃千鸟蛋,然后吃细细的燕窝丝、炖蟹黄、麻雀胗、卤猪蹄、羊排骨、炒海参、胶质丰富的鱼翅等;最后是糖浆竹笋、糖水百合。道道菜都是精心制作出来的美味佳肴。喝的是以铜壶加热的绍兴酒。宴席丰盛,气氛活跃。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太友好了。大家吃得都很开心,只是新婚夫妇相互没太注意对方。
节选11
像所有的纪念碑一样,这种宝塔是一层一层叠起来的,如同饭后的甜点。只是“菜”的式样更优美些。如果是用中国的瓷器盛这些“菜”,也没有什么令人感到惊讶的,肯定会美不胜收。
远远望去,我们看到一座加农炮铸造厂和一家造枪厂,厂里的工人都是当地人。穿过鲜花盛开的大花园就到总督府了。府上桥梁、凉亭式样多变;喷泉布局巧妙;门厅一道接一道,古朴典雅;整个庄园金碧辉煌,蔚为壮观。亭台楼阁,上翘的屋顶比比皆是;绿树成荫,庭院深幽。道路上铺的是青砖,这些砖头还都是修建长城时遗留下来的。
节选12
细细观察,不仅仅是发动机毁坏了,煤水车也不能用了。水箱已裂开,煤撒了一地。可是行李车却奇迹般地完好无缺。
从爆炸现场来看,我可以断定那罗马尼亚小伙子一定未能幸免于难,他根本没有机会逃离,八成已炸成了肉泥。我往前找了100多码,依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无疑他已被炸飞了。
一开始,我们只是傻傻地望着出事现场,不知所措。大家都吓呆了,很久都说不出话来。
“显然,”有一个乘客打破沉寂说,“司机和司炉肯定被炸死了。”
“他们俩真可怜!”波波夫说,“可我不知道列车怎么会跑到南京支线上来而没有被发现!”
“大概是因为天太黑了,”埃费瑞列尔说,“司机没有辨清交叉灯信号吧?”
“只能这样解释了,”波波夫说,“或许他是想设法刹住车,可刚好相反,火车却以高速在运行。”
“可是,”班超说,“邛谷高架桥还没有竣工,南京支线怎么会开放了呢?是有人将道岔合上了吗?”
“值得怀疑,”波波夫说,“或许是不小心给合上了。”
“不对,”埃费瑞列尔很慎重地说,“这肯定是种犯罪行为,有人想捣毁火车,害死车上所有的乘客……”
“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波波夫问。
节选13
弗朗西斯·忒维昂爵士,一位沉默寡言的人,他整个旅程中没有说什么话。我很想再听听他的声音,哪怕一秒钟也行。嗯!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机会终于来了。现在这位先生正带着蔑视的眼光仔细端详几节车厢,好像在寻找什么似的,然后从黄色的摩洛哥皮包里拿出一包雪茄。但他拿出火柴盒一看,发现里面一根火柴也没有了。而我手中的雪茄此刻燃得正旺,我抽得真得意,爽极了。很遗憾,在全中国也找不到一个像我这样抽得很得意、很有风度的人了。
弗朗西斯·忒维昂爵士已经瞧见了我嘴上的雪茄,便不由自主地朝我走来了。我觉得他肯定是向我讨火儿来的。他伸出手来,我把雪茄递给了他。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接过去,弹掉白灰,点燃了他嘴上的雪茄。
既然我没有听见他说声“借个火儿”,那么我至少希望他说声“谢谢,先生”。
可他半个字也没说。他很轻蔑地抽了几口自己的雪茄后,若无其事地把我的雪茄扔在了月台上,然后扬长而去,招呼也不打一个就走出了车站。
这样的人都有,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深感震惊罢了。他一不打个招呼,二不做个手势,若无其事。对这种不列颠的超级粗鲁蛋,我真无语了。诺尔提兹少校在一旁忍不住哈哈大笑。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