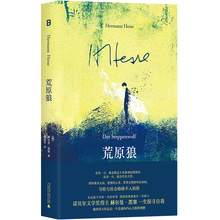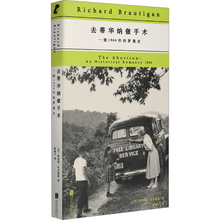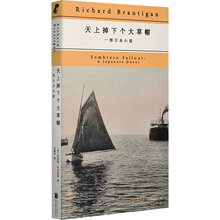“事实是,没有哪个动物吃鹰和狮子。”
她朝后退了一步,以便观看层层延伸的粉笔画。箭头示意图把第一层、第二层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生产者与第一、第二和第三消费者以及必不可少的小部分分解者连在一起,一切都与呼吸、热量流失和生物量增加联系在一起。自然界中一切都适得其所,也许不是每个生物,但至少每个物种都有其定性:吃或者被吃。真是很奇妙。
“记在你们的本子里。”
她说什么,大家就做什么。
这一年现在开始了。六月的躁动终于过去,孵化般炎热的日子和裸露的臂膀。阳光穿透玻璃的防线,把教室变成温室。空空如也的后脑萌生着夏日的期待。单单是对消磨什么都不干的悠闲时光的憧憬,就掠走了孩子们的注意力。带着游泳场的目光,油油的皮肤,汗津津的自由渴望,孩子们粘在椅子上,遐想着假期的到来。有的已经开始漫不经心,神志不清。另外一些假装对即将到来的成绩单的谦恭,把生物课测验卷放在了讲台上,就像猫把老鼠放在客厅地毯上。只为了下节课打听分数,抽出计算器,贪婪地计算着小数点以后三位数,希望提高平均成绩。
但英格·洛马克绝不属于那些到学期末就屈服的老师,只因为他们即将失去彼此。她不怕,就这样陷入微不足道孤家寡人的状态。夏季学期越临近,几个同事就越被温情的宽容侵袭。他们的课堕落成空洞的任由学生玩的闹剧。这里是跑神的目光,那里是一下温柔的抚摸,抬头装腔作势,痛苦的电影场面。好成绩泛滥,对“优秀”评分的出卖。拿学年末成绩做手脚,把几个没有希望的学生托进高年级,才真是恶习。好像还真的帮了什么人似的。同事们根本不明白,顺着学生,只会损害自己的健康。他们就是吸血鬼,掠尽一个人的生命力。由老师养活着,由他的职责和违反监护义务的恐惧养活着。他们不断袭来。荒唐的问题,可怜的灵感,没有品味的亲近。纯粹的吸血鬼主义。
英格·洛马克不会再让人耗干了。她因拽紧缰绳出名,完全没有咆哮和甩钥匙串的事儿。她为此自豪。退后放松什么时候都可以。偶尔给点甜头,喜从天降。
重要的是,给学生指出方向,给他们像马一样戴上眼罩,以集中他们的精力。确实吵闹的时候,只需用指甲在黑板上划过或者讲狗绦虫的故事。对学生而言,最好是时刻感觉到,他们被她攥在手心里。别让他们幻想着还能说点什么。在她这里,没有发言权,没有选择余地。没人能选择。只有被教养的选择,别无可能。
这一年现在开始。即便它早已起了头。对她来说今天开始,九月一日,今年这一天是星期一。英格·洛马克现在信心满满,在即衰的夏天,不是耀眼的新年之夜。她总很高兴,她的校历准确无误地把她带到岁序更替。简单的翻页,无需倒计时和铮铮作响的香槟杯子。
英格·洛马克一眼扫过三排座,头纹丝不动。她多年练就的精功:至高无上的,不动的眼光。根据统计,起码有两人对专业确实感兴趣。但看起来,统计正处危险之中。也不管是不是高斯正态分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看他们六个星期无所事事。没人打开过书本。长假期。没以前长了。但仍旧太长!要重新适应学校的生物钟,起码需要一个月吧。起码,她不需要听他们的故事。他们可以向斯万妮克讲述,她给每个新的班级都上相互认识的游戏课。半小时后,所有人被纠缠在一个红线团里,能够说出坐在身边的人的姓名和爱好。一只有零星几个座位上有人。这么少,很显眼。在她的自然剧场里观众少得可怜:十二个学生——五个男生,七个女生。第十三个男生又退回到实科中学去了,尽管斯万妮克竭力替他说话。反复补课、家访和心理鉴定。大致是注意力障碍。无奇不有!全是阅读的发育障碍。阅读正字法问题之后又是计算问题。还会有什么?生物学过敏?以前只有体育差或音乐差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