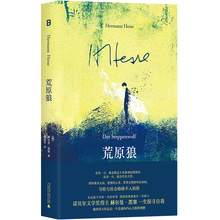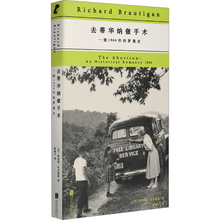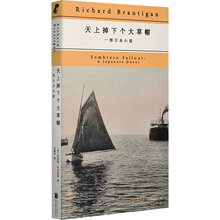这使写作变得粗野。类似生命之前的粗野。你总能识辨它,森林的粗野,与时间一样古老的粗野。惧怕一切的粗野,它有别于生命本身又与它不可分。你顽强奋斗。缺乏体力是无法写作的。必须战胜自己才能写作,必须战胜写出的东西。这事很怪,是的。这不仅是写作,文字是夜间动物的叫声,是所有人的叫声,是你与我的叫声,是狗的叫声。这是社会令人绝望的大规模粗俗。痛苦,这也是基督和摩西和法老和所有的犹太人,和所有的犹太儿童,这也是最强烈的幸福。我一直这样认为。
诺弗勒堡的这座房子,我是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一书改编成电影的版税购买的。它属于我,归于我名下。那是在我的写作狂以前。火山般的狂热。我想这座房子起了很大作用。它抚慰我童年时的一切痛苦。我购买它时立刻就知道这对我是件重要的事,有决定意义的事。对我自己和孩子而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于是我照管房子,打扫它。
花很多时间去“照管”。后来,我被书卷走,就不大照管它了。
写作可以走得很远……直至最后的了结。有时你难以忍受。突然之间一切都具有了与写作的关系,真叫人发疯。你认识的人你却不认识了,你不认识的人你却似乎在等待他们。大概只是因为我已经疲于生活,比别人稍累一些。那是一种无痛苦的痛苦状态。我不想面对他人保护自己,特别是面对认识我的人。这不是悲哀。这是绝望。我被卷入平生最艰难的工作:我的拉合尔情人,写他的生活。写《副领事》。我花了三年来写这本书。当时我不能谈论它,因为对这本书的任何侵入,任何“客观的”意见都会将书全部抹去。我用经过修改的另一种写法,就会毁灭这本书的写作以及我有关它的知识。人有这种幻觉——正确的幻觉——仿佛只有自己写得出写成的东西,不论它是一钱不值还是十分出色。我读评论文章时,大都对其中的“它四不像”这句话感兴趣。这就是说它印证了作者最初的孤独。
诺弗勒的这座房子,我原以为也是为朋友们买下的,好接待他们,但我错了。我是为自己买的。只是到了现在我才明白,我才说出来。有时晚上来了许多朋友,伽里玛一家经常来,带着夫人和朋友。伽里玛的家人很多,有时可能达十五人之多。我要求他们早一点来,好把餐桌摆在同一间房里,让大家都在一起。我说的这些晚会使大家都很高兴。这是最令人高兴的晚会。在座的总有罗贝尔·昂泰尔姆和迪奥尼斯·马斯科洛以及他们的朋友。还有我的情人们,特别是热拉尔·雅尔洛,他是魅力的化身,也成了伽里玛家的朋友。
来客人时我既不那么孤单又更被遗弃。必须通过黑夜才能体验这种孤独。在夜里,想象一下杜拉斯独自躺在床上睡觉,躺在这座四百平米的房子里。当我走到房屋的尽头,朝“小屋”走去时,我对空间感到害怕,仿佛它是陷阱。可以说我每晚都害怕。但我从未有所表示让什么人来住。有时我很晚才出门。我喜欢转转,和村里的人,朋友,诺弗勒的居民一起。我们喝酒。我们聊天,说很多话。我们去咖啡馆,它像好几公顷的村庄一样大。清晨三点钟它挤得满满的。我记起了它的名字:帕尔利Ⅱ。
这也是叫人迷失的地方。侍者像警察一样监视我们的孤独所处的这片无边的领域。
这里,这所房子不是乡间别墅。不能这样说。它原先是农庄,带有水塘,后来成为一位公证人——巴黎的大公证人——的乡间别墅。
当大门打开时,我看见了花园。几秒钟的事。我说好,一走进大门我就买下了房子。立刻买下了。立刻用现金支付。
现在它一年四季都可住人。我也把它给了我儿子。它属于我们两人。他眷恋我也眷恋它,现在我相信。他在屋里保留了我所有的东西。我还可以独自在那里住。我有我的桌子,我的床,我的电话,我的画和我的书。还有我的电影脚本。当我去那里时,儿子很高兴。儿子的这种快乐现在是我生活中的快乐。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