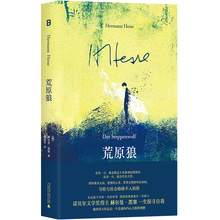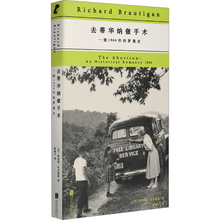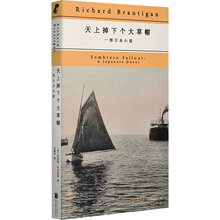男人看着女人在做某些家务事,特别是在准备饭菜时,脸上的表情夹杂着虔诚的敬意、厌烦和畏惧。男人像猫一样害怕扫除,害怕点燃的炉子和扫帚——刷子在地砖上扫动的肥皂水。
为了庆祝当地传统的圣人节日,瑟贡扎克、卡尔科、雷吉斯·吉尼乌和苔蕾斯·多尔尼要从山上下来,到我这里吃一顿南方饭,生菜、塞肉的曚鱼和煎茄饼,除了这家常菜外我还加上烤家禽。
维阿尔住在三百米外一所漆成粉红色的小屋里,这天早上他不高兴。阳台一角摆着配上烤架的熨衣炉,我这位邻居像婚礼中的猎狗一样缩在角落里。
“维阿尔,你想他们会喜欢这个配小鸡吃的调味汁吗?四只切成两半的小鸡,加上欧柏鱼,撒上盐和胡椒,浇上纯酒,再刷上点香草汁,香草的小叶子和味道就留在烤鸡上了。你瞧瞧,它们看上去不错吧?”维阿尔瞧着,我也瞧着。确实不错。被拔过羽毛的、残缺的小鸡的断裂关节处还残留着少许粉红色的血,可以看出翅膀的形状和小爪上鳞纹的嫩皮,这些爪子今早还在欢快地奔跑、抓搔……我那大段话讲完了,维阿尔一言不发。我叹口气,一面搅动我那盘略带酸味的、油汪汪的调味汁。不一会儿,鲜美的肉汁会滴在火上,使我胃口大开……我将不再吃肉,但我想不在今天,而是过些时……“给我系紧围裙,维阿尔。谢谢,明年……”“明年您做什么?”“我要成为素食者。你用指尖蘸蘸我的调味汁。
怎么样?这汁浇在嫩鸡上……不过……今年不行,我太饿了——不过我还是要做素食者。”“为什么?”“说来话长。当某种食肉行为结束时,其他一切食肉行为就会自动消除,就像跳蚤从死刺猬身上撤出一样。
你给我倒点油,慢慢地……”他弯下赤裸的胸膛,因阳光和盐而发亮的皮肤反射出白日。根据他的晃动,他的腰部呈绿色,两肩呈蓝色,就像费兹的染匠。我说“停止”,他便不再倒金黄色的油,挺起身来,我的手在他胸前停了一会儿,就像停在马身上一样,这是恭维。他瞧着我的手,它表明我的年龄——其实它比我的年龄还大几岁——但我不缩回手。这是一只变黑的小手,它的皮肤在指骨周围和手背上变得相当松弛。指甲剪得平平的,拇指喜欢像蝎尾一样跷起,还有伤疤和擦伤,但我却不以为耻。两个指甲漂亮——母亲的礼物。三个指甲不太漂亮——对父亲的回忆。
“你游泳了?你在水边足足游了四百米?现在才七月份,你为什么有那副假期结束的样子,维阿尔?”维阿尔的面孔很端正,相当漂亮,感情上稍有波动就使它不安。他看上去不高兴,但我们从未见他忧愁。
我说他漂亮,因为所有的男人在这里住上一个月都会由于炎热、大海和赤身露体而变得漂亮。
“你从市场上给我带来了什么,维阿尔?对不起,嗯?迪维刚来得及去弄鸡……”“两个甜瓜,一个杏仁奶油饼,还有桃子。无花果——花已经没有了,其他的还没熟……”“这我比你清楚,我每天去葡萄园检查……你太好了。我欠你多少钱?”他做了一个无知的姿势,肌肉丰富的肩头一上一下地耸动,就像正在呼吸的胸部。
“你忘记了?等等,让我瞧瞧甜瓜的大小……这个奶油饼是十六法郎的那种,还有两公斤桃……十四加十六是三十,三十加十五是四十五……我欠你四十五至五十法郎。”“您围裙下是游泳衣?您没来得及游泳?”“游过了。”他很自然地舔舔我的上胳膊。
“不错。”“啊!你知道,这盐可能是昨天晚上的……我们休息一会儿,有的是时间,他们都迟到……”“是的……我能做什么有用的事哩?”“当然,你结婚吧。”“啊!……我三十五岁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