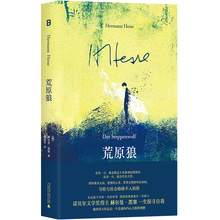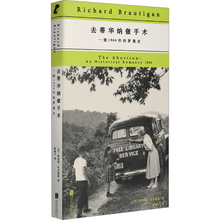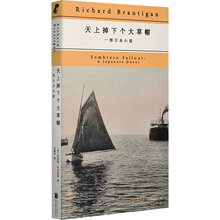“蕾雅!把你的珍珠项链给我吧!你听见没有?把你的项链给我吧!”大床上没人应声。那是一张雕镂的铸铁及铜质大床,像一件盔甲似的在暗处闪闪发亮。
“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项链给我昵?我戴着跟你戴着一样合适,甚至比你戴着更好!”随着大床花边搭扣一响,露出两条玉腕,手腕细腻,两只手慵懒地抬起。
“把它放下,亲爱的,这条项链你摆弄够了。”“我在摆弄……你怕我把它偷走吧?”在阳光透过的粉红色窗帘前面,谢里在手舞足蹈,黑糊糊的,像是大炉子底部的一个可爱的小魔鬼。但是,当他退至大床前时,他的全身,从丝质睡衣到麂皮平底拖鞋,又变得雪白一片。
“我没有害怕,”温柔的细声从床上回答道。“但你会把项链的线弄坏的。珍珠挺沉的。”“它们是沉甸甸的,”谢里认真仔细地看过后说,。那个送你这件宝物的家伙没有耍你。。
他站在挂在两扇窗户之间的墙上的穿衣镜前。仔细端详自己那年轻男子的俊美容貌,他既不高也不矮,青丝秀发如乌鸫羽毛。他敞开睡衣,露出似盾牌般挺着的坚实灰暗的胸脯,他的牙齿,深色眼睛的眼白以及项链上的珍珠闪现着粉红色的光亮。
“把项链摘下来,。女性的声音命令着,“你听见我跟你说的话了吗?”年轻男子面对镜中自己的身影低声地笑着说道:“是,是,我听见了。我很清楚你是怕我强拿了你的项链!”“我才不怕哩。不过,如果我把它送你的话,你是会照收不误的。”他奔向大床,扑了上去:“怎么!我就那么脸皮厚呀。我可是认为,一个男人接受一个女人的一颗珍珠嵌在饰针上或两颗珍珠镶在纽扣上都是愚蠢的,但是要是接受一个女人送的五十颗珍珠,那就太丢人了……”“四十九颗。”“是四十九颗,我识数。你是说这玩意儿我戴着不合适?也就是说你想说我很丑?”他侧脸对着躺在床上的女子,露出一个挑衅的笑来。
他的牙齿小小的,嘴唇湿漉漉的。蕾雅在床上坐了起来:“不,我不会这么说的。首先,就是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的。不过,你能不能别这么蹙紧鼻子笑呀?你是不是非要鼻子边上起上三道皱纹你才满意呀?”他立即止住了笑,把脑门儿伸过去,像个老妖婆似的灵巧地缩起下巴。二人敌对地相视着:她,穿着内衣,肘撑在边饰中,而他,侧身坐在床沿儿上。他心想:“她跟我谈论我会起皱纹,她心里觉得挺舒坦。”而她则在寻思:“他就是美的化身,为什么一笑起来就很丑呢?”她思索片刻,然后便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说了出来:“这是因为你高兴的时候一脸的坏样儿…···你只是因为恶意或嘲讽才笑。这就使你变丑r。你经常是很丑的。
”“这不可能!”谢里怒气冲冲地嚷道。
由于愤怒,他的眉毛同鼻根蹙在了一起,睫毛下,怒目圆睁,凶光毕露,嘴上微微现出不屑但端庄的弓形来。
蕾雅微笑着看到他那副她所喜爱的神态:先是反抗,继而顺从,变化甚快,无法自行其是。她把手放在年轻人的头上,后者不耐烦地摇动着脑袋挣脱这只手的桎梏。她像是在抚慰一只宠物似的轻声喃喃道:“好了……好了……怎么啦……到底怎么啦……”他扑在女子宽阔的粉肩上,用额头,用鼻子,拱那个熟悉的地方。他已经闭上双眼,在寻找被长长的双臂护住的丰乳。蕾雅把他推了开去:“别这样,亲爱的!你要去‘阿尔比’吃午饭,现在都十一点四十了。”“不是吧?我是去老板娘那儿吃午饭?你也去吧?”蕾雅懒洋洋地缩到大床底部。
“我不去,我不想应酬。我午后两点半将喝点咖啡,或者六点钟喝点茶,或者八点差一刻抽支烟……你放心吧,她会有时间跟我见面的……再说,她也没有邀请我。
”谢里一直赌气地站着,这时一脸诡谲地说:“我知道,我知道为什么!我们各有其人!我们有美丽的玛丽一劳尔和她的诱人的小妞儿!”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