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迷
困住了。撞扁了。重量从四面八方压过来,在一堆废铁里挤成一团(你都快跟车子合体了)。可千万别着火,别着火!操,真他妈疼。血红的桥。都怪我自个儿(没错,该死的血淋淋的桥;瞧那座桥,瞧那个开车的家伙,瞧他没看到另一辆车,瞧那两辆车轰地一声撞上了,瞧那家伙骨头都断了,瞧他血流个不停,淌满了这该死的桥。是啊,都怪你自个儿。白痴)。求你了老天,千万别着火。血红一片。一片血红。瞧那人在流血,瞧那车在漏油。水箱是红的,血是红的,满地都是油乎乎红彤彤的血。水泵还在转--操,真他妈疼啊--水泵还在转,可是满地都湿嗒嗒的。现在随时可能有车追尾,把我彻底碾死,不过好在还没着火;有多久了,我想知道撞车之后过了多久了?车;警车(果酱三明治)是果酱三明治,我是果酱车是面包切片。看这男人血流不止。都怪你自个儿。祈祷没别人受伤吧。(不,别祈祷;咱不信神,记着,骂娘就行了。妈妈说:"没必要说那种话。"咱是躲在散兵坑里的不信神的家伙,永远都记得怎么骂娘。好吧,哥们儿,这下算玩完了:你躺在这灰蒙蒙粉扑扑的路上,血流个不停,四周随时可能着火,当然你可能本来也撑不了多久,随时可能有其他车从后面撞过来如果那司机也晕乎乎地盯着这该死的桥所以如果你打算开始祈祷现在真是个好时候可是操他妈的老天--耶稣基督啊疼死我了!好了好了,只是拿这个名字来骂娘,说真的,我不是认真的,我向上帝发誓。好吧,再见吧上帝,你这个混蛋,没错,说的就是你。)说这些就够了,小子。那些字母是什么意思?MG;VS;还有我,233 FS。可是还有--哪儿--谁--?哦,他妈的,我不记得自己叫什么了。有一回聚会也是这样,喝大了,抽多了,起身太猛,这次可不一样(我怎么这时候还能想得起那次聚会的事儿,可是却想不起自己叫啥了?这下麻烦大了。我不想这样。快把我弄出去)。
我看到雨林里的一道峡谷,上面搭着一座爬满藤蔓的桥,深得吓人的谷底流着一条河。有只巨大的白猫(我?)沿着小路跑过来,一跃上了桥;它真白,像只得了白化病的豹子(那是我吗?),大步流星地顺着摇摇晃晃的桥奔跑(我看到的是什么?这是在哪儿?这是真的吗?),像惨白的死亡(应该是黑色的,但我就是悲观主义,哈哈)飞掠而过--
停下来了。视野变成一片白色,开始出现一个个洞;像胶片着了火(火!)困在门里(豹子困在门里?)。停止了,融化了,眼前的景象开始解体(瞧这眼前的景象解体吧),离得再近也看不到了。只剩下白花花一块屏幕。
疼。胸口一圈一圈地疼。像是一个商标,仿佛是圆形的。(我是不是个画在邮票上的小人儿,刚刚被盖了邮戳?羊皮纸上纹着一行字:"的图书馆馆藏"请选择:
a.上帝阁下
b.大自然女士
c.C.达尔文及其子
d.K.马克思股份有限公司
e.以上皆是)
疼。惨白的噪音,惨白的疼痛。一开始是四面八方挤过来的重量,现在是疼痛。啊,生活就是这么变化无常。有人在移动我了。动来动去;他们把我拖出去了吗?开始着火了吗?我到底是死了,被漂白了,还是血流干了?(按时归还了?逾期了?)现在我什么也看不见(现在我什么都能看见)。我躺在一片平原上,四周都是高山(也可能是躺在床上),四周都是……机器?人?其中之一;两者都是(比如,人,把思维放开的话,还真全是一回事。差远了)。谁在乎这个?我在乎吗?妈的,我可能已经死了。可能真有来世……唔。可能其他的东西都是梦(是啊,没错),我醒来就会看到("黑暗的车站")--那是什么声音?
你听到了吗?我听到了吗?
黑暗的车站。又来了。像是火车鸣笛的声音;有什么东西正要出发。什么东西正要开始,或者正要结束,或者同时开始和结束。黑暗的车站正冲我过来。或者没有。(我不知道,我刚到这儿。别问我)。
黑暗的车站。
噢,好吧……
变形记
一
黑暗的车站,空旷而颓败,列车徐徐驶离站台渐行渐远,汽笛声回荡消失在远方。黯淡的夜色之下,汽笛声听起来潮湿而冰冷,仿佛列车排出的团团蒸汽将自身的特质灌入了这声响。茂林密布的群山吞噬了汽笛声,如同厚布吸收了细雨。唯有微弱的回音经由森林中间或露出的悬崖峭壁和碎石坡地上涤荡而来。
汽笛声最终消失之后,我仍然面朝废弃的车站,不愿意转身面对身后那静默的马车。我侧耳倾听,试图捕捉逐渐远去的列车在冲下陡峭的山谷之时引擎发出的最后声响;我想听到列车的喘息声、活塞的咔嗒声以及气阀的嘎嘎声,然而静谧的山谷中一片沉寂;火车的声响全部消失了。车站上方,尖屋顶和粗烟囱矗立在阴沉的天空下,在灰色背景下描摹着黑色的笔触。几缕轻烟在山谷潮湿冰凉的空气中缓缓散开,飘荡在黑色石板和被煤烟熏暗的砖块上空。煤炭燃烧的气味和蒸汽的潮湿气息萦绕在我的衣服上,经久不散。
我转身看向密封的马车。它被漆成灵车般的黑色,从外面上了锁,还用厚重的皮带捆绑加固。车后,两匹马紧张地踏着铺满落叶的路面。它们摇晃着黑色的脑袋,转动着巨大的眼珠。鼻孔翕张,喷出阵阵白气;马具叮当作响,带动车厢微微摇晃,犹如行进中的列车。
我检查了一下车厢紧闭的门窗,拽了拽紧绑的皮带和金属把手,然后爬上车夫的位子,拎起缰绳。我盯着面前通往森林的狭窄小路,执起鞭子,犹豫片刻,又放了回去,不愿意打破这山谷的寂静。我摸到木制的刹车杆。身体出现了某种古怪的生理现象:我双手潮湿,却口干舌燥。车厢摇摇晃晃,或许是因为那两匹马一直在不安地躁动。
头顶的天空阴翳而沉闷,四周的山峰布满密林,峰顶被团团云层遮蔽,那犬牙交错的山顶与锋利的山脊仿佛被轻柔的蒸汽托了起来。四周散落着暗淡的光线,没有影子。我拿出表,意识到即使一切顺利,我也无法在天黑之前完成旅程。我拍拍口袋,里面有火石和引火纸。夜色降临之后,我也能弄出光亮。车厢再次摇晃,两匹马骚动着,不停地刨着地面,脑袋四处乱转,白眼球鼓得厉害。
不能再拖了。我松开刹车,策马小步前进。车厢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摇晃颠簸,离黑暗的车站越来越远,渐渐没入森林之中。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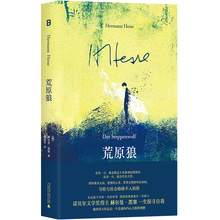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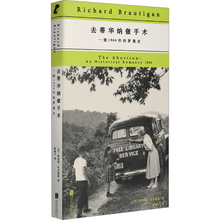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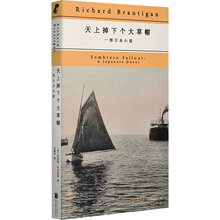

——泰晤士报
班克斯丰富的想象力使我们在人类最深的梦魇中让挖掘寻找趣味成为可能
——时代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