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害怕,怕这副躯壳再也不听从我的意愿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意识到死亡,意识到人类只是整个自然界的一部分,出生与死亡是自然的过程。可惜的是,所有你在乎的人不能一起走,总有个先后。
“对不起,”我喃喃地说,双眼死死地盯着身后的一堆落发,“没想到这么快就剪完了。”女理发师抬眼看着镜中的我,不置一词。
我带了些自己的照片给她,这些照片是三个星期前好朋友马丁为我拍摄的,当时我还拥有自己的头发,自从开始接受化疗,我的头发细胞1就在与药物的轮番作战中输了个精光。
这家假发造型美发店非常好找,一进入阿姆斯特丹医学中心的入口大厅,你就能发现,因为大厅的门口高高挂着广告牌:“如需试戴请上二层”。店面的布局也很合理,肿瘤患者接受治疗后可以直接进来。
我希望理发师能知道,我最喜欢什么样的发型。照片就平铺在桌上,可照片里的女孩却越来越陌生。理发师给我拿来一本假发造型册和一顶蓬松金发,不经意地压在照片上。
“这款怎么样?”
“绝对不行。”
镜子里是理发师泄气的神态,可说真的,试了半天,这里所有的假发真的都不行,总是把我搞得像个有变装癖的男人。不一会,她又拿来一顶黑色的长款假发帮我戴上,镜子里她期待地看着我,我却只联想到了“枪花”乐队的吉他手2,难道我要顶着这样一头鬃毛?太可怕了。
这个尴尬的时刻,我的妈妈、姐姐和最好的朋友安娜蓓尔都陪在我身边,大家都觉得有些难以接受,没一个人开口说话。安娜蓓尔拿起一顶假发,乱放到头上,她滑稽的模样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尴尬的气氛也因此消失了。
我和姐姐都喜欢把头发使劲向后梳,然后在额前简单地留几缕刘海,我凝视着姐姐高高的棕色发髻,健康油亮,看起来神气极了。忍不住将目光移向旁边的安娜蓓尔,她的一头黑发浓密茂盛;看向妈妈,她留着一头利索的短发;再望向镜中的自己,只剩下一撮毛。三个星期过去了,快得像飞一样,但我始终没搞明白,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在这里做什么?
我想逃,把自己藏在家里,藏在四面墙围起来的小天地里。可以不再面对我的疾病,还有周围人的反应,因为他们的态度无时无刻不提醒着我:嘿,别忘了你的病。邻居们总是露出同情的目光,菜贩子也会塞给我超大包的维生素,朋友们把我紧紧拥在怀里,亲戚们围着我哭泣。想到这些,我的眼眶不自觉就潮了,死命地盯着镜子中的自己,鼓鼓的嘴唇此时抿成了一条开口向下的抛物线,苦闷地挂在脸上。任由发型师在我头上鼓捣,看她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她摆弄得越久,我的嘴唇就抿得越紧,心里对这一切也就更加怀疑。镜子里的完全不是我,简直没法看。
过了好久终于可以离开试戴间了,离开时头顶了一个属于我妈那代人的发型。丑得跟个锅盖似的,而且惹得我头皮发痒。我不再是苏菲了,找不到半点儿过去的影子,我现在根本就是一个呆板、无聊的老处女,刚从一个呆板、无聊的乡下地方上来。
可女发型师一直在我耳边兴奋地向我说着什么。我们站上电梯,下楼回到医院的大厅里。直到这时还能听到她在我耳边说:“你要先熟悉一下,不可能明天醒来就能适应这一切。把戴假发当成一种游戏,试试看,不到两个星期你就找回自己了。”
是啊是啊,找回自己。我找回的难道就是眼前这个呆板的老处女?我,干脆改名为史黛拉3算了。我转身望向妈妈,她的眼里早已经噙满泪水。
女发型师已经在假发行业里干了二十年,她说自己是本城少数几个曾经与来自中国、日本的潮流发型师一起工作过的专业人士。“那边流行俏皮、时髦的发型,非常适合你这个年龄的女孩。”
我在电梯里还忍不住照镜子,寻找她全力打造的潮流女孩,压根没找到。我只看见一只头顶假发的灰老鼠。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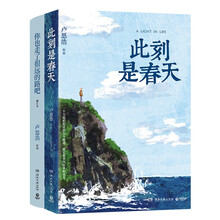








——德国《明镜周刊》
凭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勇气,直面死神,苏菲为整个欧洲作出了榜样。
——法国媒体
苏菲,谢谢你,谢谢你的诚实、毫无保留和勇气。
——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