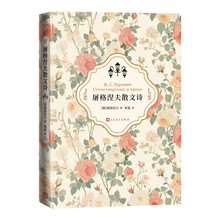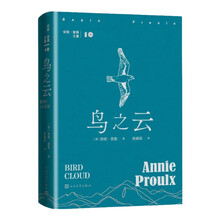艺术家的肖像 幼儿期的容貌特征一般不会在青春期的肖像里再现,因为我们是如此多变,我们只能也只愿在铁的记忆方面构想往昔。然而,往昔一定包含着无数个现在的流动连续,是一种存在的发展,在这种存在中我们实际的现在只不过是一个阶段而已。而且,我们这个世界主要是依据胡子和身高特点来辨认熟人的,多半与其中的那么一种人相疏远,这种人通过某种艺术,依靠尚未定型的某种思想过程,寻求从个人化的物质团块中释放出作为他们个性化律动的东西,即他们各个部分最初的或外表的联系。但是,对这些人来说,一幅肖像并不是一纸身份证,而是一条情感曲线。
理智的运用被流行的看法提前了大约七年,因此不容易准确断定这幅肖像的像主的自然感受力是在多大年纪开始醒悟永恒之诅咒、忏悔之必要和祈祷之功效等观念的。<以牺牲所谓“常识 ”为代价,他所受的训练早就开发了一种极为强烈的精神责任感。
他像挥霍的圣徒一样耗尽钱财,以射精般的激情令许多人惊奇,也以修道院的高傲气派触怒了许多人。有一天,在玛拉海德附近的一个树林子里,一个工人惊异地看见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正沉迷在东方的姿态中祈祷。确实经历了很长时间,这个少年才领悟到那种最畅销的美德的本质,那种美德使人能够心安理得地赞成各种主张,而无须根据它们来整顿个人生活。宗教的消化价值他是从不欣赏的,他选择—— 因为那更适合他——那些较贫穷、较卑贱的修道会,在其中一个忏悔者,至少从理论上讲,似乎不那么急于显示自己是一个世俗之人。但是,尽管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迫使他一改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热情奔放,羞愧地转向内心,当进人大学学习的时候,他仍然从虔诚的修行中得到抚慰。
在这个时期前后,所有的来者都被灌输了一种谜,以防止危机的产生。现在他思维敏捷,足以认识到他必须秘密地解决他个人的事情,从此谨言慎行便成为轻松的赎罪苦行。他懒得谈论丑闻,不愿显得对他人好奇,这有助于他真正的起诉,而且也并非没有一种令人满意的英雄的味道。他猜想,正是他后来称之为赎罪者的那个根深蒂固的利己心的一部分在他身上汇聚了人类社会的种种行为和思想。
难道少年的心灵是中古式的,能够如此预测阴谋?野外运动(或者它们在心智世界的通讯员)或许是最有效的疗法,但是对这位以一跃来躲避嘴里哼哼叽叽脚穿靴子的幽灵、异想天开的理想主义者来说,选择对他不利的场地进行模拟狩猎对他既不公又荒谬。
然而,在这迅速坚固起来的防御背后,这敏感者做出了回答。让那一群敌意之犬跌跤打滚,咻咻吸嗅,追踪着猎物来到高原;那儿是他的地盘;他从闪耀的多叉鹿角上向它们抛去蔑视。>在这个意象中有明显的自吹自擂,但也有一种自满自得的危险。因此,他忽略那合唱中喘息者呼哧呼哧拉长的低音——无论怎样的距离也无法使之悦耳动听,开始对年轻人作傲慢的诊断。他的判断精妙、审慎、尖锐;他的判决如雕塑。<这些年轻人从一个乏味的法国小说家的猝死中看到了伊玛纽埃尔的手——上帝与我们同在;他们赞美格拉德斯通、自然科学和莎士比亚悲剧;他们相信,在擅长外交的教会里,应该按照日常需要调整天主教教义。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上级的关系中,他们表现出一种神经质的(只要有权威的问题存在)非常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他注意到一个班级的半赞赏、半非难的态度,含蓄地向其他人发誓保证节欲,<在他们中间(有传闻说)放荡的生活并非不为人知。尽管信仰与祖国的结合在这个容易燃起狂热的世界里任何时候都是神圣的,但出自戴维斯之手的一个对偶句,谴责了最不驯服的性情——却从未失去人们对它的喝彩,而在回忆时,人们对麦克马纳斯的崇敬几乎不亚于对卡伦红衣主教的崇敬。>他们有许多理由尊重权威;即使<一位学生被禁止去看《奥塞罗》(他被告知“戏中有些粗俗的言语”),那又是多么小的考验呢?更确切地说,那难道不是留心提防的监督和关心的证明吗?他们难道不相信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中,这样的监督将继续、这样的关心将保持吗?权威的行使有时可能是(难得)有问题的,而它的用意呢,绝不会有问题。因此,有谁比这些年轻人更感激不尽地答谢某位和蔼的教授的戏谑或者某位门房的粗暴呢?是谁更热衷于想方设法地爱护并亲自抬高艾尔玛·梅特的声誉呢?对他来说,他正处在困难时期,被剥夺了财产,穷困潦倒。至少在沉思中,他已熟知高贵,而在这种生活方式里他感受到了一切卑劣的东西。一个热心的耶稣会会员建议在爱尔兰黑啤酒厂设一个牧师职位:毫无疑问,要不是他想(用中世纪经院学者们的话来说)做一件艰难的善事的话,一个啤酒厂的牧师任命不会对一个令人赞叹的社团只抱轻蔑和遗憾的心理。也许他应该在各种社会群体中寻找慰藉,以求在世俗之人中间增进思想,而不是在被如此众多愚蠢或古怪的童贞女包围着的温暖的宗教社团里寻求肉体的安逸。
而且,曾对着自己的狂喜而颤栗的性情是不可能屈从默认的,一个灵魂也不可能注定要受奴役,何况美的形象已如纱幕降落在他的命运之上。在早春的一个夜晚,站在图书馆的楼梯脚下,他对他的朋友说 “我已经离开教会”。>当他们臂挽着臂穿过大街小巷走回家的时候,他讲述了他是怎样穿过阿西西的一道道大门离开教会的,他的话语仿佛是那些大门关闭的回声。
接着便是放纵:穷乞丐的简单历史很快就被抛到了脑后,他与最狂妄的人为伍。修道院长约阿钦、诺拉人布鲁诺、迈克尔· 森狄瓦基乌斯,所有这些创始的大主教都在他身上施展了魔力。他下到斯威登伯格的地狱中去,还自贬到圣十字约翰的忧郁之中。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