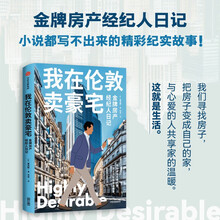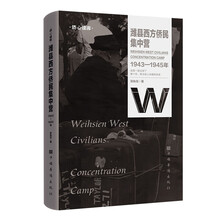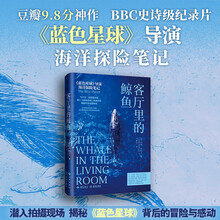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和非虚构等称名及其相关的文体话题,近年来论议颇多,甚至还引起了一些争议。这也说明,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纪实文学,或当下主要包括报告文学的纪实文学,并不“沉寂”和已经“走向衰落”。今年八月,《深圳商报》记者谢晨星,根据《红岩》杂志社“红岩文学奖”计划取消报告文学单项奖的新闻事由,采写了《报告文学是否走向衰落?》的访谈,谢晨星以“新媒体冲击报告文学”,“批判性大大减弱”、“数量虽多精品却少”等为基本的视点,表达了记者判断的取向。谢晨星所说三点,虽是实情,但不足以此来判定报告文学走向了衰落。在我看来,以报告文学为主体的纪实文学,非但没有衰落、沉寂,而是活跃而热闹的。我们评价报告文学,基本的做法是应该回到报告文学存在的现场,在贴近中发出真实的声音。社会转型的深化,生成了现实的多向开放。我们不能用文学中心时代留存的文学批评心理定势,观察、评价边缘化的文学。现实决定文学存在。报告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时代文体。现实的无限丰富与复杂,需要报告文学记写;多变多质、跃动不居的生活,又成为这一文学样式发展的直接源头和永动力。读者对于纪实文学的持续需求,反映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这为纪实文学的发展导入了不可或缺的读者市场因素。当然这些情况不能直接推导出纪实文学的必然繁荣的结果,更不能说明纪实文学创作的高质量。“数量虽多精品却少”确实是纪实文学的现实,但其实这也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真实。
一
我在这里使用纪实文学这个概念,这是一个为人非议的指说。其实,满足一定的逻辑前提,这是一个很清晰的范畴,并不应该有歧义。纪实文学作为一个“类”和作为报告文学一种“体”,大小有别,它们之间具有属种关系。显然报告文学一体只是纪实文学大类中的一种。使用纪实文学这个指称,言者如我是有逻辑指向和重点的。通常而言,报告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新闻文学,而80年代以来的历史报告文学的泛化,使得这样的诠释陷于某种尴尬。我们可以说,董汉河《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钱刚《海葬》等历史题材的纪实作品,为历史报告文学,因为这些作品其现实的意旨是很明显的,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特殊对话。但是,我们却很难说王树增的《1901》、《1911》等作品就是报告文学。如果说是报告文学,那也是一种“非典型”的报告文学。因此,从学理的逻辑看,将这样的作品统说为纪实文学,或可避免文体命名方面的尴尬。所谓历史的报告文学,其重要的意义是表示纪实文学叙写空间的开拓。当然,纪实向历史的开掘是有限的,失范的历史纪实必然会使纪实走向它的反面虚构,而虚构无疑就取消了纪实文学。在我看来,大致规范的历史纪实写作,其基本的要求是主体在还原历史存在时是“够得着”的,无需以虚构再造历史。这种“够得着”首先在叙事对象的时间上是适度的,大致而言这种适度的时间为百年上下。其次在具体的写作中是可纪实的,即历史的存在具有切实的史料、文献记载;作者可以通过采访与过往存在具有关联的人物,走近历史,再现历史;作者还可以通过踏访历史遗存,感知当年人与事活动和发生的现场。
2012年历史纪实一如既往地在纪实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份额。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熊光炯《心远——一个教育世家的百年沧桑》,不是一般的教育史叙事,作品以名副其实的“教授村”切入,以一个教育世家的“百年沧桑”串联诸多的叙事要素,将“教育世家”的本体叙事与百年中国史大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构造了历史纪实的宽度。李青松《开国林垦部长》是一短篇,采用的是历史小叙事写法,饶有滋味的细节和场景,呈现了开国部长可敬可爱的精神形象。这些作品,各有特色地体现了“够得着”、可纪实的历史非虚构写作的基本规范。
二
近年以纪实文学、非虚构置换报告文学的另一个背景,可能与说事者对报告文学文学性不足不满有关。当然,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性,我们不能以小说的文学性要求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我们似乎也很少讨论小说的文学性。但既为文学,报告文学就应该满足文学的一些基本的要求。文学与新闻的最大不同是,文学的表达更强调主体的个人性。新闻的报告文学常常成为为一种模式写作,文学的滋味流失;文学的报告文学需要强化主体的文学思维和写作的文学元素。我并不认为置换称名就能解决报告文学文学性不足的痼疾,但非虚构所要求的主体对于客体的体验、纪实文学对于文学性的强调,都是积极的,有价值的。实际上,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与作家的文学思维、文学能力直接关联。《你可知道,那草帽在何方》是李迪采访公安部“清网”行动的受命写作。通常此类写作新闻的意味较强。而李迪的作品题目就显示他思维的文学惯性。这一题目既贴合了作品内中的细节,又酿造了作品某种叙事基调。在抓捕的故事演进中,进行真切的人性观照。作品的尾声,“模糊的泪眼,仿佛看见那顶草帽,随风飘荡,落入深谷。紧跟着,响起凄绝悲怆的歌——妈妈,那顶草帽,它在何方,你可知道,就像你的心失去了,我再也得不到……”,竟是这样地摄人心魄。在资讯发达的今天,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优势已不明显,如何优化其文学性的表达,形成非虚构自在的文体魅力,《你可知道,那草帽在何方》等作品,会给写作者以有益的启示。
三
我不是报告文学的取消主义者。报告文学不会消亡,自然这一文体也不可能人为取消。我只是认为,在纪实文学类中的报告文学这一体,它具有自身独特的体性特质。这样的体性特质决定了报告文学的特异而重要的价值。在我看来,基于非虚构的现实品格,是报告文学文体的核心价值,是报告文学之谓报告文学的文体支撑。这是报告文学的文体常识。但常识有时是最容易遗忘的。当前报告文学创作中最缺失的就是现实品格。报告文学的现实品格,要求作家能主动回应社会的关切、介入现实、呈现真相。何建明是一个高度重视报告文学现实品格的作品。《三牛风波》是对现实作出快速反应的有为之作,揭开风波,还原真相,在贴近对象中,反思风波。《国家》是现实大叙事作品,将2011年从利比亚撤侨这一“中国外交空前行动”,作了详尽的跟进报告,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将更为凸显。具有现实品格的报告文学,不能只为评奖而只写作“主旋律”的作品,还要触及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反映现实的原生态。报告文学不能只写成功的、发达的,也要写失败的、落后的,写出完整的现实。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我特别看重2012年3月《文汇报》“乡土中国”推出的关于乡村的“口述实录”。作者曾维康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报告文学的领地中是一个新人,或许这样的写作在其人生中只是一种“穿插”,但是作品对乡村实生活的朴素叙说以及蕴藉其中的思考,在一些专业或成名的报告文学作家那里是不多见的。具有现实品格的报告文学,不仅要呈现有意义的当前生活,还要能对报告对象作出理性的深刻的解释,也就是说作品需要具有思想的力量。现在的报告文学较多的是一种“平面写作”,作者不注重或没有能力对写作对象作深度的思考,少有主体性的思考。深刻的、新颖的思考有赖于新的思想资源,新的知识背景。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现代日常的今天,有为的报告文学作家,应当具有更宽广的视野,具有更强更深的思考力,对于报告对象尽可能给出新的解释。在现在活跃的一线报告文学作家中,陈启文无疑是一位真正的在场主义写作者。他不仅在叙写客体的现场,也在思想的现场。《北京风暴》是2012年体现报告文学现实品格的一个样本。“7?21”北京暴雨事件是一个重大的当下题材,但少有报告文学加以具体的记写,更很少有反思意味很强的作品。陈启文在灾后深入现场,以自己的方式观察、思考、呈现事件。作品不仅记录暴雨所造成的巨大破坏,讴歌救灾中的英雄,更带给我们深刻的思考。在陈启文看来,可以说“一场暴雨检验公民社会的成色,如暴雨中闪光的‘北京精神’”,“但比这更重要的还是北京‘7?21’暴带给我们的是集体震惊和反思”。在“充满了人性温度的故事或细节背后,还有人性的另一种拷问。拷问的其实不是人性,而是制度。制度也是有人性的,有温度的,又如何让我们的制度进一步人性化?”这样的思考不是多余的,而是必须的。报告文学应该具有这样的品格。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