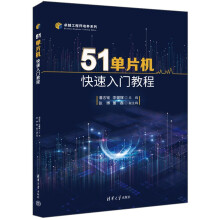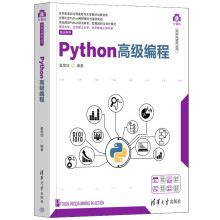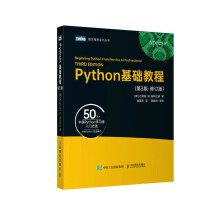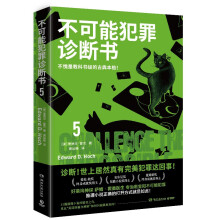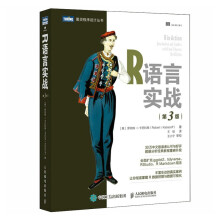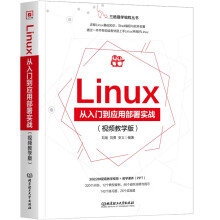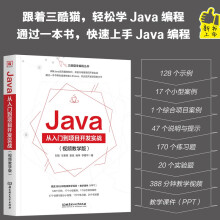“你知道吗,姨,离婚几年了?我想见孩子,从来就没有顺利接走过一次!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理由为难我,我想孩子可以忍,但孩子也想我,您知道吗?您能理解吗?童童悄悄拿爷爷的电话给我拔电话,换作是您,您会怎么做?可以不管孩子的感受吗?”
“我理解,孩子是你生的,你想他那是自然的,谁也代替不了母亲的爱,孩子想妈妈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也是做妈妈的,我能理解。”她回过头来对牟青说,“让小孙带两天吧,她是亲妈,那还能错得了啊?”
牟青不说话,我看屋檐的柱子边站着的那个女人进了屋,其实我很明白,牟青是想在她面前表现得男人一些,好像这样才能证明她在他心中的位置。
“今天就让童童跟着妈妈去住两天吧,”牟青的姨说,“我做主了,让他们娘俩儿好好亲亲。好吗,小童?”
童童点点头答应了。
上了车,我擦掉泪痕,转头问童童:“刚刚妈妈那么凶,我看你一直在来回地搓揉你的小手看着我,你害怕没有?”
童童摇摇头说:“没有。”
“对不起,好孩子,妈妈不想这样的。”我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握着童童热乎乎的小手。
“嗯,我知道,妈妈。”童童小大人的样子说,“你知道吗?我都快想不起你来了,为什么你不让我们在楼上住?我那个妈妈说你不要我了,妈妈,你不要童童了吗?”
“不是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我的眼泪又涌出来,我咬着牙控制着,“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儿。”
电话响了,我定了定神接听电话,是陈岩,他说:“在忙什么呢?我在西城了,你在哪里?”
“我刚刚接我儿子了。”我使劲吸了吸鼻子,故做轻松。
“你哭了吗?怎么鼻音那么重?”
“没有,你在哪里?”
“我在石油大学操场,准备踢球呢,你来看吗?你带孩子来看我们踢球吧,男孩儿一定会喜欢的!”陈岩的语气富有感染力。
我回过头来问童童:“要不要去看踢球?”
童童点头说:“好。”
“好吧,暂时我也没想好去哪里玩,就去看你踢球吧。”我在下一个路口打了转向灯向石油大学驶去。
在商店给童童买了瓶饮料,我们来到石大操场的看台上。远远的,陈岩向我们挥手,还是那天他穿的那身白球衣红裤子足球鞋。童童乖乖地坐在我身边,每次接他回来,总要有大半天他还是会非常拘谨,时间再久点他才会放松,像找到感觉了,但往往还没亲够呢,牟青又打电话说要接他回去了,他尽量让我和孩子呆在一起的时间不要太长,我一直不明白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表面上说是为了童童,其实更多的是怕那个女人不高兴吧。
说实话,我没有心情看陈岩踢球,我轻皱着眉头,我的目光不知道飘在哪里,好像不自觉地叹了口气,童童小心翼翼地看看我,我努力给他一个微笑,说:“没事儿,看到那个向你挥手的叔叔了吗?等你长大一点儿让他教你踢球好不好?”
“嗯,好。”童童不知道是不是真喜欢,表现得没有个性,什么事儿都看大人的脸色,有时甚至带着讨好的表情。我的心里难过得要命,这样的时候,我总是很恨我自己,如果当时我可以预知童童在这场失败的婚姻中受到的为难和伤害,我会不会选择离婚?陈岩踢了没多久,就替下了,他拿上那个包,还是手提一瓶水,脸上有汗也不擦,走到我们身边来。
“怎么不踢了?”我问道。
“不踢了,认识一下你的宝贝儿子。”
说着,陈岩蹲下来对童童说:“我叫陈岩,你呢?”
童童看看我,我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和微笑,他回头对陈岩说:“我叫牟童。”
“是吗?这么好听的名字,你几岁了?”
“五岁了。”说着还伸出五个手指来比划了一下。
“哈哈,童童好可爱,在哪里上幼儿园?”
“石油大学幼儿园。”
“是吗?太好了,叔叔有个同学也在你们幼儿园当老师呢,童童在哪个班啊?”
“在中(二)班。”
“哦?中(二)班啊。童童,你看这样好吗?我们一会儿出去玩玩,然后晚上叔叔请你吃肯德基怎么样?”
童童又望了望我,看我点点头他才说:“行。”
我们去了黄河边,那里树木繁茂,空气清新,陈岩和童童比赛打水漂,光着脚丫站在满是淤泥的河床上双脚来回踩,踩到出了水儿;一会儿又拿根树枝在河床上跑着画着,信手涂鸦。陈岩说带着童童找刺猬,他们沿着黄河岸边往南走,我跟在后面,不一会儿陈岩把童童扛在肩膀上,让童童骑着他的脖子,他开始飞奔。吓得童童又紧张又开心地哇哇乱叫,多久了童童都没有这样开心过。
从黄河边回来,已是华灯初上,童童竟然在旁边的座位上睡着了,下午玩得既开心又很累,睡得特别沉,我轻轻叫他,也醒不过来,陈岩问:“你们住几楼?”
“四楼。”
“干脆我送你们回去吧,你抱他到四楼可是够累的。”我想想也没有理由拒绝。
到了家里把童童安顿好,他问能用一下卫生间吗?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