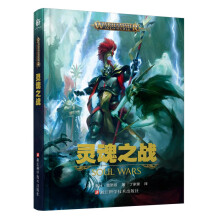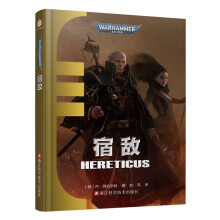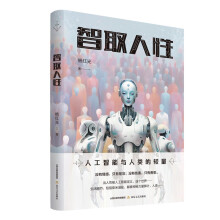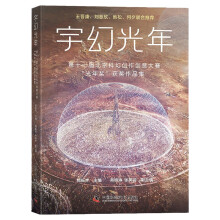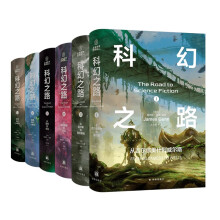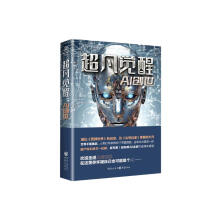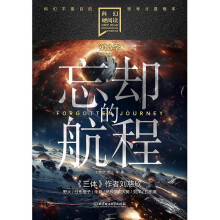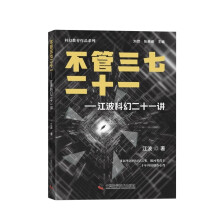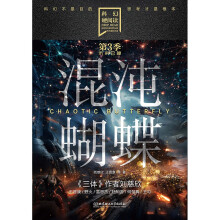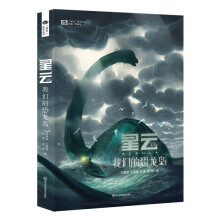《归来:父亲、儿子和他们的土地》:
1.暗门
2012年3月,清晨。开罗国际机场。我母亲、我妻子戴安娜,还有我并排坐在候机厅里固定在瓷砖地面上的椅子上。飞往班加西的835次航班将正点起飞,广播里是这样说的。我母亲时不时焦虑地看看我。戴安娜看起来也忧心忡忡。她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胳膊上,笑了笑。我应该起来走走,我对自己说,但我的身体却一直僵硬地钉在那里。我从未有过如此强的定力。
航站楼里几乎没什么人。只有一个男人坐在我们对面。他有些胖,样子很疲倦,大约五十几岁。他的坐姿里有种耐人寻味的东西——放在大腿上紧扣的双手,微微向左倾斜的躯干——透出一种听天由命的味道。他是埃及人还是利比亚人?他是要去邻国游览还是在革命结束之后返乡?他对卡扎菲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许他属于那种无法确定自己立场的人,愿意把一切都埋在心底?
广播通知再次响起,登机时间到了。我发现自己排在最前面,戴安娜在我身边。她不止一次带我回她出生的北加州。我了解她成长的地方,那里的植物,那里的阳光,还有那里广袤的土地。现在,我终于可以带她回自己的故乡了。她的随身物中有两台最爱的相机,一台哈苏和一台徕卡,还有上百个胶卷。戴安娜非常敬业,只要抓住一点线索,就一定要追根溯源。她的这一点让我既高兴又担心。我不愿再给利比亚什么,它已经从我身上拿走了太多。
母亲沿着窗户边走边打电话,从那里可以看到外面的跑道。航站楼里渐渐挤满了人——大多数是男人。我和戴安娜站在长队的最前面,身后像一条蜿蜒的大河。我假装有东西忘了拿,把她拉到了一边。突然之间,我感到,多年之后回乡并不是个好主意。1979年我们举家迁离故土,已经整整三十三年了。现在的我和八岁的我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希冀搭乘飞机来完成这次跨越,无疑是个鲁莽的决定,它将夺去我多年来努力培养的能力:如何远离我所爱的人和土地生活下去。约瑟夫·布罗茨基是对的,纳博科夫和康拉德也是对的,他们都是从未回乡的艺术家。他们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方法抵御乡愁。被抛在身后的一切都已经销蚀在时光里。回归,你将会面对那种缺席感,或者直面你视若珍宝的东西已然消失殆尽的境况。当然,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和纳吉布·马哈富兹也是对的:他们从未离开过家乡。离开,就意味着你的根被拦腰切断,变成一段枯死的树干,坚硬而空洞。
但当你无法离去也无法回归时,你该怎么办?
2011年10月的时候,我曾想过永远不再回利比亚。当时我走在纽约百老汇大道上,迎着凛冽的急风,这个想法突然就冒了出来。它看似无懈可击,仿佛是我的大脑独立制造出来的。就好像少时酒醉后感觉自己英勇无敌一样。
一个月前,我受巴纳德学院之邀去纽约做关于离散小说的演讲。其实,我和这个城市颇有渊源。我父母在1970年春天搬到了曼哈顿,当时我父亲被任命为利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首席秘书。那年秋天,我出生了。三年后,也就是1973年,我们回到的黎波里。那以后,我去过四五次纽约,但每次时间都很短暂。所以,虽然是回我出生的城市,可对我来说它依然是个陌生的地方。
在我们离开利比亚的三十六年间,我的家庭和我曾与不同的城市结缘:内罗毕,我们1979年逃离利比亚时落脚的城市,从那以后我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回去;开罗是第三年我们开始那无限期的流亡生涯后所居住的城市;罗马,我们的度假城市;伦敦,我十五岁开始在那里求学,也是我为生计打拼了二十九年的地方;巴黎,三十出头时我厌倦了伦敦之后移居的城市,当时我曾发誓永远不再回英国,但仅过了两年又回去了。在这些城市生活期间,我在脑海里勾勒过一幅画面:有一天我在那个遥远的岛屿曼哈顿,那个我出生的地方,静静地生活。我想象着,也许在晚宴上,或咖啡馆里,抑或是游泳馆更衣室里,有一个新朋友问我那个老掉牙的问题:“你是哪里人?”而我不经意地回一句:“纽约人。”在这些幻想里,我看到自己很享受这种魔术把戏般亦真亦假的表述。
我应该在四十岁那年搬到曼哈顿,那时利比亚开始四分五裂,而且我也应该在9月1日那天搬到曼哈顿,因为在1969年的那一天,一个名叫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年轻上校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而我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东西——我居住的地方、我书写的语言,还有我写这本书所用的语言——也都随之发生了改变:这些都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有某种神圣的意志在起作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