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在远方? 1926年的深秋,北京大学年仅十九岁的学生王凡西离开了北京,对政治实践充满了激情的他,对于北京“理论学习上的苦闷,学生运动的单调(和南方的火热斗争相比)”再也无法忍受。在北洋军阀治下的革命青年,对于那个激情燃烧的充满火与剑的南方革命的中心——广州产生了无限的向往,就像昆德拉的小说《生活在别处》寓意的那样,此时此地的生活总是无聊而倦怠的,而别处的生活却是诗意而浪漫的。其时北伐在进行之中,革命胜利似乎在望,而后方的革命圣地却已经弥漫着“分田分地真忙”的世俗气味。这让满怀赤子之心的王凡西深感失望。这是一幅怎样令人沮丧的“后革命情景”: 凭我这双带点清教徒色彩的眼睛看,这儿的革命者不够革命。他们没有那份严肃气,无警觉心,更没有悲愤情怀。享福与贪欢心情很普遍,生活相当随便。对我有似至宝的革命书报,这儿认真阅读的人却仿佛很少;年轻人聚在一起,女人问题谈得比政治问题起劲得多;孙中山的那两句有名口号,这儿已被普遍地改为“恋爱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革命及其理论问题永远不会听人提及。酒食征逐与方城作战成了干部们假日和工余的主要功课。恽代英的艰苦作风虽为人乐道,然从而效之者却少而又少。……人们将革命工作看成为官职,因之将革命的参加者看成简单谋差使的人。 在革命动员中充满神圣感的政治,居然如此迅速落潮为充斥着世俗欲望的此岸狂欢,革命成了一种谋生的职业和现世的交易,这在理想主义者王凡西看来无疑是在降格革命和矮化革命者。 这自然并非偶发的现象,而确实是那个天地玄黄的大时代一种让人惊异的革命景观,革命既解放身心,又在锻造一种新的锁链,革命既是浪漫主义的慷慨悲歌,又是理性的精心计算,革命既是对世俗生活响亮的拒绝,可同时又在追逐一种新的生活秩序。在这样一个大熔炉中,一个怀抱真诚的革命者就像被置入炼狱之中一般,身心俱疲。张国焘曾经说,1925年的广州,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各种新旧事物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在街面上,一方面可以看到烟赌馆林立——作为军队财政和税收的主要来源,少数私人汽车为军人所有,载着军人和军眷在马路上疾驰,旧式文学和黄色书刊占据出版物多数;另一方面,街头巷尾又随处可见五颜六色的革命标语,十字街头往往横挂大红字书写在白布条上的动人口号,熙熙攘攘的人行道上,走着系红领带的黄埔军人和穿中山装的革命者,工会和民众机构的门前,装饰得色彩缤纷,如繁花绽放。 武汉是20世纪20年代北伐革命的另外一个中心,作家黄白薇曾经饱含深情地追忆武汉的革命时代:“那个可追忆的黄金时代哟!每个青年的热血在沸腾,青年的血充实在伟大的中国的命脉里,活泼,生动,发光……欢喜的灵魂在跳跃,国魂也在跳跃。整个武汉的民气都疯狂了,醉着澎湃热烈的革命高潮。”武汉城里的革命青年男女手牵着手,走在长江河畔,迎着夏夜的微风,一起唱着情歌。他们热烈地谈着国家的未来,他们开怀大笑,他们相互取笑,他们正在恋爱。“人人都知道这是革命,革命啊,革命的赐福,革命的享受呵!”革命高潮中的武汉军校,从上千名女知识青年中选拔了两百名,编成女兵队。女兵们身穿灰色的学兵服,跟男兵一样训练,剪发、背枪、列队走在武汉三镇的大街上,唱革命歌曲,喊反帝、反封建、反蒋口号,刷标语,散传单,作演讲,演话剧,进工厂宣传,政治给凡庸的日常生活注入了一股歇斯底里的兴奋剂,多年之后,她们当中的成员仍然自豪地说:“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处在兴奋之中,根本不理睬社会上对我们的非议。” 这些女生还发动过一个“打倒封建墙”运动。因为武汉军校设在武昌两湖书院,女生队驻在原育杰中学旧址,中间隔着一道墙,女生们便说这是封建墙,要打倒,并开始动手拆除隔墙。校方只好解释说,隔墙只是隔队,男生队彼此间也有隔墙,不是封建,男女有别并非男女不平等,并答应在被推倒的墙缺处开一个小门,白天派一个卫兵,晚上再锁。但是过了些时候,卫兵也没有了,干脆是门虽设而常开。更奇特的是,这些女兵还曾经成立过一个“接吻队”,专门跟罢工工友接吻,而该队的队长,原本还是南洋一位富商的大小姐。在汉口,曾经有男工在总工会本部门前集体示威,高呼打倒妇女协会,宣称自从国民党到此地以来,宣传妇女解放,恋爱自由,以致他们的妻子都不再回家住宿,彻夜在外流连。武汉还发生过两次妇女裸体游行,第一次只有两个人,第二次就增加到八个人,一律裸体,唯肩头披一件薄纱笼罩全身,并且喊出了“打倒羞耻”的口号。这无疑是将政治革命与生活革命做了最夸张的结合,即此也可以管窥其后中国革命在私人生活领域翻天覆地之由来。 后来成为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牟宗三对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这种革命文化及其内蕴的革命精神的两歧性,有着深切的洞察: 那大浪漫时代的形态却不是如此,所以那内在的忘我的志气之锤炼根本就是非道德的。那是道德的影子,那忘我无私的貌似圣人而实非圣人,也只是圣人的影子。这就是神魔混杂的忘我。我因我当时的那开扩解放向上的感觉,我了解了这神魔混杂的貌似圣人的境界。《水浒传》里面那些好汉也是这种境界。这当然也是一种开扩解放向上,但却是向下堕的向上,封闭的开扩,窒闷的解放,最后是一个全体的物化,臭屎一堆,那也有一种风力与风姿,却是阳焰迷鹿趋向混沌的风力与风姿。 这话虽说有点刻薄,却也揭示了革命政治的某种实质,可惜更多的革命者没有这份旁观者的清醒,或者根本不愿意面对这份尖锐的真实,而让自我沉溺在个人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宏大叙事之中。 民国报人的风骨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中国,位于天津的《大公报》和立足上海的《申报》一南一北,环视全国,形成舆论呼应之势。两份报纸在内容与风格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前者稳重大方,言论相对理性温和,后者充满了摩登上海的商业气息,报纸上花哨的各类情色广告,很容易让初读者将之误作市井小报。前者的文艺副刊和言论的作者群体主要来自北平的知识界和文艺界,而后者大多来自上海滩亭子间的各类文人。撇开这些差异,两者却有着很多的相似性,比如都是创办人从他人手中购买,独立经营的,在办报宗旨上都坚持言论的独立性,都可以视为社会精英办大报的价值取向。史量才1912年从席子佩等人手中购得《申报》后,即明言其“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之定位,而1926年后的新记《大公报》更是以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位创办人所公共议定的“四不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而声名鹊起于报界。 如果说史量才是《申报》的大脑,指挥着这份发行量只有几千的小报迅速地攀升为具有广泛影响力(20世纪30年代发行量一度达到15万份)的全国大报,那么张季鸾就是《大公报》的灵魂,他在该报所发表的政论,犀利尖锐而不失洞见,总览全局而大气磅礴,《大公报》成为舆论重镇,张可谓建首功之人。从两人的生平与志趣来看,史脱胎于民国时期最富有现代气息的上海,出入于金融家、实业家等地方精英所构筑的社会网络之中,游刃有余地打造其报业帝国,并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等实体。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窥见独立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中间势力”的崛起,而其所夸耀于时人的是其处心积虑经营的《申报》。后者则具有传统士大夫的流风余韵,虽然早年亦曾留学日本,但其思想的根底在传统儒家以清议与谠论匡护公共价值与正义之准则。他先后参与过多家报纸的创办与经营,但其一生所着力的是文人论政,依靠《大公报》的公共平台,在全国造成理性而健全的舆论,进而影响最高当局的决策。张的一生以笔耕为主,甚少厕身于实业之经营。他的人生哲学就是报恩主义,报国家、人民与故土之恩,他人格伟岸,个性耿直而随和,在知识界与政府当局之间游走,扮演了民情上达的中介角色。曾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陶希圣在追忆张季鸾的文章中对此有评说:“北方的书生论政,政治当局重视北方的政论,互相呼应,很少隔膜,《大公报》尽了一番力。” 张可谓忧国忧民的传统士人,被蒋介石以“国士”视之,其一生与蒋结下不解之缘。据说蒋介石连其辖下的《中央日报》都不阅览,遑论《新华日报》等左翼报纸。他只读《大公报》,通过它了解时事与言论的动态。重要新闻政策往往通过《大公报》转达于全国报刊界。抗战后《大公报》内迁到陪都重庆,张身染沉疴,蒋介石亲往探视,并与重病中的张握手闲谈。张去世后,蒋在致《大公报》的唁电中发出“握手犹温”之感慨,公务繁忙的蒋介石多次主持或参与悼念张的公共活动。而张也是秉持“士为知己者死”之文化传统,其诸多言论往往发时人所未能发,而表蒋介石欲表达而未能明言之意,为蒋造成有利的舆论氛围。例如“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反复申述抗战之长期性与艰巨性,呼吁全国民众作持久抵抗,不以意气而草率交战致民族巨痛,而此时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北平政论刊物《独立评论》上,也发表诸多号召长期抵抗的政论,两者虽遭到激进民族主义者的怀疑与痛骂,却很长时间内不改论调,这与蒋介石的筹划不谋而合,自然是通过舆论为蒋“减压”。西安事变发生后,张痛感张学良、杨虎城之鲁莽与全国局势之危殆,高瞻远瞩,写出《西安事变之善后》,提出此事的善后措施。当时,《大公报》几乎每日都刊载张所撰写的时评,后来张所写的评论《给西安军界的一封公开信》,被宋美龄用飞机运载数万份运到西安上空广为传发,创造了“航空发行”的中国报史首例。 但张也并非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作为深受传统价值影响的报人,他深知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张力,“道尊于势”自然是其原则。当蒋介石的某些行为违背他所认为的民族大义时,张就毫不留情地批评。最为人所乐道的例子就是1927年12月2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的次日),张在《大公报》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斥责蒋“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的私人道德之糜烂,又慨叹“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点”,并痛斥蒋介石“不学无术,为人之祸”。可观其一生,虽与蒋介石时有芥蒂,却并未影响到其作为一个“报人”与蒋作为一个“政治家”之间的情谊。这份张与蒋之间“惺惺相惜”的“私谊”,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大公报》“公论”的独立与自主。尽管《大公报》时有犯禁之评论与新闻报道,却屡屡化险为夷,脱离严峻惩罚,不能不说与这份特殊关系有关。而当张去世后,《大公报》笔政由具有一定左翼倾向的王芸生主持,虽言论仍袭该报一贯的风格与尺度,却频频遭到蒋氏政权的打压。 反观史量才与蒋介石的关系,则从未有如此般其乐融融,史与蒋介石也很少私下密切接触。相对于张季鸾的文人论政,史量才更具有实业家的气象,他不仅仅是关注言论力量,更关切报业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实体力量的发展。正是依托于这样的思路,史并不满足于《申报》自身,他在上海积极地兼并和创办新报,并开设很多依附于《申报》的社会实体。或许缘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资本家的支持,以及独立于政治统治的“地方社会”的发达,雄才大略的史在上海纵横捭阖,先后出任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与上海临时参议会的主要负责人,甚至在南京开会面对政治势力以“百万雄师”相“武力威胁”时,兼具实业家、报人与社会活动家等多重身份的史量才毫无畏惧之态,反而扬言其手下有百万读者,足以纠集民意与舆论抗衡独裁之政府。当蒋介石20世纪30年代初内外交困而被迫宣布下野时,史量才居然胆敢在《申报》上刊发题名为《欢送》的时评,并呼唤一个政治革新的后蒋新时代的来临。而《申报》对于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挪用救灾款的辛辣批评,更是激起了朱的愤慨。1932年7月15日,朱在给正焦头烂额地忙于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去信:“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班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例如《申报》的《剿匪评论》,对于南京中央大学学潮的记载和评议,《申报?自由谈》和《申报月刊》登载陶行知等的文章,黄炎培做《申报》的设计部长,都是不利于党国的。”蒋阅后暴跳如雷,命令禁止邮递《申报》,于是从7月16日到8月21日长达三十五天的时间内,《申报》无从在蒋控制的区域内与读者见面。后经多方斡旋,才获恢复邮递。 《申报》批评蒋介石的围剿行动,实际上不是在消灭“共匪”,而是在制造更多的无家可归而只能被逼上梁山的“共匪”,直言这种现象产生的根由不在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而根植于持续的鸦片种植、不断攀升的苛捐杂税、地方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国民党军队对乡村的破坏,换言之,造成中国贫弱的根源在于专制横暴的国民党政权自身。针对民权保障同盟会总干事杨杏佛被蒋刺杀,以及更早的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的被刺等,史量才积极参与了由宋庆龄等发起的反蒋社会活动。 1931年12月20日,《申报》全文刊登了《宋庆龄之宣言》,宋在文中愤慨地指出:“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它早已丧失革命集团的地位,名誉扫地,遭到全国人民的厌弃和痛恨。”史量才无疑并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像张季鸾那样的谋士或国士,他是有政治抱负与政治行动力的。“九一八”后,国民党提出“ 攘外必先安内”的一味妥协政策而大失民心,以及蒋不断从江浙沪资本家那里榨取钱财与共产党打内战而导致与这个群体离心离德,都仿佛让史量才感觉到了上海民族资产阶级重建中国政治社会的可能。而他这种跑马圈地的大规模扩张行为,以及《申报》的巨大影响力,自然让依靠上海等地财阀支持发家的蒋介石视其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安。蒋对于史初出之以“胡萝卜加”的政策,威逼利诱兼而用之,一方面安排一些闲职予史量才以安抚,同时却逼着史量才辞退《申报?自由谈》的主编黎烈文,事实上是对于主张革新的黎大量刊发左翼作家鲁迅、茅盾、郁达夫、老舍等针砭时弊,尤其是痛斥国民党党治文化的杂文的不满。在这一切都未达到其预期目标时,蒋的本相毕露。于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无耻的一幕发生了,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与其夫人沈秋水及儿子等六人在由杭返沪的路上,被戴笠布置的六七个特务拦堵刺杀。史在杭州的手迹“山中岁月无古今,世外风烟空往来”成为绝笔。之后,《申报》的情势急转直下,被国民党委派的潘公展所控制,几乎再也无法发出不偏不倚的独立言论了。 张季鸾与史量才,同为民国报界奇才,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大相径庭,一得善终,死后哀荣备至;一竟被暗杀,虽然大张旗鼓查凶,最终不了了之,史只能含冤九泉。同为政客与报人的关系,对于张季鸾,蒋介石能够以犯颜直谏的“国士”待之,多有宽容和褒奖,自然与蒋自身也认同传统价值有关,并且与张始终坚守书生议政,而并无由议政而进一步干政之野心多有关联。而蒋对于史量才,则从未简单视之为手无寸铁之书生,对于其挟《申报》自重,领袖群伦于上海市主流社会,并与国民党左翼,甚至上海市黑社会或明修栈道或暗度陈仓,都多有忌惮与仇视。多次拉拢不成之后,便使出其惯有之消除政敌(史充其量只能算一个潜在政敌)的暗杀手段了。可叹张、史身后的《大公报》和《申报》竟然都未能庚续他们主政时之浩然气势,后者甚至沦为党报附庸。由此可见,中国舆论之发达与报业之壮大,与主持报纸者是否具备领袖风范与政治智慧关系甚大,政治生活中所谓人亡政息之规律也见诸报界。而舆论之独立也并非仅有诉诸西方社会所言第四权力之一途,张季鸾借助其与蒋介石的私谊,而让《大公报》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四不方针”的办报宗旨,也让今天的传媒人能够获得一些历史的启示。换言之,史量才式的立足于社会力量与政治权力的拓展舆论空间,与张季鸾式的从权力内部争取支持来获取言论的不受干涉,可以道并行而不相悖,共同合力打造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公共舆论空间。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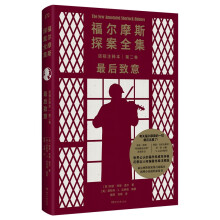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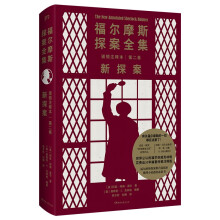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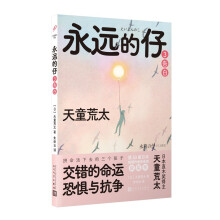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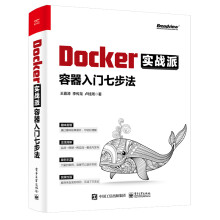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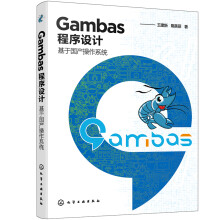
与民国相遇,遇见大变局中的碎屑和心情,遇见乱世中的悲歌与传奇。
我读了以后,既感到新奇,书中谈到的许多方面,都是我过去在研究中未曾注意的;又感到亲切,在学术追求上我们确实有许多相通之处。我自己的文学史研究、历史研究,关注、研究的中心,始终是人,人的心灵与精神,是大时代里的人的存在,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感性的存在;我要处理的,始终是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存在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追问背后的存在的意义与人性的困惑;而我的写作,也始终追求历史细节的感性呈现,具有生命体温的文字表达。现在我在小兵的新书里,也看到了类似的历史观念与写作,真有若获知音之感。
——钱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