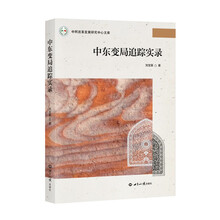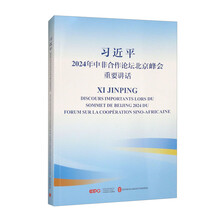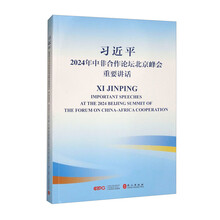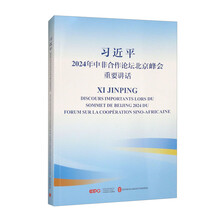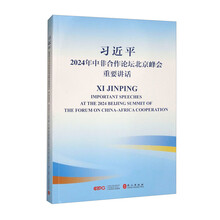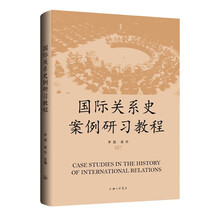20世纪50年代末,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说过,国务院有外交部,中共中央有联络部,中央办公厅有个小外事机构,这就是中办翻译组。最近,我们当年在中办翻译组工作过的几位同志,聚在一起,回忆了翻译组的成立经过、所做的工作,以及撤销的情况。尽管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谈起往事,不少细节又浮现在眼前。我们作为那个不寻常时期的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见证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由友好到破裂的全过程。
中办翻译组的成立
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成立于1957年1月,由阎明复、朱瑞真、赵仲元三人组成,阎明复任组长。翻译组的任务是接替师哲的工作,负责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
中办翻译组成立前,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主要由师哲担任。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苏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函,都是由任弼时亲自翻译的,用过的文稿也由他保管。从1943年起,开始让师哲参加翻译。莫斯科来的电函,由师哲翻译成初稿,经任弼时校对后,再呈送毛泽东。发往莫斯科的电函,由师哲翻译,经任弼时校对后再发出。1945年师哲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后,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才完全交给他一人承担,用过的文稿也由他保管,1949年1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西柏坡,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都由他担任翻译。新中国成立后,师哲的翻译任务更重了,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10月周恩来赴苏同斯大林商谈中国派志愿军赴朝鲜问题、1952年8月周恩来、陈云访苏商谈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10月刘少奇率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等,都是由师哲担任翻译。师哲最后一次为中央领导担任翻译是1956年10月随刘少奇、邓小平赴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讨论“波匈事件”问题。之后,他就到山东工作,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临行前,师哲向刘少奇请示工作。当刘少奇问谁可以接替他为中央领导担任俄文翻译时,师哲建议从各单位选调一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翻译,组成一个专门的翻译组,放在中央办公厅,这样中央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便于培养和教育他们,也便于保密。刘少奇采纳了师哲的建议,把建立翻译组的任务交给中办主任杨尚昆。
1957年1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刘少奇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因师哲已去山东,只好请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姜椿芳担任翻译。恰巧这天是星期六,司机早已下班回家,姜椿芳找不到司机,不得不坐三轮车到中南海西门,然后气喘吁吁地赶到刘少奇住地的会客室。完成翻译任务后,已是凌晨2点了。事后,刘少奇认为半夜三更把一个50多岁的老同志叫来当翻译实在不方便,便打电话给杨尚昆,催他尽快组建翻译组。
杨尚昆在同中办副主任李颉伯讨论组建翻译组时,李颉伯推荐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阎明复,说他正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率领的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国家,1月下旬回国后即可前来上班。杨尚昆推荐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朱瑞真,说不要办理调干手续,打个电话就可以过来。李颉伯又打电话给师哲,请他在中央编译局挑选一人,师哲推荐了赵仲元,说他将出差去山东,一个星期后回来即可上班。1957年1月中下旬,赵仲元、朱瑞真、阎明复先后到中央办公厅报到,中办领导宣布正式成立翻译组,由阎明复任组长。
中办翻译组成立后,其工作由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领导,在编制上隶属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研究室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居仁堂后楼。中办领导特别是直接领导我们工作的杨尚昆,对我们翻译组的几个年轻同志非常关心,为使我们能更好地完成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当翻译的任务,创造了一切必要条件。为了帮助我们熟悉中苏关系的现状和历史,凡是有关中国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和电报,杨尚昆阅后都让送给我们阅读。特别是毛泽东和其他领导接见外国使节、外宾、兄弟党代表的谈话记录,他都批给我们阅读、学习,便于我们及时了解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和精神,了解毛泽东对当前国内外重大问题的观点,熟悉毛泽东的习惯用语等等,以便在为毛泽东当翻译的时候能领会他的精神实质,能比较准确地翻译。他还亲自给我们讲述中共党史、中苏关系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如1928年在莫斯科举行中共六大的情况、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的情况、瞿秋白同米夫和王明进行斗争的情况、苏联情报组人员在延安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触的情况等等。同时,经杨尚昆批准,我们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一样,可以到后楼的文件陈列室阅读所有中央各部委的文件和各地方党委、政府呈报给中央的文件,包括绝密文件,以便我们能及时了解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动态。此外,杨尚昆还委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群众工作组组长章泽指导我们的政治理论学习。我们也订阅了不少苏联报刊,如《真理报》、《消息报》、《布尔什维克》、《新时代》、塔斯社的《每日电讯》和一些文艺刊物,以便及时了解苏联的信息和提高阅读俄文文献的能力。
中办翻译组做的主要工作
1957年中办翻译组成立的时候,中办副主任李颉伯在向我们交代任务时说,你们的任务就是为中央服务,具体地说,就是翻译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件,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出国访问或接见外宾时担任口头翻译。过去这部分工作由师哲担任,现在这副担子放在你们肩上了,担子不轻啊!你们必须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俄文水平,才能胜任这项工作。
1957年2月上旬,杨尚昆主任交给我们一项任务,说苏共中央已把共产国际时期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档案文献移交给我们,共30箱,现存放在中央档案局,你们先去看看,都是些什么文件,列出一个清单来。我们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粗略地看了一遍,搞出一个简要目录。这些文件包括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共中央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共各省市委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的复印件、各地准备武装起义的计划、共产国际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和对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六大的文件,等等。
完成这个任务后,我们接着翻译了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因为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重要的新理论观点,中央非常重视这篇讲话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宣传以及他们的反映,要求我们尽快把它译成俄文,以便公开发表。我们邀请了新华社的两位苏籍俄文专家审改译文,其中一位叫易哥尔尼可夫,精通中文。我们如期完成翻译任务,并根据中办的指示将译文交新华社发稿。
因为我们翻译组人手少、任务重,从1957年四五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开始,凡有重大外事活动,我们都请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李越然来参加我们的工作。李越然精通俄文,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给苏联派驻中国的经济总顾问当翻译,多次为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当翻译,陪同他们去苏联访问。长而久之,我们把他当做翻译组的成员了。后来,我曾提议把李越然调到中办翻译组,杨尚昆也表示同意,但由于李越然有一段“传奇式”的经历,保卫部门对调他来中办提出异议,此事也就作罢。李越然的父亲李芳中先生精通俄语,在齐齐哈尔中东铁路交涉局当通事(即翻译),同时又是苏联情报人员。李越然从4岁起就跟着父亲学俄语。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击溃了日本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不久,国民党接收大员也来到齐齐哈尔,并建立了临时地方政府。这时,苏联红军吸收年轻的李越然为他们做情报工作,并把他送到苏联赤塔一个专门学校培训半年。当他1946年4月回齐齐哈尔时,国民党接收大员及其地方政府被跑了,整个北满都成了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李越然找到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里宁,说现在已是共产党的天下,原来的情报工作已经失去意义。从此,他就中断了同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联系,并把红军交给他的电台上缴给东北公安局。这段经历,在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使他屡屡遭到不幸。
从1957年开始,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之间相互通报的事情、来往的信函逐渐增多,双方领导人的互访活动也增多了,我们翻译组的任务更繁重了。当时苏共中央有要事与中共中央通报或协商,一般先由苏联驻华使馆打电话给我们翻译组,提出受苏共中央委托有要事向中共中央转达,我们报告杨尚昆,然后杨尚昆向毛泽东报告,在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则向刘少奇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或由毛泽东或委托其他领导同志接见苏联大使。决定后杨尚昆办公室通知我们翻译组,由我们同苏联驻华使馆联络。一般说来,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驻华大使请求接见时,大都由毛泽东接见。1956年以后,毛泽东有时接见,有时委托刘少奇或周恩来接见。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后,接见苏联大使的规格逐步降低,刘少奇、周恩来也很少接见,一般由邓小平或彭真接见。1963年中苏公开论战后,接见苏联大使这件事便委托给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了。每次中央领导接见苏联使节都由我们翻译组的同志担任翻译和记录。我们把苏联使节转交的信件翻译成中文并把会见记录整理好后,送给杨尚昆审阅,并由他批示印发范围后交中办机要室处理。
翻译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函,是我们翻译组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中苏两党往来信函中,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每一份函件除了提供中文正式文本外,还都附了俄文译本。而苏共中央发来的函件只有俄文正本。那时,无论是把中文正本翻译成俄文,还是把苏共的俄文正本翻译成中文,都由我们翻译组承担。一般来说,每当苏联驻华使馆转来苏共中央的来信时,我们都连夜译成中文,送杨尚昆审批后,黎明前交到中办机要室,两三个打字员流水作业突击打印后,于上午9点前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的办公室。1957年2月至1966年10年间,中苏两党中央之间的信函往来,凡由我们翻译组经办的,都有详细记录和档案,“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翻译组解散时都奉命上交了。
关于苏共中央来函的翻译问题还有一段插曲。1957年7月至10月,中苏两党就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问题多次交换信件。10月26日,苏联大使尤金交来苏方准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草案。在接到苏共中央送来的宣言草案后,我们连夜译成中文,呈送杨尚昆,由他批送给有关的中央领导人。胡乔木看到这个宣言草案后,向毛泽东建议,这个草案需要认真修改。毛泽东以及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胡乔木的意见,并指定由胡乔木进行初步修改。毛泽东指出,在文字上要尽可能保留苏共中央的原稿,但是重要的问题还是要表明我们党的观点,并作出修改。胡乔木把译文一页一页地贴在大稿纸上,在稿纸的边上和空档上一段一段逐字逐句地反复修改。胡乔木对草案的修改约100多处,较大的补充有20余处,删节30余处。在修改过程中, 他感到我们的译文有的用词不够准确,很恼火,把阎明复叫去核对。他批评说,你们要一字一字忠实地翻译,如黑暗就是黑暗的,不要译成暗无天日的;残酷的就是残酷的,不要译成残酷无情的。总之,不要节外生枝。胡乔木的批评对我们触动很大,使我们更加理解所谓翻译要讲求“信、达、雅”,其中第一条是信,要忠实原文。这一要求后来成为我们翻译工作遵循的首要原则。
我们翻译组也参加了中共中央重要会议的文件翻译工作,印象最深的是翻译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文件的情景。因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中央很重视关于八大二次会议文件的对国外宣传工作,委托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过问这件事。王稼祥指定由中办翻译组和新华社的郑葵等一起把八大二次会议文件译成俄文,由姜椿芳和阎明复定稿。5月23日,王稼祥打电话要翻译组和郑葵到他办公室。他还把正在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师哲也请了来,共同研究八大二次会议文件俄文译文中的疑难问题。由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刚刚过去,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对文件中的某些提法有不同意见也不敢当面摆出来,如:“不断革命”一词本来是当年托洛茨基提出的一个极左的口号,苏联已经批判了好多年,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八大二次会议文件中的“不断革命”,应当如何解释?再如“一个跃进接着一个跃进”的翻译问题,有人说,译成俄文就是“一个跳跃接着一个跳跃”,这有点像兔子赛跑,跳跃式地向前发展,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关于“马鞍型”、“波浪式地前进”的提法,也有这个问题。争论最多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有人说,没有奋斗的目标,没有达到目标的期限,而且也没有主语,这不像一条总路线;也有人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是一般常识,谁都懂得鼓足干劲比松松垮垮好,力争上游比甘愿下游好,多快好省比少慢差费强,这样译成外文,人家会嘲笑我们。我们几个青年人就这样冒冒失失地提出了一大堆问题。王稼祥和师哲并没有责怪我们,一再说,原文如此,翻译无权改动,但你们可以在原文的框架内把译文表述得更圆满些,尽量少出漏洞,少授人以柄用以攻击我们。此外我们还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了关于“КУЛИТ ЛИЧНОСТИ”的翻译问题,向这两位老前辈请教。师哲说,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他请示过刘少奇,刘少奇说,“КУЛИТ ЛИЧНОСТИ”是贬义词,应该翻译成“个人迷信”;后来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只能译成“个人崇拜”,不能译成“个人迷信”,但也有一些翻译仍把这个词译成“个人迷信”。这样,就形成了“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两种说法并存的局面。师哲还提醒我们,两个月前,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个人崇拜有两种,其中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对斯大林正确的东西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因此,你们在翻译正式文件时,必须译成“个人崇拜”。从这里可看出,王稼祥并不完全赞成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总路线和“大跃进”的方针,师哲对毛主席把崇拜真理和崇拜个人混为一谈的说法也持有不同意见。
翻译组成立后,中央领导赴苏联或东欧国家访问,或苏共中央领导人来华访问,也都由我们翻译组担任翻译。1957年四五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中国共产党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我们翻译组承担了翻译工作。伏老在华的各项活动,由李越然担任翻译;阎明复分工照顾伏老的儿子及其夫人,并在外地参观中给伏老做些翻译工作;朱瑞真跟随罗瑞卿和苏方保卫人员,负责安排伏老的安全保卫工作;赵仲元则给其他苏方人员当翻译。1957年11月,以毛泽东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我们翻译组的几位同志随团担任俄文翻译。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三次即席讲话,阐述了“以苏联为首”、“东风压倒西风”、“团结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等观点,都是由李越然当场翻译的。1958年5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率代表团列席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阎明复等随团担任翻译。1958年七八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秘密访华,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进行了四次会谈。1959年九十月,赫鲁晓夫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会谈,双方发生了激烈争论。赫鲁晓夫这两次访华以及中苏间举行的会谈,都由李越然、阎明复担任主要翻译。1960年9月中苏两党会谈、9月底至10月中旬莫斯科会议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10月中旬至11月初莫斯科会议以及会后刘少奇以国家元首身份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由李越然、阎明复、侯志通、陈道生、朱瑞真、赵仲元等随行担任翻译。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解除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后,中央派周恩来率团访问莫斯科,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访问苏联。阎明复随团担任了翻译工作,中国驻苏使馆的王钢华 等人参加了翻译工作。
中办翻译组成立以来,见证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由友好到破裂的全过程,也参与了中苏论战的一些工作。1960年4月22日,经毛泽东审改,中国主要报刊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名义上是批判南斯拉夫的观点,实际上是批判苏共的一系列观点和对外政策。接着,苏联《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也发表了影射攻击中共的文章。双方文章的发表,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当时,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上述三篇文章的宣传工作,指定我们翻译组和新华社一起把三篇文章译成俄文,经姜椿芳、阎明复定稿后对外发表,然后由外文出版社印成专门的小册子,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新华社等驻外机构在苏联东欧国家散发。从此以后,中苏两党利用参加国际会议、举行会谈或交换信函等形式,你来我往,互相攻击,我们翻译组的同志大都参与了这些会议、会谈或信函的翻译工作。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捷克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先后召开代表大会。在这些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人苏斯洛夫、库西宁、科兹洛夫、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分别带头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并暗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攻击苏共是受中共唆使的。我们翻译组的阎明复随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保、匈、捷、德党的代表大会。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为回答苏共在这些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等七篇文章。这七篇文章被翻译成俄、英、法、日、西班牙、阿拉伯等文字对外发表,我们翻译组的同志参加了这些文章的俄文文本的翻译和定稿工作。1963年3月2日,为起草论战文章和信件,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康生任组长,吴冷西为副组长,乔冠华、王力、姚臻、熊复为主要成员。为把论战文章和信件译成俄文,在成立文件起草小组的同时,也相应组成了一个翻译班子。这个翻译班子就是以我们翻译组为基础,先后借调何长谦、欧阳菲、李越然、张报、刘莫阳、林莉、杨蕴华、罗正法、任田生、张达楠参加翻译工作。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除详细地阐述他们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观点外,还提出一个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7月14日又发表《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就苏中两党分歧的由来、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问题、民族解放运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国际共运的团结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和建设共产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精神,先后写了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每篇文章都是由“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把稿子写好后,送中共中央审改。审改的程序,一般是先由邓小平主持,把起草小组成员召集起来讨论,根据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经邓小平认可后再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再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然后送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定稿。每篇文章都经过七八稿才能完成,起草小组在前面修改稿子,我们翻译班子在后面跟着修改译文,也是经过七八稿才能最后定稿。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一共发表了九篇文章,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原先还准备写“十评”,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十评”没有发表。
随着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也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理论不断升温,我们翻译组的成员也开始发生变化。1964年的一天,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突然找阎明复谈话,说“李越然有些历史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他不适合为中央领导同志担任翻译,以后中央再有什么外事活动时,不要再请他来参加工作了”。接着,1965年5月在“清理中南海干部队伍”的理由下,李越然被调到第二外国语学院。李越然在离开中南海之前到中办翻译组办公室同我们告别时,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明明知道他调出中南海的原因,又说不出口,大家只好相互勉励:不管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将一如既往地努力为党工作;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之间的兄弟情谊不会消失。
中办翻译组的解散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论战的加剧,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形势的估量,使党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上的错误也一再发展起来。1963年,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四清”运动在全国广大农村开展起来。1964年7月14日第九篇评论苏共公开信的文章发表后,我们翻译组的任务越来越少。1964年9月,赵仲元跟随杨尚昆去了陕西省长安县搞“四清”。长安县有个传说,说历史上凡是从长安(今西安)、洛阳、开封出巡的大官,谁到过牛角村,他就像钻进牛角一样,很快就要倒霉了。我们听后哈哈大笑,认为这是谎言,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不幸,这种历史的巧合很快应验在杨尚昆身上。1965年9月,阎明复和朱瑞真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考虑到临时有任务回来方便,便被派到彭真抓的一个“四清”工作点,即北京市顺义县李遂公社。
1965年2月初,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越南访问途中在北京作短暂停留。在京期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接见了他。由阎明复担任翻译。这是阎明复最后一次给毛泽东担任翻译。
1965年3月,苏共纠集1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并发表会议公报,宣称,“主张停止对兄弟党具有不友好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反对一些党干涉另一些党的内部事务”,鼓吹“团结反帝”,“一致行动”。公报发表前,苏联驻华使馆代表将会议秘书处的一封信和公报交给中共中央。之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这篇文章揭露了苏共新领导“三真三假”的面貌: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文章指出,三月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翻译组参加了这篇文章的翻译工作。
1966年2月24日,苏共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根据彭真指示,中办领导打电话把阎明复和朱瑞真从“四清”工作点叫回,阅看文件,为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做些准备工作。阎、朱在北京等了几天,随后听说,毛泽东不同意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说,阎、朱党去不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于3月22日复信苏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我们参与了3月22日复信的翻译工作,这是我们翻译组解散前执行的最后一项任务。阎、朱翻译完中共中央3月22日复信后,重新回到“四清”工作岗位。苏共二十三大以后,中苏两党中断了一切往来。
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职务,调到广东省委担任副书记。12月5日,他在离开中办前同我们翻译组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说:“由于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你们的翻译任务不多了,你们要及时转向研究工作,研究苏联、研究苏共,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有很多经验和教训有待你们去研究、去探讨、去总结,研究要从做好大事记、积累材料做起。此外,你们已经参加过一届农村‘四清>,今后要争取再参加一届城市‘四清>,这样,你们对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对中国的国情就会有个初步的了解,将来无论到什么工作岗位上都会终生受益的。”我们当时还天真地认为越南战争正逐步升级,杨尚昆与胡志明非常熟悉,很可能是名义上调杨尚昆去广东工作,实际上委托他担负抗美援越的任务。
杨尚昆调走后,彭真曾取代杨尚昆直接过问我们翻译组的工作。他曾考虑随着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中办翻译组的工作逐步转移到中联部,需要把翻译组一分为二,把阎明复和赵仲元调到中联部工作,把朱瑞真留在中央办公厅值班,一旦中央有翻译任务,打个电话,阎、赵再回来,仍然是三个人一起工作,但这个想法未能实现。不久,“文化大革命”批判的矛头直指彭真。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5月22日,中办举行所谓的“揭盖子会议”,传达“五一六通知”,号召揭发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
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宣布成立秘书局,下设文电处、信访处、调研处,撤销原来的机要室、秘书室、研究室(即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这样,中办翻译组也就不存在了。原来在中南海居仁堂后楼办公(包括我们翻译组)的大部分同志奉命搬出了中南海。7月15日,我们这些离开中南海的同志被送进中办学习班,我们翻译组的同志从此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审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朱瑞真问师哲,为什么当年离开中央到地方工作?师哲透露了缘由: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在同米高扬的谈话中严厉批评了苏共领导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说:“对当年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做法我们是有一些意见的,过去我们不便讲,现在要开始讲了,甚至还要骂人了。” 师哲预感到中苏反目在所难免,而他本人在苏联克格勃工作过,回国后又介入中苏高层特别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联络工作,一旦两党关系恶化,他肯定首当其冲成为第一个“牺牲品”。的确,在他离开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苏两党分歧日益加重,直至彻底决裂。“文化大革命”中,不仅早已远离中央领导的师哲,而且所有曾为中央领导服务过的俄文翻译,都在“里通苏修”的罪名下受到了审查。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