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以“新迷影”为题,缘于“电影之爱”,迎向“电影之死”。
“迷影”(Cinephilie)即“电影之爱”。从电影诞生时起,就有人对电影产生了超乎寻常的狂热,他们迷影成痴,从观众变成影评人、电影保护者、电影策展人、理论家,甚至成为导演。他们积极的实践构成了西方电影文化史的主要内容:电影批评的诞生、电影杂志的出现、电影术语的厘清、电影资料馆的创立、电影节的兴起与电影学科的确立,都与“电影之爱”密切相关。从某种角度看,电影的历史就是迷影的历史。“迷影”建立了一系列发现、评价、言说、保护和修复电影的机制,推动电影从市集杂耍变成具影响力的大众艺术。
电影史也是一部电影的死亡史。从电影诞生起,就有人不断诅咒电影“败德”、“渎神”,预言电影会夭折、衰落,甚至死亡。安德烈·戈德罗曾说电影经历过八次“死亡”,而事实上要远超过这个数字。1917年,法国社会评论家爱德华‘布兰出版了图书《反对电影》,公开诅咒电影沦为“教唆犯罪的学校”。1927年有声电影出现后,卓别林在《反对白片宣言》(1931)中,宣称声音技术会埋葬电影艺术。1933年,先锋戏剧理论家安托南’阿尔托在《电影83》杂志发表文章,题目就叫“电影未老先衰”,认为电影让“千万双眼睛陷入影像的白痴世界”。而德国包豪斯艺术家拉斯洛‘莫霍利一纳吉在1934年的《视与听》杂志上也发表文章,宣布电影工业因为把艺术隔绝在外而必定走向“崩溃”。到了1959年,居伊·德波在《情境主义国际》的创刊号上公开发表了《在电影中反对电影》,认为电影沦为“反动景观力量所使用的原始材料”和艺术的消极替代品……到了21世纪,“电影终结论”更是在技术革新浪潮中不绝于耳,英国导演彼得-格林纳威和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分别在2007年和2014年先后宣布“电影已死”。数字电影的诞生杀死了胶片,而胶片一“迷影人”虔诚膜拜的电影物质载体,则正在消亡。
电影史上,两个相隔一百年的事件在描绘“电影之爱”与“电影之死”的关系上有代表性。1895年12月28日,魔术师乔治·梅里爱看完了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放映,决心买下这个专利,但卢米埃尔兄弟的父亲安托万·卢米埃尔却对梅里爱说,电影的成本太高、风险很大,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技术”。这可看作“电影终结论”在历史中的首次出场,而这一天却是电影的生日,预言电影会消亡的人恰恰是“电影之父”的父亲。这个悖论在一百年后重演,1995年,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应《法兰克福评论报》邀请撰写一篇庆祝电影诞生百年的文章,但在这篇庆祝文章中,桑塔格却认为电影正“不可救药地衰退”,因为“迷影精神”已经衰退,能让电影起死回生的就是“新迷影”,“一种新型的对电影的爱”。所以,电影的历史不仅是民族国家电影工业的竞争与兴衰史,也不仅是导演、类型与风格的兴替史,更是“迷影文化”与“电影终结”互相映照的历史。“电影之爱”与“电影之死”构成了电影史的两面,它们看上去彼此分离、相互矛盾,实则相反相成,相互纠缠。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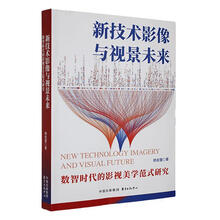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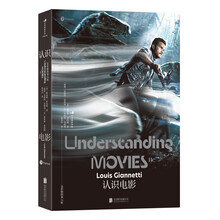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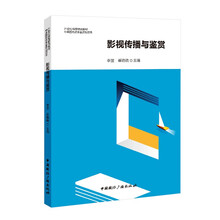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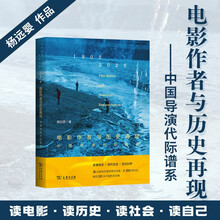

眼泪是什么?眼泪就是你的成功的泉源。你相信吗?
——S.M.Eisenstein(谢尔盖·爱森斯坦)著白力译述
★摘自《联华画报》,1934年第4卷第9期
先行澈底的地组织的地推翻“摄影和电影跟艺术并没有关系,因为它们只是自然底机械式的复写而已”这个意见,是很有价值的事,因为这样做,是较接近于理解电影艺术底特质的一个好的方法。
——安海姆(鲁道夫·爱因汉姆)著,刘鸥译,摘自《晨报·每日电影》,1935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