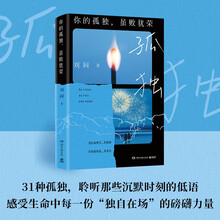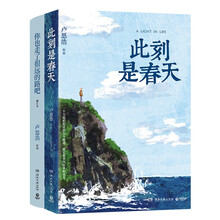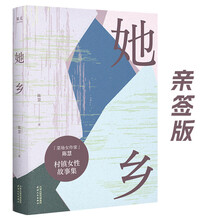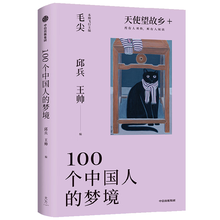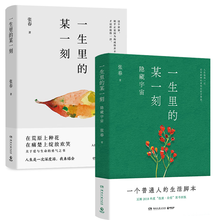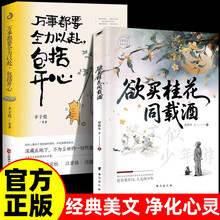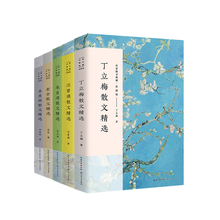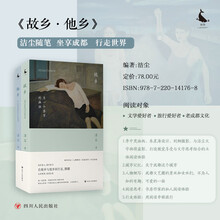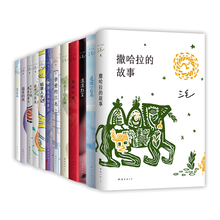《鲜花上跳动着音符的地方》:
我上过三所小学。一所是汉语小学,两所是蒙语小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就读于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奈林稿小学,读蒙语。我是从二年级开始读的。我六岁时,九岁的姐姐上学了,母亲让她边上学边看护我。每天我都跟着姐姐准时到校,我就坐在教室门槛上看他们上课,也跟着念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冬天室外太冷,老师允许我进到屋里靠着墙蹲在后面,只要不影响上课就行。一年下来,姐姐会的语文、算术,我都会了。等到我该上学了,我就跟父亲说让我和姐姐一个班上课吧,一年级的课我都会了!父亲向校方征求意见,学校说那就考考吧!老师写了一黑板的语文和算术题考我。我念对了语文,算对了算术,顺利通过了考试。就这样,我直接从二年级上了小学。我一路很顺地读到三年级,再开学就要读四年级了。这时,父亲的工作调动了,因此我家要从学校附近的毛敦艾里(木头营子)搬到呼和格勒(瓦房)牧场。
到了牧场才发现这里的小学没有蒙语班。于是父亲联系了离家十五里的古尔奔格勒(蒙语:三家子)小学让我和姐姐读书。不巧的是该小学只有五、六年级有蒙语班。这使得我只好跳了一级,跟着五年级读书。大概这未读的四年级太重要了,直接上五年级很吃力。我稀里糊涂就小学毕业了,中学也没考上。回到家,放了近一年牛犊。后来又跟着牧场小学汉语班继续读四年级,竟然顺利毕业,还考上了旗(内蒙古地区行政单位,相当于县)重点中学。
我的汉语稍好过一般蒙古族孩子,可能与父亲有关。他的同事中汉族人居多,来家里玩的汉族小孩也多,时间久了,算是对汉语耳濡目染了吧!还有另一个因素是:内蒙古地区有条件的蒙语小学里蒙语班会开设一门汉语课,这是我比较喜欢的课。
我上的第一所小学叫作奈林稿小学。奈林稿即奈林郭勒,是“细细的河流”的意思。学校因坐落在该河边的奈林稿乡而得名。学校离我家一千米远。因依水而建,校园内外绿树葱茏,有槐树、柳树、杨树、榆树。学校旁边有一条大路,经常可以见到从辽宁方向过河而来的骆驼队在学校附近休息一夜后向北开拔。据大人说,他们是向草原深处的城乡送货的(早期的物流吧)。我现在看书才知道,这是从沈阳(旧称奉天)到蒙古地区运物资的驼队的必经之路,其实是一条商贸之路中间的一站。
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是个英俊的蒙古族小伙,名叫白乙拉(意为欢喜)。他的头发和眼睛是淡黄色的,脸白里透红。他的未婚妻名斯日古郎(意为聪慧秀丽),是漂亮的蒙古族姑娘。她经常到我们班来,帮助白乙拉老师给我们上课。我对他们的印象非常好,至今没有忘记他们当年的模样。
我对第二所小学的印象一般,因为老师有点冷漠,可能是个有苦难的人。十岁那年,我的小弟病重,我向老师请假回家看望,他嘲讽我“又不是大夫,回去能干啥”,气得我头也不回地奔家去了。
我念的第三所小学是瓦房牧场小学。因我是从四年级开始读汉语班的,一开始也不是太顺利。因是国营牧场的小学,师资力量在当时算是很强了。我们的崔权老师是北京地质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啊!这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算是草原上的高级知识分子了。我的汉语水平的提高,乒乓球爱好的培养和短跑成绩的提高等,都与他的影响分不开。崔老师后来还当上了牧场小学的校长,再后来据说当了牧场的场长。
读个小学换了三个地方,中间还跳了一级,仍费时七年,再加上第一年随姐姐读书,共计八年,我的小学读得够费劲了。但蒙汉文化熏陶和阅历的增加,使我有了一般小学生没有的经历,对人、对事的看法,对生命的体验有了独特的感受,我觉得很值。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