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过去的事
听妈妈讲过去的事
那一年,我最想要的就是有一个男朋友。当时的我十七岁,而且从来都没有约会过,但该有的我全都有:胸部、长及肩膀的头发、月经周期、欲望。我当然有欲望。
有一次,在我还小而且对技术层面还不精通时,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假装在做爱,我们的腿张开成剪刀状,张开到我们的胯部对着胯部,身体紧紧相贴。这件事被我奶奶当场逮到,她要塞西莉回家,然后用一根木头搅拌匙打我的屁股,还要我坐在餐厅里念《圣母经》。她说,她很确定我之所以有那种兴趣是遗传自我的母亲。或许我是吧,然而,即使年纪还那么小,我就已经认为对性感到好奇并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在我十七岁前,除了收到一张情人卡片,还有在爱达荷州(Idaho)沙尖镇(Sandpoint)游乐场的露天看台下被一位丹麦鹰级童军偷走了三个吻之外,我什么经验都没有。
这让我感到十分沮丧,而我那个当年九岁的妹妹梅根可是一点都帮不上忙,她总是很乐意帮忙确认我一定如自己所想的那么丑,甚至
还暗示着可能有男孩子觉得我很丑。
爸爸告诉我,我需要的是耐心。“时候到了自然就会发生,随缘吧,你一定会交到男朋友的。”他说。我回答他,如果我们没有经常搬家,或许缘分早就已经来到我面前了。
所以到最后,我去找妈妈寻求安慰。我问她,她第一次谈恋爱是在什么时候。
“汉斯·克劳斯·费雪。”她跟我说。
我找到她时,她正在厨房里擦地板。她的双手和双膝都压在亚麻地毯上,头发用一条红色的印花手帕绑起来。她停了一会儿,思考问题,接着她露出牙齿微笑。她伸手到厨房料理台上拿香烟,然后再次坐在地板上,背靠着水槽旁的料理台。她双脚交叉,让膝上的烟灰缸
保持平衡。
“那是我和艾儿菲姨妈住在德累斯顿(Dresden)的时候。其实我是不能和男生约会的,我才刚满十五岁,阿姨说我还不能外出。他们那个年代是很严格的,你知道的。”她点燃香烟,烟雾后的双眼在微笑。我们都知道,艾儿菲姨妈说的话对妈妈的行为,并没有什么约束的效果。
“他是面包师傅的儿子。我认识他是因为艾儿菲姨妈要我每天去拿面包。如果她让布莉姬塔去,谁知道还会不会发生这件事呢?或许我永远也不会认识他。但是,感谢布莉姬塔很懒。总之,他每天都在店后面,不断把面包拿下来。”她停了一会儿,目光仍然停留在我身上,“你猜他帅吗?”
“他帅吗,妈妈?”我问。你一定要怂恿妈妈继续讲她的故事。那是乐趣的一部分。
“他帅吗?这个嘛,我会告诉你的。他的头发和你的发色一样,
不,或许稍微深一点,而且是像这样往下梳(她用手比画了一下),那个时候的男生都是梳那样的头。他的眼睛是蓝色的,嗯,或许更像蓝绿色,而且是浅色的,一种浅浅的蓝绿色,就像旧玻璃会有的那种颜色。他的嘴唇相当薄,很薄,通常我并不喜欢男人嘴唇薄薄的,但配上汉斯,它们让他变得相当……我该怎么说呢?
“傲慢,就是这两个字。他会站在后面的房间,把面包拿下来,而我心里则想着‘玛拉,你一定要让那个男孩成为你的男朋友’。你可以想象,我只要看着他,就知道他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她露出牙齿微笑着看我:“我那时非常爱他。我每天去拿面包,在等待的时候,我脑子里都在幻想自己亲吻着那纤细的唇。”
“你吻了吗?”
“这个嘛,一开始要让他注意到我是很困难的。我只是一个女孩,
而爱上汉斯的女孩很多。”
“不过你确实让他爱上你了,不是吗?”我问。
她还是那副露出牙齿微笑的表情。她用一只手把几股长发固定在印花大手帕下,还是没说话。妈妈不需要说话,她只是露出牙齿微笑。
“你做了什么?有那么多别的女孩子,你是怎么让他注意到你的?”
“我开始穿着我的德国女青年联盟制服去拿面包。每一天都穿,即使没有开会也一样。他是青年运动团体的领导人。”她停了一会儿,思考并研究香烟的尾端,然后再次露出微笑,“有时我会在店的后面看见他,他会穿上他的制服。他穿那件制服时看起来很帅,而且走路时有点神气,所以我看得出来制服让他感觉到自己很重要。因此,我心想:‘玛拉,如果他知道你是女青年联盟的优良成员,他一定会喜欢你的。’”
“他有喜欢你吗?”
她对我眨眨眼。
“那么艾儿菲姨妈怎么说呢?她不反对你在不该和男生约会的时候去约会吗?”
“这个嘛,她是有点反对。其实一开始她很反对,但我告诉她汉斯的家世很好,还说他是个好男孩,功课很好,而且有一次我在面包店里听他父亲告诉舒华兹太太,汉斯可能会被选进阿道夫·希特勒学校。他说那件事快拍板定案了。”她说。
“所以,当阿姨听见这件事之后,她就说周五晚上我可以和他一起去跳舞,不过布莉姬塔要跟着一起去,”她大笑,“以防我发生有关亲吻那双薄唇的事。那个时候他们相当严格,不像现在。”
“但是你是怎么让他爱上你的,那才是我想知道的部分嘛。你是怎么让他开口邀你出去的啊?”
妈妈拿着香烟,先是盯着香烟看,最后将香烟在烟灰缸里弄灭。周遭的地板仍是湿的,我们坐在刷子、桶和地板破布后面,背靠着厨
房的橱柜。
“我做了一件相当下流的事。”妈妈说。她的声音很低,而且带有阴谋的意味。
“什么事?”
“嗯,有一次他走到店前面和我讲话时,我说自己实际上是大公的孙女。”
我大笑:“真的吗?”
“我告诉他,我祖父是大公,因为安全的关系,我被送到德累斯顿和艾儿菲姨妈一起生活,但事实上她并不是我的亲阿姨,只是我家人付钱请来照顾我的一位奶妈。”
我可以想象到妈妈以如此戏剧性的方法做出这种事,而且觉得很有趣。可怜的汉斯,他一定不知道自己跳入了什么样的陷阱。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她耸耸肩,咯咯地笑:“我不知道。这只是我做过的某件事,我想确定他喜欢我。”
“可是那是谎言呀,妈妈。”我说,心里仍然觉得想发笑。
她又耸耸肩,噘着嘴,摆出沉思的表情:“不,也不尽然啦,反正只是个故事嘛,我又不是故意讲来害人的,只是没有足够有趣的真实事情可以告诉他。”
“所以,你告诉他,你的祖父是大公?”
“这个嘛,你一定要了解,我当时非常想跟他交往,我只是希望事情能顺利进行。我想,如果他相信,那么他就一定会想和我一起跳舞,而且一旦他认识了我,那么我和什么人有没有关系就不重要了。”她转头过来看我,以眼神表示不需要认真以对,“我当时只有十五岁每个人十五岁时都会有一点疯狂,相信我。”
“他发现真相了吗?”
她耸耸肩,跪下来继续擦地板:“我不知道,到耶拿(Jena)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我正在做梦。那个梦和史都华大道上的那间房子有关,在梅根出生前,我们住在那里。我住在楼上的小阁楼房间里,爸爸帮我把这间小阁楼房间改装成卧房。我站在小窗子前,看着下面的街道,但原本种在史都华大道两旁的榆树变成了向日葵。街道上没有人,但阳光让一切闪闪发亮,非常漂亮。
然而,即使它看来似乎像是史都华大道上的那栋房子,但我知道事实上它并不是。它是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在底特律(Detroit)曾经住过一阵子的公寓。虽然楼上的卧房属于史都华大道,可是我知道那楼梯向下通往底特律的公寓。
在梦里,我可以听见妈妈在哭泣。她当时坐在楼梯下面阴暗小储
藏室里的一个硬纸板盒子上,但我仍然在楼上史都华大道的房子里。
“莱丝莉,你起床了吗?”
我猛然醒来。
梅根正站在我的卧室门口。她只穿了内裤和一件前面写着“NASAJohnsonSpaceCenterHouston”(休斯敦美国航空航天局约翰逊太空中心)的超大T恤。她靠在门框上,双脚交叉:“爸爸说你必须立刻起床,他今天早上得去上班,所以他不在时,你一定要下楼来陪妈妈。”
“几点了?”
“差不多九点了。爸爸说他午餐后会回来。”
她转身,没关门就走了。
我闭上眼睛。我依然记得那个梦,而且因为突然被叫醒,以至于它还紧抓着我,而且梦境相当真实,甚至当它逐渐消失时也是如此。
等我穿好衣服来到厨房时,爸爸已经去上班了。梅根还在吃早餐,她把椅子往后推,两只脚藏在宽大的T恤下面。妈妈正在收拾盘子,把它们放进水槽里。收音机的声音开得好大,现在正播着《周六晨间以物易物商店》。妈妈很迷这个节目,她会慢慢欣赏所有她梦想得到的交易。
我伸手拿了一片吐司放进烤面包机里。吐司是全麦的,上面全是嘎吱嘎吱作响的小麦种子,虽然把它做成烤吐司很棒,但吃的时候会一团乱,因为上面的小麦种子会掉得到处都是。
梅根正在挑小麦种子,藏在T恤下的双脚把衣服撑出一个球形,她小心翼翼地把种子放在T恤上,再用舌尖一一舔掉。
“老实说,梅根,你吃东西时真像只猪。”我说。
梅根拿起另一颗小麦种子,转头看我,确定我在看之后,就用舌
尖舔掉它。
“妈妈,你看她,梅根把她的吐司搞得非常恶心。”
妈妈从水槽那里转过身来。她看了梅根一会儿,摇摇头。“你把面包屑搞得到处都是。”她说,“坐好,把你的脚放在该放的地方。”
我走到橱柜拿棉花糖米香棒:“梅根,妈妈说把你的脚放下来。”
“所以呢?你又不是我妈。”
“可是她是,所以,快照着做。”
“哼,看你有没有办法让我放下来啊?”
我生气地坐了下来。
梅根继续挑吐司上的小麦种子时,我伸出手抓住她其中一只脚,
然后猛然地把它拉到地板上。
妈妈没理我们。她背对着我们,继续洗碗。她一手拿着钢丝球,一手拿着旧的铸铁长柄平底锅,拼命地刷。她偶尔会暂停,把窗台上烟灰缸里燃烧的香烟放在嘴唇上,还一度把收音机的音量调高。不过她始终没有转过身来。
梅根伸手要拿另一片吐司时,我的手紧抓着她的手腕。
“放开!”梅根说,声音相当大,“别一天到晚对我发号施令,莱
丝莉!”
“你吃吐司的方式很恶心,而且你是故意的。好了,你不可以再吃了。你这个故意搞得乱七八糟的捣蛋鬼。”
“不用你管我!”
“妈妈,你叫梅根不要再弄了啦!”
“莱丝莉,放开我的手!”她站起来想挣脱,结果椅子往后倒,弄出很大的声响。
妈妈转过身来。
没有人作声。
我们两个人都看着她。她拿起香烟,很小心地把它放进烟灰缸里弄灭。厨房里尽管还有“周六晨间以物易物商店”的喧闹声,但我仍可以听见香烟碰到烟灰缸玻璃时发出的声音。
妈妈很不耐烦地举起一只手拂开脸上的头发:“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是姐妹,怎么可以老是吵架?”
我们没有回答,回答也是于事无补。
“我真不懂你们,”妈妈说,“你们为什么不快乐?你们拥有那么好的人生,有欧麦利和我,我们爱你们。我们给你们一切,可是你们好像还是不快乐?”
“我们快乐啊。”梅根说。
“我们只是闹着玩的啦,妈妈。”我赶紧说,“我们不是故意要听起来像在吵架,我们只是在玩,对不对?”
“我真不懂你们。”妈妈摇头。
“我们很快乐,妈妈。”梅根又说了一遍,她的声音里带着轻微的绝望,“看到了吗?我在微笑,我和莱丝莉真的很快乐。别哭了,
好吗?”
但是已经太迟了。妈妈把脸埋在双手里,接下来,她从厨房跑出去。我们留在那里没动,听着她凌乱的脚步声踏在楼梯上,直到收音机的声音盖住脚步声为止。
梅根也开始哭了。被翻倒的椅子还在她身后的地板上。她看着我,让眼泪流下脸颊。
“好了,梅根,你想再吃一点早餐吗?来点烤松饼好不好?我知道你喜欢烤松饼。别哭了,好吗?我帮你弄一点松饼好不好?”
她擦擦眼睛,摇摇头,接着她把椅子扶正,也离开了厨房。
我爸称这种事为“发作”,妈妈的发作。妈妈发作时,爸爸会半耸着肩,然后面带微笑,仿佛那只是她一个反复无常的小怪癖,就像别人在泄露秘密之后,会朝自己身后撒盐一样。
然而我讨厌这种情节。小时候,我以为那样是正常的,我以为每
个孩子的母亲都这样;直到十岁或十一岁时,我才发现别人的母亲不会这样。
我一个人在厨房里,把水槽里几个剩下来的盘子洗好,清理桌子,
将梅根的面包屑擦掉,最后把已经泡得软软的麦片倒掉。
不久之后,梅根回到厨房,她想用一把宽齿梳整理发尾。“帮我好不好?”她拿出梳子说,“我没办法把所有的结梳开。”
我妹妹有一头漂亮的头发。她的头发就像爸爸的头发,颜色深得几近黑色,但也像妈妈的头发,非常直。你可以用你的手指头梳它,它会轻柔地、波浪般溜过指尖,像水一样;然而,梅根的头发最棒的部分是它的长度,它几乎长到可以让她坐在上面。
她的头发太多,经常会散掉,因为它全部的重量让她无法使用小女孩用的发夹或头饰带。梅根总是带有一副未被驯服的表情,尽管如此,人们有时候还是会停下脚步,转身再看她一眼,因为她十分醒目。我在梅根这个年纪时,始终不被允许留那么长的头发,不过我也不曾拥有像梅根那样又黑又直的头发。
“莱丝莉,爸一定会杀了你,因为你让妈妈发作。”我在梳梅根的头发时,她说。
“我?是你的错!你这只小猪。爸爸会杀了我们两个。”
她没搭腔。她离开我身边,拿走我手中的梳子,走到桌子那里。她坐上桌子,然后把长发拉到身前,梳发尾打结的部分。
“梅根,不要在桌子上梳头发。”
她没答话。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那样很不卫生,换别的地方!”
她还是没反应。不过她放下梳子,改用手指头去梳,并看着头发。
“莱丝莉?”她问话时没有抬头,“妈妈为什么会那么做?”
“做什么?”
“就是那样。我的意思是,我们只是在开开玩笑,仅此而已。为什么她总是无法了解呢?”
我耸耸肩。
“她为什么一直认为我们不快乐?为什么对她来说,我们每一分钟都百分之百地快乐是那么的重要?”
“这只是其中一件事而已,梅根。”
“什么其中一件事?”
我耸耸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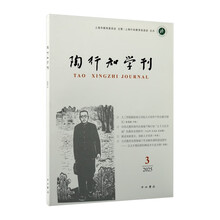


★桃莉·海顿是个罕见的天才,她笔下的爱与恨有一股穿透人心的力量,感动了无数读者。《玛拉的向日葵森林》使我的身心灵,深深为之悸动不已。
——《当好人遭难时》作者哈罗德·库什纳诚挚推荐
★桃莉·海顿赢得我们最高的尊敬。她可贵,不可思议。这个世界需要更多像桃莉·海顿这样的人。
——《波士顿地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