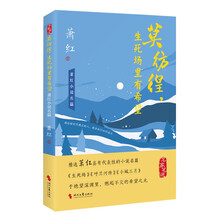荷花
夏天拍到单枝的荷花,已属不易。总是开成一片花海,我们俩一人手拿一部相机,边走边拍。他总希望我把图片拍得正,是那种端端正正的构图,我却喜欢倾斜的,爱玩点小花样。是性格使然。我在他眼中总是有点顽皮,说话又有跳跃感,有时说完话,就痴痴地望着他笑,很好玩。
摄影是近来才有的爱好。小时候学过一点画,说“一点”,也有六年之久,画素描,画静物,也跟着老师出去画风景写生。那时北京冬天天冷,老师、学生全都穿着一种叫“棉猴”的蓝外套,现在这种衣服基本上都已绝迹了。
学画和摄影还是许多相通之处。这一点我还得感谢我的母亲。她是一位过于严厉的母亲。每次想到“严厉”二字都会想到母亲。今年小说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央台播放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刚睡醒觉,坐在餐桌旁一边喝咖啡,一边吃午餐。我听到新闻主播用过于职业化的清冷声音在说:“莫言有一位过于严厉的父亲……”“严厉”二字一下子把我击中了,我想到了自己,我也有一位“过于严厉”的母亲。
我的学画之旅是从童年开始的。稚童学画,没有老师。我母亲是一位雷厉风行的眼科医生,具有科学精神,又懂得节俭,她不买单本的儿童画册给我模仿,而是每星期去百货公司买一款新出的手绢。她这种教育方法是独树一帜的,完全属于自创。
母亲买手绢给我,是为了让我临摹上面的画。画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天女散花的女子,有清绿妩媚的植物,有五彩斑斓的海底生物,也有想象的童话女孩。那些画多属于线描,轮廓线是用一条细细的黑线勾勒出来的,简单干净,孩子用来临摹它,倒是一种不错的方法。
但六岁女童对于画画还茫然无知,懵懂得很。
她不知道应该画什么,怎么模仿。第一次很新鲜地画了一幅,再下去就不怎么愿意了,只想逃避。妈妈又买来新手绢,上面的画风很强劲,是一位少数民族妇女,担着一副担子,里面装满鲜黄的果子,四周都是浓郁的芭蕉叶,线条繁复,很难画。
六岁的我第一次感觉到力所不能及,小手握着画笔,紧张得直出汗。太爱那些纷繁的色彩,却又内心明知画不出来。那天母亲要去医院值班。母淡淡地说:“你把手绢上的图案画下来。我下班回来要检查。”这样的话,让我心生绝望。我很小就知道,喜欢的事物,不能被人逼着去完成,那样的话也就乐趣全无。母亲却不知。她一心想培养我一个爱好,把小小女子培养成淑女。压力好大。才六岁。’
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觉得自己是大人。我几乎没有童年,知道自己长大后会干一件很特殊的事,静等岁月流逝,从一个小小人儿慢慢长大。
母亲生气的时候,总是骂:“像你这样,长大以后能干什么呀!”我却暗自明确自己能干什么。我很小就识字,心中向往一个职业,那时还不知道叫“作家”,只是隐隐约约知道,长大以后可能会写东西,而不是画画。我羞于告诉母亲自己的梦想,只有每天按时完成母亲交给的任务。在她快要下班回来的半小时前,用画笔在纸上飞快地涂写,色彩涂抹得有些怪诞,线条也丑。
记得童年有一次被带去看荷花。因为手绢上有荷花。我凝望单支荷花,没画什么,只是在想,这太美。许多年以后,我手拿相机站在颐和园相同的位置,轻轻用数码相机,记录下这朵花。快门响起之间那零点一秒,时光飞逝,许多年过去了,而我还站在原地,凝望那朵花。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