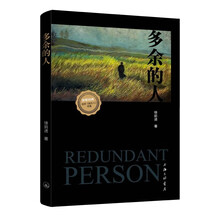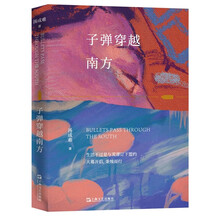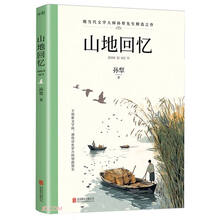结婚五年了,姜淑贞的肚里还没有坐上果儿,让她人前人后都有点儿抬不起头。
常年不见蜂子往上落,再好的花儿还有不瞎的吗?“随军吧,随军……”村里的老辈人叨叨来叨叨去,姜淑贞也就离开村子,来到了商都市。丈夫纪大梁在南关消防中队当着中队长,战友们搭手把中队后院的一间空仓库拾掇拾掇,就成了家属房。
也算是乔迁新居了,何况又赶上大年三十,指导员姚永智领着大家拥进来,说是要闹新房燎新灶。纪大梁一边替战友们拍打着身上的雪,一边吩咐着,“淑贞啊,快,快,下饺子,下饺子!”姜淑贞就着小煤炉小锅灶,把她包的那些大肉酸菜馅饺子下了一锅又一锅,只盼着把人打发了,好和丈夫上床。
饺子塞进肚里了,他们还不走。你一把花生,我一把枣儿,只管往枕头下塞,往床单上撂。
姜淑贞看着,又好气又好笑:“扔啥哩扔,又不是新媳妇。”姚永智一本正经地说:“哎,嫂子,你可不能这么讲。这是老问题,新任务。啥时候不达标,啥时候不算完。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呀?”战士们像喊操一样,齐声叫:“对,对,不达标,不算完。”姜淑贞只好抿着嘴儿,任由他们闹。
这样闹了还不够,姚永智挥挥手,几个战士又嘻嘻哈哈地跟着他扑到了大床上,扯被子,拉枕头,把个大床弄得乱七八糟。
姜淑贞拿眼睃丈夫,巴望着他能说句话。哪知道纪大梁只是站在旁边抽着烟,憨憨地笑。
姜淑贞无可奈何地央求道:“好了吧,好了吧,嫂子求你们,你们该走啦。”姚永智故意耍赖:“不走不走,这年夜饭的酸菜饺子没吃够,没吃饱。”大家跟着起哄:“就是就是,没吃够,没吃好。
”姜淑贞说:“明年吧,明年嫂子腌他一大缸酸菜买他半扇猪,管叫你们吃个够。”姚永智看看墙上的电子钟,这才从床上坐起来。
“嫂子说话算话?咱们拉钩——”“行,以后大年夜都到嫂子这儿来吃酸菜饺子!”姜淑贞把指头伸过去。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战士们像孩子一样齐声嚷嚷。
“好,咱们走喽——”姚永智起身往外走。
“走喽——”战士们跟着。
出了门,还听着他们在外面喊:“明年再来吃饺子!”“明年再来吃——”欢笑声热闹声,都搅进了风雪里。
姜淑贞锁好门,回身对丈夫说:“该睡了,睡。
”纪大梁不情愿地掐灭烟头,遗憾似的叹口气,那情形就像好戏没看完。
姜淑贞半嗔半笑地伸手在丈夫鼻尖上捺了捺,“怪不得你让我包那么多饺子,是不是你们早就串通好,要来咱家闹一闹?”纪大梁说:“当兵的平时生活太单调,这不是个娱乐节目嘛。”“好啊你,拿我出洋相,拿我当猴耍。”姜淑贞攥着拳头,往丈夫身上捶。
纪大梁不但不躲,反而迎上来,嘴里连连叫着,“捶得好,捶得好,这儿酸,往这儿捶!这儿,这儿——”捶着捶着,姜淑贞又捏拿起来。她捶的是经络,捏拿的是穴眼儿,一招一式都像模像样。她爹是中医先生,她也就得了些家传。捏着,推着,拿着,不知不觉地就把丈夫的衣服脱光了。
这一脱,就像冬天的山体去了荫庇,裸露出斑驳嶙峋的疤痕。攀爬跨跳,是消防兵的看家本事,天天苦练,人人身上都留下许多印记。姜淑贞认得出,丈夫身上的乌黑是一些旧伤,而那些青紫则是新近才添加上去的。
姜淑贞脱口道:“咦,你好歹是个干部了,还练那么苦!”纪大梁说:“干部不带头,咋能领兵哩。”姜淑贞摇摇头,嘴里“咝咝”地吸溜个不停。仿佛疼的不是丈夫的皮肉,而是她自己的。怕丈夫受寒,她拉过被子,将丈夫掩起来,然后取出爹配的活血化瘀展筋丹,把手探进去,在那些青紫处揉了又揉。
纪大梁故意“哼哼”起来,做出一副很受用的样子。
“美得你吧!”姜淑贞揉好了,朝着那皮肉就是一巴掌。
“耶耶耶,你这是啥医生,注意点儿医疗态度啊。”“我就是这态度,我就是这态度。”姜淑贞扬手还要打。
“别打别打,这儿还没治,还有这儿——”纪大梁拍拍自己的右肩膀。
那是肩周炎,老毛病。
姜淑贞燃起一根灸条,凑近丈夫的右肩眼儿,晃来晃去地灸起来。
纪大梁陶醉般地眯着眼,和姜淑贞唠闲话。
“淑贞,你到城里了,高楼马路的,没田没地给你种,你不闲坏了?”“你整天张口闭口都是‘组织“组织’的,我就听组织的吧。”纪大梁忽腾一下坐起来,正色道:“淑贞,组织上事太多,咱可不能给组织上找麻烦。”姜淑贞笑了,连忙把丈夫往被窝里推。“瞧你急赤白脸的,我这是逗你嘛。来之前我已经想好了,学我爹呗,开个跌打推拿小诊所……”“哎,对对对,这才是我的好老婆!”纪大梁伸手一拽,就把女人拽进了被窝。
“火火火——你还到被窝里当消防队员呀!”姜淑贞慌忙把胳膊探到被子外面,将灸条在地上捺熄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