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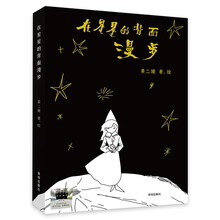







《写作最难是糊涂》为著名作家阎连科的文学随想录,囊括了他数十篇有关文学和写作的短论与随想,以及十几部重要作品的序和后记,为读者展示《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等作品诞生的前前后后。
很少有作家的写作,像阎连科这样和生命贴得如此之近,与痛苦缠得这么紧密,他的作品总是有着一种“灵魂淌血的声响”,走向心灵之死,又使心灵复活。
回忆《日光流年》的写作过程,至今仍使我有着后脊发冷的感觉,那种 备受煎熬的不光是自己的躯体,更是心灵的一次死亡过程。或者说,那是一 次走向心灵之死的漫长写作。13年前,1994年的4月,我从河南携着妻小调往北京二炮部队的电视剧 制作中心,“名分”是编剧,实际上我仍在天天思考着小说。虽然那时腰椎 病使我几近瘫痪在床,每走几步快路,腰的疼痛和左腿的麻木便让我感到活 着没有意义,而死去又是一种恐惧。就在这样的矛盾中,我把家安在了二炮 文化部专门为我腾出的两间会议室里,把床摆在西边,把锅放在东边,把孩 子的课本搁在床头,把新买的拖把挂在公用厕所的门后。收拾一毕,迎接我 的第一件事情,是我的小说《夏日落》因为在香港有了称赞,被那边的一些 报纸杂志誉为是大陆“第三次军事文学浪潮”到来的代表之作:“其第三次 浪潮的宗旨,就是描写军人灵魂的坠落。”他们哪里明白那个时候我们的社 会意识,正忙着进行“反和平演变”,社会思想中,还有着“凡是敌人反对 的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这样一股强烈的暗流。既 然香港那边如此颂赞我的小说,那必然是小说中有着被“敌人”欢迎的地方 ;加之有人连续写信给总政有关部门,状告我的军事文学创作有这样、那样 的问题。于是,我就被组织约去进行严肃的“谈话”。谈话之后,我就开始 忍着腰病,趴在床上一份一份地写着总也不能通过的检查。腰上离不开用钢 板制作的宽大腰带,又因为经常趴在床上写作,出现了不停的眩晕症状,而 寄往《钟山》、《花城》等刊物都已排版的小说全被紧急撤回,精心写出的 检讨又总是被退回修改…… 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在两个多月如行走在黑暗胡同中样等待上级给 我的处理决定中,在我和妻子说好若被处理转业就从此不再写作、一心回家 种地的时候,我又迎来了二炮部队成立三十周年的盛大纪念活动。为了立功,为了表现,为了“将功赎罪”,我拖着病体,希望能为部队三十周年写些 什么。各级领导为了让我能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为了我有一些立功的表现,使人家在帮我解困时有些说辞,也就把纪念三十周年的电视剧的编剧任务恩 于了我。于是,为了完成这部电视剧创作,我就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中国 残联专门为残疾人服务的下属工厂,请他们根据我的病情,为我设计、制作 了一个能在活动躺椅上半躺、半坐、仰头向天进行写作的一个铁器写作架。那个写作架,既能在地上滑动,又能在地上固定;架上的写作板,能根据我 仰躺的姿势,调整出和我手臂、眼睛相适应的各种写作角度。这样,我就在 等待处理决定的过程中,开始了那部歌颂部队官兵“爱国爱军,敢于牺牲” 的电视剧创作。剧本不长,只有十集,取名为《青山巍巍》。可每次我扶着 墙壁或让妻子搀着,从床边走向那只有几步路的写作架时,我都会忍不住掉 下眼泪。妻子问我:“是腰疼得厉害吗?” 我向她摇头。妻子又问:“那为啥?” 我就咬着嘴唇,让她离开,说我要写作了,最好家里没人。妻子就提着 菜篮上街买菜,买完了在楼下转悠,不到烧饭的时候,不回家打扰我的写作。可是,妻子走了,我也不一定真写,就那么躺在椅子上发呆,一呆就是半 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半天。样子好像是在思考我的命运、我的生存,还 有我活着的意义和写作的目的。其实,那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空白中又堆 着些许人生的杂物。就这样,一个多月之后,我交掉了十集电视剧剧本,完成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主旋律写作。就这样,在剧本通过之后的下半年,我躺在残疾人工厂为我特制的写作 架上,开始了长篇小说《日光流年》的创作。因为躺椅太硬,我总是在椅面 上垫下一床被子。那年夏天,写《日光流年》时,我的后背出了很多痱子。那年夏天,写《日光流年》时,关于《夏日落》挨批、被禁的许多事情,慢 慢有了不了了之的结果。后来,听说莫言因为《丰乳肥臀》的创作离开了部 队。后来,见到了一个中国作协的批评家,他说你被不了了之的原因,是港 台都又报道了你阎连科被批的这起事件,祸起于此,祸息于此。而我们单位 的领导,则给我说是,你写《夏日落》是偶然的一桩事情,总体上你是好党 员、好干部,又带病为部队成立三十周年进行写作,就在党员会上作一次公 开检讨,事情也就了了。也就作了公开的检讨。也就继续着《日光流年》的创作。下年,《日光流年》写到三分之一时,电视剧拍摄完毕,还拿了总政的 “星光杯”奖和优秀编剧奖。领奖时我没参加,领导领奖回来开会,兴奋地 在会上表扬了我。我为表扬感动,也为拿奖高兴。可从办公室回家又躺下写 作时,忍不住冷泪直流,默默哭泣。这次流泪,脑子里不是空白。脑子里写 满了生命、生存和生活,还有《日光流年》中人物为活着的意义和无意义。流泪,是为自己在写作中的心灵之死,为心灵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就这 样,我一边四处求医看病,一边躺在椅子上写作。残联为我制作的写字架是 深红颜色,厚漆,写作中漆没被磨掉,可不知为什么我会在那块活动写字板 上涂满了各种各样的墨水,写满了发呆时胡乱写上去的没有意义的字和句子。到了两年之后,第三年时,小说写到了四分之三,我遇到了西安的 一位教马列主义哲学的教授,他对马列主义哲学心存疑惑,可对中医坚信不 已。他是治腰椎病业余、神秘的奇人高手,经了他的精心,最终使我从腰上 卸掉了那六年时间下床时必须捆在腰上的铁板腰带。疾病虽未根除,但却使 我终于可以行走,可以每天拿出一点时间坐下写作。在我可以重新坐下写作 时,我没有继续《日光流年》的创作,而是用一周的时间写了中篇小说《年 月日》。由于对坐下写作的渴望,由于坐下写作又给我带回了写作的生命之 愉,《年月日》的创作不是在写,而是在泻,一稿而就,就而寄出。1997年11月,我完成了《日光流年》的初稿,完成了走向心灵之死、又 使心灵复活的一次写作。那年单位年终总结,因为我连续几年表现不错,或 多或少进行了主旋律的创作,大家一致同意要给我记功,可被我委婉而拒了。我说:“我把我的长篇写完了,我已经给我记过了功。” 2007年1月21日于北京P49-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