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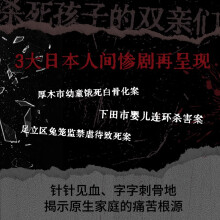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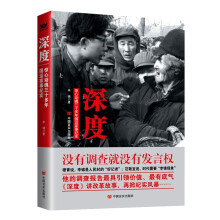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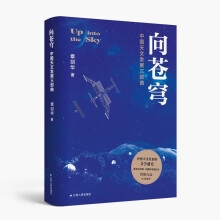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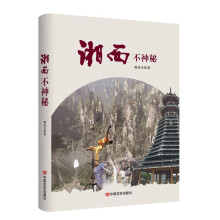
我是杂食动物,吞食感情、生物、书籍、事件和争斗。
我真想把整个大地吞下。我真想把大海喝干。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自传
全新修订版新增8万字+10张珍贵手稿
巴勃罗·聂鲁达是二十世纪所有语种中ZUI伟大的诗人。他书写任何事物都有伟大的诗篇,就好像弥达斯王,凡他触摸的东西,都会变成诗歌。——加西亚·马尔克斯
访问中国时,得知自己中文译名中的“聶”由三只耳朵组成,他说:“我有三只耳朵,第三只耳朵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声音。”——巴勃罗·聂鲁达
海报:

聂鲁达,举世闻名的伟大诗人。他踏遍世界,足迹密布亚洲、欧洲、美洲。他是历尽沧桑却始终拥有童心的孩子。
以一段段诗意而饱含人生体验与智慧的文字,缀连起宽广似海的一生,放射着有趣灵魂的恒久光芒,映照出整个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
我的生活丰富多彩,这是诗人的生活。
我是杂食动物,吞食感情、生物、书籍、事件和争斗。我真想把整个大地吞下。我真想把大海喝干。
我家里收集了大大小小许多玩具,没有这些玩具我就没法活。不玩的孩子不是孩子;不玩的大人则永远失去了活在他心中的孩子,而那却是他十分需要的。我也像造玩具那样建造我的房子,并且在这所房子里从早玩到晚。
我要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就只是人,除此没有其他头衔。人们不会为一条戒律、一句话、一个标签而苦恼。
我见过不同的海洋,遇见过无数的人。我改变过许多回。每当我试图回忆,我的诗歌就开始层层堆叠,重新组合,就像书页被弄湿时那样。
这部回忆录是不连贯的,有时甚至有所遗忘,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如此。断断续续的梦使我们禁受得了劳累的白天。我的许多往事在追忆中显得模糊不清,仿佛已然破碎无法复原的玻璃那样化作齑粉。
传记作家的回忆录与诗人的回忆录绝不相同。前者也许阅历有限,但着力如实记述,为我们精确再现许多细节。后者则为我们提供一座画廊,里边陈列着受他那个时代的烈火和黑暗撼动的众多幻影。
也许我没有全身心地去体验自己的经历;也许我体验的是别人的生活。
我写的这些篇章,将像金秋时节的树林和收获季节的葡萄园那样,从中必定会落下正在枯萎的黄叶,也会结出将在祭神的酒中获得新生的葡萄。
我的生活丰富多彩——这是诗人的生活。
现在,我又见到了特木科,这个位于祖国南部的城市。在我漫长的童年时代,它意味着世间所有现实和所有奥秘。之所以说是漫长的童年时代,是因为在那些阴雨绵绵的寒冷地区,年龄是静止不变的。
智利南部的树木得等上几百年才会长大。于是,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几乎所有的景致都已被破坏。庄园的主人毫不留情地烧毁了美妙的古老森林。人类的贪欲推动了这场规模浩大的破坏活动。他们需要能够迅速长大的树木。这是做木材生意的需要。
我童年记忆中的城市留下的东西所剩无几。当然了,熟悉的面孔更是几乎一个也没有。另一群孩子,另一群老人,另一群拥有陌生眼睛的人。
我只找到了一副熟悉的面孔,我立刻认出了它,它似乎也认出了我。那是一匹大木马的脑袋,摆在村里的老皮具店里。它的周围摆满了一成不变的商品:马鞍,拴牛的皮绳,刺激马儿飞奔的巨大马刺,粗鲁骑士用的宽腰带。
但是,在那堆迷人的农具里,只有那匹大木马的玻璃眼珠再次让我着迷。它带着无尽的悲伤看着我,它认出了那个孩子,他不止一次环游世界,现在又回来问候它了。它和我都已经老了。我们当然有很多话要向彼此诉说。
在五十年前的特木科,生意人会在门前挂上巨幅图案,以此宣传自己的商品。从偏僻神秘的藏身处远道而来的阿劳科人远远地就能看清楚在哪里可以买到油、钉子、鞋子。街角的那把大榔头告诉他们那里有工具卖。他们也可以在“锁具”五金店里买到工具,那家店的标识是一把蓝色的大锁。鞋匠把大靴子高高地挂在店里,以便招揽阿劳科人。三米高的木制调羹和钥匙明白无误地指点他们在哪里可以买到米、咖啡和糖。
我曾经穿着短裤,怀着极大的敬意从这些庞大的标识下走过。我觉得它们来自一个大而无当、怪诞而危险的世界,就像邻近丛林里挂在高耸入云的大树上的硕大蕨类植物和藤蔓。它们属于让简陋的木屋颤动的狂风,属于突然开始用烈火的语言歌唱的火山。
引言
题记
一年轻的乡巴佬
二浪迹城市
三走向世界之路
四灿烂的孤独
五西班牙在我心中
六出发寻找阵亡者
七多花又多刺的墨西哥
八黑暗中的祖国
九流亡始末
十归航
十一写诗是一门手艺
十二亲切又冷酷的祖国
演讲、手稿及其他自传性文章
附录
巴勃罗·聂鲁达是二十世纪所有语种中ZUI伟大的诗人。他书写任何事物都有伟大的诗篇,就好像弥达斯王,凡他触摸的东西,都会变成诗歌。
——加西亚·马尔克斯
他的诗篇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
连聂鲁达的家也都是诗,是《大地上的居所》和《漫歌》的复制品和确证。
——胡利奥·科塔萨尔
聂鲁达同时拥有睁开的和闭上的眼睛。梦游人的眼睛。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帕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