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则爱情“丑闻”中的民国女性
同性恋与单身之罪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风卷了媒体的丑闻中, 女性总是扮演着一种带有侵略性的角色。这些丑闻在公众中引起的反应可为我们提供一个间接的视角,观察当时的社会是如何调整并适应着变化中的性别关系和亲密模式。
在五四时期浮出水面的一代女性,在争取个人权利和自主的斗争张,把自由恋爱作为一种有力的武器抓在手中。与政治参与权、经济独立权和受教育权不同,恋爱与婚姻的自由似乎是一种卓然个人化的功业,可以为一切勇敢的灵魂所得,而且最不易受到来自社会制度之惰性的阻挠。对她们而言,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而通往解放之路的起点 即在自己的家中,始于同父母就婚姻问题展开对峙,包括是否结婚、何时 结婚以及与谁结婚。尽管如此,到20 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时候, 典型的桥段已经发生转移,从一名女儿对于家庭的反抗,变成挣脱束缚后的女性在缺乏家庭管束的条件下对于爱情生活的灾难式管理。在保守派看来,性丑闻的出现证明,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把女人交付到她们自己的 手中。甚至连自由派的批评家,也惯于把丑闻解读为女性不成熟、缺乏经验以及无力在爱的矿藏探寻中保持平衡的证明。可是当涉及可行的解决方案时,公共舆论的区分仍如以往一样泾渭分明,而在“爱情定则”论争中 提出的议题也一再重现。
陶思瑾和刘梦莹的个案,把恋爱关系中女性的侵略性或越轨行为的问 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或者在某些观者看来,是一个新的低点)。 陶思瑾和刘梦莹是两名女学生,经由作家许钦文相识,并同宿在许钦文家中。1932 年某天,在两名室友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陶思瑾拿厨 房里的一把菜刀砍死了刘梦莹。这起事件吸引媒体趋之若鹜,争相报道, 对其新闻轰动性的开发与利用,持续了数月有余。许钦文即刻成为众矢之的,不论是法庭还是公共舆论的审判场,都指控他与两名女子卷入了一场三角恋爱,并任由嫉妒日益加深,终致升级为一场谋杀。陶思瑾和刘梦莹的日记揭示出,二人已经维持了一段长达三年的热烈的同性爱情关系。可 即便如此,许钦文依然不断接到法院的传票,在刑事与民事法庭上先后 受到共计 10 项指控。最终,他还被判入狱,服刑超过 10 个月之久。“三角恋爱”范式的影响力如此之大,竟足以让杭县的地方检察官以“年逾三十,尚未娶妻”和“以鳏居之人,而容留青年女子”两项罪名立案起诉许钦文(许钦文,1937,5)。
在许钦文的陈词中(部分以法庭对日记内容的选择性披露为依据), 陶思瑾和刘梦莹情火炽烈,乃至于立誓永结盟约,并购买订婚戒指。她们为同性爱的坚强、高贵与亲密而深感无比骄傲,而当两人之间滋生出不协 和的信号时,她们又感到无比的苦痛。可尽管事实披露如此,法庭和公众 仍然坚持以异性恋的方式对此事进行解读,甚至提出,即便不是(有充分 的不在场证明的)许钦文,也有其他的男性参与共犯。莫名其妙地成为司 法与民意偏见的受害者之后,许钦文对于女性、法庭传统而保守的先入之见以及媒体之间的火热竞争,秉持着一种悲悯的心态;可与此同时, 他本人也为渲染这起事件投入了不少笔墨,其中就包括他在《无妻之累》(1937)和《两条裙子》(1934)中收入的一系列回忆片断。许钦文在回忆 文章中对纠缠数年的审判过程进行了轶事化的讲述,并为“性的倒错”提供了现代心理学式的分析(许钦文,1937,145—150)。从本质上来说, 他赞成普遍认同的观点,即同性恋是一种未满足的异性欲望的变体,它可 以像后者一样,在强度上极为“锋利”,而在表达上则相当“荒谬”(郑婴, 1930,3)。如果说,许钦文对于这起事件产生兴趣,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潘光旦 在他主办的杂志《华年》周刊上发表的评论,则更像是受到了专业冲动的驱使。
潘光旦基于法庭材料、新闻报道和他与一位知情朋友的私人通信做 出诊断,肯定地鉴别出偏执妄想的症状,或曰“谕旨式的幻觉”(原文的 英文翻译为“imperative hallucinations”),并把这些症状归因于由火炽热情 所催发的酷烈嫉妒心(潘光旦,1993,8:437—438)。潘光旦以他在冯小青研究中同样的方式(第五章),为这一诊断添加了一剂社会改革的药方。 他感到痛惜的是,中国几乎不存在合格的精神病专家,可供法院传唤,以 确认被告的精神状态。他们的专业意见可具有定夺被告生(减刑或无罪释 放)与死(死刑)的意义(潘光旦,1993,440—441)。而即使被告足够幸运,得以脱罪,又什么措施可以防止再犯?“试问社会将如何安放。让 她回家么?让她再进学校或其他公共场所么?谁能保她不再发生同性爱, 不再妒,不再杀?”(潘光旦,1993,441—442)。最后,潘光旦指出,目下中国的学校制度装备不足,难以应对青少年的情绪烦扰。所谓的训育主任,只晓得如何与洗衣工暗中串通,监控学生手淫的频率;至于如何帮助 学生管理他们的情绪生活,而令他们不再有手淫的必要,训育主任却毫无 头绪。潘光旦将问题的根源定位于社会制度的欠缺,与当时主流的道德 式回应拉开了醒目的距离;后者的展开,主要依赖的是个人化与极端化的 话语:浪漫之爱腐蚀了道德素质;那些为爱而杀人之人,他们的行为都出 于可鄙的自私动机;不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爱情都不能减轻一个人在道德与法律上所犯的罪孽。
情场女侠
另一起牵涉到两名女子的事件,极具说服力。事件中的两名女子分 别扮演了侵犯者和受害者的角色,其中侵犯的一方被奉为女英雄而得到人 们的追捧,究其原因,便是她居于三角恋爱之外的位置。张璧月与张璧池两姐妹同在远方的一所中学求学,而已经订婚的璧池却与她们已婚的教师 黄长典纠葛在一起。他们的私情被璧月发觉之后,璧池因为惧怕父母的怒 火而逃到了另一个城市。璧月与黄长典当面对质,并向他开枪射击(虽不致命),随之获罪入狱。在服刑期间,璧月成为媒体的焦点,轰动一时,公众也鼓噪喧哗,一致要求将她释放。不久,她的学校便将她保释出狱。 在《新女性》上的一则评论中,署名芳心女士的作者区分了公众反应的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堆砌了大量对璧月的吹捧,将她的行为作为一次向 自由恋爱的正面攻击而大加颂扬。这位作者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令人惊 讶的事实:持有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礼教道德家和抱残守缺的儒家旧党,还包括自诩的“青年志士们”。第二种反应是谴责璧池的轻信与天真,竟 然让自己甘心接受一名已婚男子的勾引。第三种主要是来自两姐妹所在学 校同窗的声音,指认黄长典为真正的恶人,厚颜无耻地将一名女学生诱入 一段虚假的承诺关系,因而活该被枪击。公众情感似乎压倒性地倾向于璧月,这位意图谋杀而未遂的罪犯。据说,甚至连冰心(1900—1999)也曾致信给她,称赞她的勇气。在娱乐的舞台上,也上演了一出赞美其英勇气 概的戏剧,并冠以一个吸人眼球的标题:“情场女侠张璧月”(芳心女士, 1929)。
芳心女士违逆公众的热情,给出了她自己的如下判断。璧月以暴力恐吓所谓的同流合污之人,蓄意地干涉了她妹妹的恋爱权利。而璧池也并非毫无指摘之处:如果她有勇气爱上一名已婚男子并要求他离婚,那么当情事隐瞒不住时,她也应该有勇气直面自己的家人。黄长典受到了不恰当的指责,因为他在自己的已婚状态一事上并没有欺骗过璧池。他真正的错误,只在于他竭力隐藏两人偷情的秘密。芳心女士在论文的结语中充满焦虑地指出:“这次惨杀案表示出来,我国社会现存制度下 [……] 反动的空 气窒息的喘不过气来的青年男女 [……][ 以及 ] 宗法因袭即封建思想与势 力。”(芳心女士,1929,358)
这位评论者显然不甘心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违法者得到公众舆论慷慨的宽恕,而受害者却只是因为违反了由保守派和自由派共尊的爱情的潜在法则,反而成为公众羞辱的靶心。璧月被神化为“侠”,说明女子的行动力若想获得认可与承认,前提是她的行为必须英雄般地代表了某些其他的人或事。如果璧月与璧池两姐妹都卷入了与这位教师的浪漫纠葛中,则暴力事件将不可避免地被解读为衍生自三角恋的争夺,那么对于璧月的批判 便绝不会比陶思瑾所承受的更轻。事实正与此相反,璧月完美地符合了将果决的行动力与弃己结合于一身的女侠典型(回想第一章曾讨论的《儿女英雄传》中的十三妹),被推崇为“现社会新女子最好的典型”。看起来, 新女子最为高尚的使命,是在于维护安定,而非“情场”流连。然而,来自芳心女士的异质声音提示出,在后娜拉时代,并非所有的女性都愿意接受这种以反浪漫主义的逞勇斗狠而赢得声名的角色楷模。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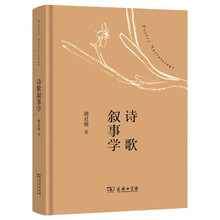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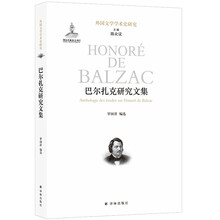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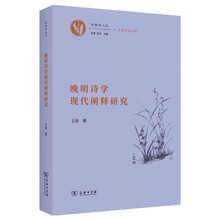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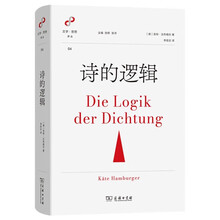

——杨联芬 人民大学教授
李海燕描述了爱情与传统道德、启蒙、个体、市场、市民、民族主义、社群等多个主题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前所未见的哲学深度探讨了中国的现代性的重要问题:进入现代社会后,很多之前的信仰和资源都被颠覆了,情感却能成为一种合法的媒介,情感到底在社会转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它自身又被怎样塑造?
——王斑 斯坦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