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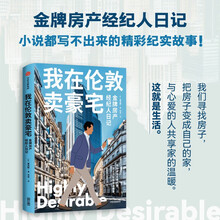



《俄国纪行》: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旅行纪实名篇,收录传奇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旅途全程拍摄的数十张纪实作品。
海报:
《俄国纪行》是著名作家约翰?斯坦贝克与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 40天苏联之行(1947年7月至9月)的记录。这是一次巨人之间的伟大合作。斯坦贝克和卡帕的足迹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从乌克兰田园到格鲁吉亚海滨。斯坦贝克充满热情、同情而又幽默生动的文字,与卡帕卓越的摄影写实珠联璧合,真实展现了苏联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
俄国纪行
第一章
缘起
这则故事和这趟行程的发端和用意,有必要先说个明白。三月底,我——向约翰·君特特别讨请才能使用这个代名词——坐在东四十街贝福特旅馆酒吧内。改了四遍的戏本已销毁,从指间流逝,我坐在吧台凳子上,沉吟着下一步要做什么。这时,罗伯特·卡帕有点落寞地走进酒吧。打了几个月的牌局终于收场,书也送进印刷厂,他蓦地发现自己无所事事。向来善解人意的酒保威利,建议来一杯天下无双的“瑞士酒”。我们闷闷不乐,倒不是新闻因素使然,而是处理新闻的方式所致。因为,新闻已不再是新闻,起码在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如此。新闻已经变成硕儒俊彦的事。高踞华盛顿或纽约案头的人看看电报,配合自己的心态重做编排,再签上文末署名。我们常看的新闻已经不是新闻,而是寥寥可数的学究对新闻意义的看法。
威利把两杯浅绿色的瑞士酒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开始谈论,在这世道,诚直开明的人还能有何作为。报纸上,有关俄国的消息每天不下数千言。斯大林的想法、俄国参谋总部的计划、军队素质、原子武器和导向飞弹实验等,全都由不在现场的人所写,他们的信息来源绝非无可非议。于是我们想到,有些跟俄国相关的事还没人写,而这些事正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那里的人穿什么?餐会中上的是什么菜?有什么食物?他们怎么做爱,怎么处理死亡?他们谈论什么?他们也跳舞、唱歌和演戏吗?孩子是否要上学?我们觉得,去探探这些事、拍拍他们、写写他们,不失为好事一桩。俄国政治诚然跟我们的政治一样重要,但那里想必也一样还有重要的另一面,想必也有我们无法看到的俄国民众的私生活,因为从来没人写过,也没人拍过。
威利又调了杯瑞士酒,他附和我们的看法,说他对这种事也有兴趣,想看的正是这些东西。于是,我们决定一试——纯粹报道,辅以照片。我们要合作。我们要避开政治和较重大的问题。我们要避开克里姆林宫、军人和军事计划,尽量接近俄国民众。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并不知道是否可行,反而一跟朋友提起,他们倒是很笃定我们办不到。
我们的盘算是:若能办到,很好,可以有篇很好的报道;若办不到,我们也会有篇报道,谈谈怎么力有不逮。打定主意后,我们打电话到《纽约先驱论坛报》邀乔治·柯尼希(George Cornish)聚餐,告诉他我们的计划。他同意这是件好事,答应尽力协助我们。
我们共同敲定几件事:我们不应该去挑衅,应该尽量避免批判或示好。我们要尽量据实报道,写下所见所闻,不加论述评断,对自己不充分了解的事不妄下结论,也不为行政官僚延误生气。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碰到很多不了解、不喜欢和不自在的事。这虽是外国实情,但我们决意即使要批评,也应该是事后,不是未曾眼见就批评。
签证申请在适当时间送往莫斯科之后,我的签证在合理时间内获得了批准。我前往纽约苏联领事馆,总领事说道:“我们同意这是件好事,但你为什么非得带摄影师同行不可?我们苏联有很多摄影师。”
我答道:“但你们没有卡帕。既然要做,就得合作,把事情做得圆满。”
苏联有点不情愿让摄影师入境,对我倒是没有不情愿,在我们看来,这倒是很奇怪,因为检查管得了胶卷,却管不了观察者的心。我们在苏联之行全程中发现一件真实不虚的事,有必要在这里稍加说明。相机是最可怕的现代武器之一,对那些曾经历战火、挨过轰炸和炮弹的人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在一阵轰炸之后必然是摄影;残破的城镇和工厂背后,通常是利用相机做空中制图或侦测制图。因此,相机是令人畏惧的器材,携带相机的人到哪里都受到怀疑和监视。你若不信,不妨带着布朗尼四号(Brownie No. 4)柯达相机到橡树岭、巴拿马运河或全国上百个实验区附近便知分晓。今天,在很多人心目中,相机不啻是毁灭的前兆,引人疑窦可谓其来有自。
我不认为我跟卡帕真以为可以如愿去做这件事,是以我们也跟别人一样大感意外。签证下来时我们吃了一惊,于是跟威利在酒吧稍微庆祝一下。这时,我发生意外摔断了腿,躺了两个月,卡帕倒是四处搜罗器材。
多年来一直没有美国人摄影报道苏联,所以,卡帕不但张罗最好的摄影器材,还多准备了一份备用以防失落。当然,他除了携带战时所使用的Contax和Rolleiflex相机之外,也额外多带相机。他额外带的相机、底片和闪光灯实在太多了,国外航班超重费用就付了三百美元左右。
我们要前往苏联的消息一传开,各式的忠告、告诫和警告纷至沓来,值得一提的是,多数人都不曾到过那里。
有位老妇人以惊恐的口吻告诉我们,“哎呀,你们准会失踪,你们一过边界就会失踪”!
我们以精确报道的兴味答道:“你知道有人失踪?”
“不,”她说,“我个人虽不知道,但确实有很多人失踪。”
我们说道:“这话也许不假,我们也拿不准,你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个失踪者的名字?你可知道有谁知道有人失踪?”
她答道:“有好几千人失踪了。”
有位男士别有深意地耸耸眉,满脸狐疑地对我们说:“你们想必跟克里姆林宫很有交情,否则他们不会准许你们入境。一定是他们收买了你们。”此人其实就是两年前在史托克俱乐部发表诺曼底登陆总体方案那位仁兄。
我们说道:“不,据我们所知,他们没有收买我们。我们只是想做点报道的工作而已。”
他抬眼瞅着我们。他一认定便自以为是,两年前知道艾森豪威尔心思,现在也了然斯大林的想法。
有位老绅士朝着我们一颔首,说道:“他们会拷问你们,这是他们的做法;他们会索性把你们关进黑牢再行拷问。他们会扭你们的胳臂,让你们饿肚子,直到你们乖乖顺从,说他们要你说的话。”
我们问道:“为什么?所为何来?有什么目的?”
“他们对谁都是这样,”他说,“我前几天刚看过一本书说……”
有位相当有分量的商人对我们说:“去莫斯科,嗯?带几颗炸弹去炸炸红小子。”
各式忠告逼得我们透不过气来。有人告诉我们该带食物去,否则准会饿死;什么通信线路该保持畅通;偷运数据出境的方法。世上最难说得清的是,我们只是想报道一下俄国人的模样、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农民们聊些什么与如何重建残破国家。这是世上最难解释的事。我们发现,好几千人都患了莫斯科病,也就听信荒诞意见和排除事实的状态。当然,我们也发现俄国人同样患了华盛顿病。我们发现,我们丑化俄国人之际,俄国人也在丑化我们。
有位出租车司机说道:“他们俄国人呀,洗澡时男女共浴,不穿衣服。”
“真的?”
“当然是真的,”他说,“这是不道德的。”
追问结果,原来是他看过一篇芬兰蒸气浴的记事,却把气出在俄国人头上。
听了这些情报之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约翰·曼德威尔爵士(Sir John Mandeville)游记中的世界绝未消失,双头人和飞蛇的世界依旧。
的确,我们出国期间所出现的飞碟,并没有推翻我们的命题。在我们看来,当今世上最危险的趋势便是,宁愿相信流言,不追究事实。
我们前往苏联时所携带的最佳装备,是汇聚在一个地方的所有流言,而我们在本文中所坚持的是:一旦我们记下流言,就可称为十足的流言。
我们在贝福特酒吧跟威利喝了最后一杯瑞士酒。威利已成为我们这个计划的专任合伙人,瑞士酒也越调越出色。他给我们的建议中,不乏最好的忠告。威利很想跟我们同行。他若能成行倒不失为美事一桩。他给我们调了杯上好的瑞士酒,自己也呷了一杯之后,我们终于准备动身。
威利说道:“你们在吧台后学到了多听少说。”
往后几个月,我们常想起威利和他的瑞士酒。
事情就这么开头。卡帕带回大约四千张负片,我也带回几百页札记。我们一直在沉吟如何把此行做个了结,几经讨论后决定依照日程、经历和见闻不加区别地如实写下来。我们要写下所见所闻。我知道这种做法跟大部分的现代新闻报道背道而驰,但唯其如此本文也不失为一种调剂。
这只是我们的经历。它不是俄国故事,而是一则单纯的俄国报道。
前言(苏珊·席林洛)
第一章 缘起
第二章 抵达苏联
第三章 莫斯科生活
第四章 基辅
第五章 乌克兰见闻
第六章 斯大林格勒
抗辩书(罗伯特·卡帕)
第七章 格鲁吉亚
第八章 第比利斯
第九章 旅行结束之前
《俄国纪行》是斯塔贝克经典作品中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其重要性尚未为世人完全认知……斯坦贝克细心安排的短文,一如卡帕的照片,所摹写的是他自己对一个被战争夷平、宣传充斥、否定言论自由、深信计划式反应真实不虚的国家与人民的情绪反应。
——苏珊·席林洛(Susan Shilling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