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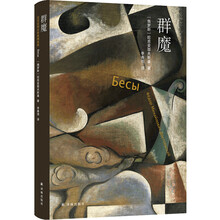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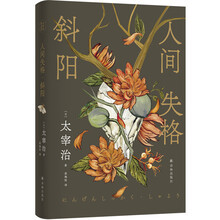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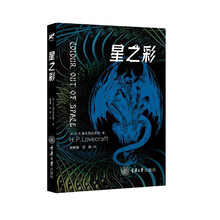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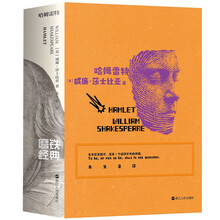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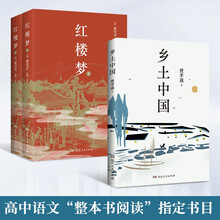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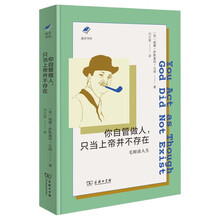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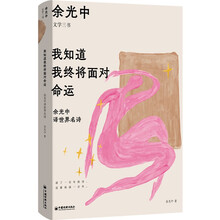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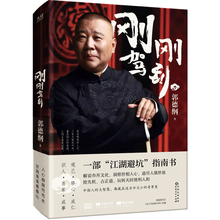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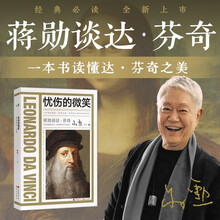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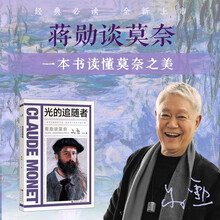
余光中是两岸三地受欢迎的散文大师之一。他的散文,壮阔铿锵,又细腻柔绵,余光中最经典、最艺术的散文评论集,首次在大陆公开发行,极具收藏价值。
《从徐霞客到梵高》是余光中继《掌上雨》和《分水岭上》之后的第三本纯评论文集。其中的十四篇文章,一半写于香港,一半写于高雄;最早的一篇写于1981年,最晚的则写于1993年。书名《从徐霞客到梵高》,因为其中有四篇文章析论中国的游记,另有四篇探讨梵高的艺术,占的分量最重。游记既为散文的一体,往往兼有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之功,因此论游记即所以论散文。
梵高
英国诗人兼艺评家李德在《艺术的意义》一书中轩轾梵高与高更,认为梵高之所以不朽,端在贯彻一个“诚”字。他说:“高更的命运就不像(梵高)这么确定了。他不像梵高这么对自己坦诚。看过梵高的书信再看高更的日记,只令人觉得他性情浮躁,不可忍受。他太自负了。”
高更提倡综合主义,并以中世纪和埃及的艺术为例,说明艺术的本质是“装饰性的”(decorative)。他有四句口号如下:
为艺术而艺术。为什么不?
为人生而艺术。为什么不?
为作乐而艺术。为什么不?
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是艺术。
李德对此大为不满,他说:“所以也可以为装饰而艺术——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是艺术。说一幅画具有装饰性,等于说它缺少某种价值,这种价值我们可以叫做人性(因为此地不在讨论神性)。拿高更和梵高一比,我们立刻注意到其间的差异:那就是,这位荷兰人对人类充满热爱,而且一直努力用他的艺术来表达这热爱,正如,据他所知,莎士比亚和伦勃朗表达过的一样。也许有人会说,那只是文学的志向,和画家的眼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是艺术。但是艺术并不是一种抽象;艺术是一种人性的活动,只有透过某一个人的个性才能完成。某人个性之品质将充溢其艺术之抽象性质,而其艺术之价值将取决于其人性感受之深浅。由此而来的充实感,求之于梵高则有余,求之于高更,求之于高更全部作品的动人之美,却显然不足。”
李德对这位象征派大师的评断未免太苛。指责高更的艺术失之装饰,是可以的,但是从一个人的日记来推断他艺术的高下,则未免诛心之论。许多艺术大家确很谦逊,但是自负的人未必不能成为宗师。不过在另一方面,说梵高艺术的可贵,主要在其诚心,我却完全同意。
梵高是一个元气淋漓、赤心热肠的苦行僧,甘心过最困苦的生活,承受最大的压力,只为了把他对人世的忠忱与关切,喷洒在他一幅幅白热的画里。梵高一生有两大狂热:早年想做牧师,把使徒的福音传给劳苦的大众,却惨遭失败;后来想做画家,把具有宗教情操的生之体验传给观众。他说:“无论在生活上或绘画上,我都可以完全不靠上帝,可是我虽然病着,却不能没有一样比我更大的东西,就是我的生命,我的创造力……在一幅画中我想说一些像音乐一样令人安慰的东西,在画男人和女人的时候,我要他们带一点永恒感,这种感觉以前是用光轮来象征,现在我们却用着色时真正的光辉和颤动来把握。”
“光辉和颤动”(radiance and vibration)正是梵高画中呼之欲出的特质。两者都来自他的赤忱,流露于色彩,便成他画中奇异的光辉,表现于线条,便成为他画中蟠蟠蜿蜿起伏汹涌无始无终的颤动、震动、律动;无论这些特质是起于他的宗教狂热,癫痫症,或是天才,总之看他的画,尤其是后期的成熟之作,常令人肺腑内炽,感奋莫名,像是和一股滚滚翻腾而来的生命骤然相接,欲摆脱而不能。梵高的人像画,无论对象是荷兰村野的食薯者,比利时诗人巴熙,法国南部的邮差鲁兰和儿子亚蒙,阿罗的女人,布拉班特的老农夫,目光忧郁的嘉舍医生,或是一幅又一幅的自画像,无不笔简意深,充溢着同情与了解,对象的性格强烈地流露在脸上,手上,敏感的眸子里隐约可窥灵魂的秘密。雷诺阿把原已可爱的人物画得更美,劳特累克把原来不美的人物画得更夸张,更突出,梵高把原本平凡的人物画得具有灵性和光辉,而更重要的是,具有尊严,其结果乃是艺术之至美。看遍了西方的现代画,没有一位大师的人像画比梵高的更富于人性。李德说梵高的艺术,由于关心生命的目标,不应归于马奈、塞尚、高更、雷诺阿之列,而应与他生平崇拜的伦勃朗和米勒相提并论。我觉得梵高其实应该置于伦勃朗之旁,米勒之上,因为米勒的田园颂歌今日看来未免有点伤感,他的感性似乎承先的成分多于启后。如果要在诗人里面找梵高的伴侣,我倒愿举出两位博爱众生的伟人:布莱克和惠特曼。梵高不像布莱克那么形而上,也不像惠特曼那么达观,他的画里也看不出像他们诗中那种对动物的爱护,对孩童的赞美;但是对于人类和自然的忠诚和敬爱,梵高的画似乎更白热化。
梵高的人画像,尤其是他的自画像,常给观画者强烈的震撼,这种感觉,我在看中国传统的画像时从来没有经验过。不但画中人的性格、表情,尤其是眼神和嘴态,复活在纸上、布上,即使背景的色彩和线条,也尽了象征与陪衬之功。我从未见过一幅画像能像“比利时诗人巴熙像”那么单纯、宁静,而又崇高。诗人的外套黄得暖极、亮极,他的须发又黄又绿,真是天真有趣,拙极巧极,他的眼神澄明而又凝定,像在倾听宇宙间无边的宁静,只因为他的背后是密蓝色的夜空,深极冷极,却闪着几点似花又似星的光芒,噢,可爱之极、美极。绿发与蓝空都浓极稠极,于是用一道鲜黄色向中间分开,真说不出这一手是拙招还是绝招。这些对照鲜丽的、武断而又纯粹的色彩,或许也受了高更的理论启示,但是画中的人性,那一股对于诗人朋友的敬爱,却出于梵高的内心。
巴熙(Eugène Boch)并不是名诗人,但一登梵高的画像,也就似乎戴上了梵高所谓的光轮,不朽了。此图作于1888年,亦即画家死前二年,是巴黎印象馆中所藏梵高二十一幅人像画的杰作,但是另一幅人像:“嘉舍大夫”,也许更加有名,不是因为画得更好,而是因为受画者嘉舍医生是一位慧眼识天才的先知,不但是许多印象派画家之友,并且在举世不识梵高为何人之时肯定了梵高的成就,成为他临终前最后的知己。“嘉舍大夫”作于梵高逝世之年,和“奥维教堂”、“麦田群鸦”同为最后的名作。图中的医生斜坐在桌旁,一手扶桌,一手握拳而支颐,若不胜其慵倦与烦忧,蹙眉之下,一对蓝色的眼眸茫然出神地凝望着虚无,那么沉郁而多思。画中的基调是冷肃的蓝色,从医生外衣的黯蓝到背景的灰蓝和钝蓝,分成三层,而以圆桌的鲜朱红色来衬托。和“比利时诗人巴熙像”的安详相比,嘉舍医生显然心有郁结,神情不安;也许这时画家自己的生命更充满着痛苦与烦恼,所以主客的情绪很容易合为一体。
不过梵高的人像之中,最动人也最祟人的,仍是他的自画像。英国批评家霭理斯曾说:“一切艺术家所写者莫非自传。”画家的自画像本就相当于作家的自传,可是梵高作自画像,不但为了自我探索,也因为他太穷,雇不起模特儿,也画得太“怪”,不讨人喜欢。他的自画像极多,癫痫症发作以后尤然,而无论所画是侧左或侧右,戴帽或露顶,割耳前或割耳后,都给人“把灵魂裸露在脸上”的感觉——那鼻梁的孤挺,那嘴角的执着,那颈项的倔强,还有那总是带点怒意或是忧容的蹙眉之下,那两只正在灼灼探人的、又沉郁又渴望又寂寞的眼睛,在在流露着殉道者的悲剧性格。甚至那黄中带红的须发,也似乎沿着两腮的乱髯,因内热的煎熬而燃烧成一片。甚至背景也不甘寂寞,因律动的线条而蠢蠢欲动或已骚然旋转,成了蓝漩涡似的滚滚光轮。这种自画像,巴黎印象馆中藏有两幅;我认为最祟人的一幅,画家以左手拇指勾住调色板,而背后蓝涛滚动着漩涡的,却在纽约。
印象馆里悬挂的梵高作品,最有名的应推“奥维教堂”和“阿罗的梵高卧室”。两画的色调,一幅阴沉而神秘,另一幅温暖而亲切,各有千秋。梵高后期作品,纵情于鲜黄,至于狂热的程度,为了平衡色调,又用深蓝来反托,造成视觉上也是情绪上的紧张对立——那幅鲜丽无比,令人对画惊叹的“夜间的露天酒座”便是如此。
梵高的风景画当然也有许多神品,其中有宁静可以卧憩的,也有波动令人不安的。我认为后一类里杰作最多,也最近于他的人像画。看过“秋收”和“阿罗医院的花园”等宁静的作品,再看“橄榄园”、“小麦田与松树”、“奥维教堂”、“麦田群鸦”等激动的作品,令人惊讶之余,发现梵高的风景竟可以分别表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心境。在“秋收”一类的画里,几乎所有的线条都是直的,其方向不是水平便是纵立;但是在“橄榄园”中,几乎所有的线条都是曲线,地势在波动,树态在蟠蜿,天色在奔泻,形成了一个回旋不安律动不歇的青绿盘涡。在“奥维教堂”里,前景的草地、黄花、红沙,是亮丽的人间,但背景的蓝空,蓝得那么秘不可解,怪不可测,却是永恒,可是中间的教堂,曲线则蠕蠕而动,直线则岌岌欲倾,整座建筑的感觉是歪的;加上钟楼上两面圆钟斜睨之眈眈,呼应着下面一排排玻璃彩窗之瞑瞑,真像一场猛烈的梦境。梵高把这些风景画成了人,具有人体外在的形貌和内在的激情。
梵高从印象派学到光的生命,从点画派学到分色,又从象征派学到武断而纯粹的色彩,但是有一样东西完全是他自己的。那便是线条,尤其是那些断而复续,伏而复起,去而复回的又粗又短的曲线,像是宇宙间生生不息动而愈出的一种节奏,一种脉搏。那线条总是一动百随,紧密排列;那种曲行之势,不是飘逸,不是精美,而是顽强粗犷,富于弹性。也有艺评家不满梵高的艺术,认为他始终只是一位素描家,认为他画油画的方式就像别人画素描一样——也就是说,他的基本表现手法仍在线条,尤其是粗线勾勒的轮廓。但是梵高作品的气势,那种笔挟风雨一气呵成的节奏感,也正在此。抽去他画中那些鲜活、健旺而又武断的线条,就不成其为梵高了。那些元气淋漓的线条,以简驭繁,拙能生巧,每一笔,都是梵高用他的胆汁签下的名,没有人能够冒充。
梵高作画,前后只有十年,比起毕加索来,只得七分之一。从二十七岁到三十三岁(1880-1886),是他的荷兰时期。这时他的眼界未宽,取法的对象是田园写实主义的巴比松派,形体重拙,色调阴郁,所画多为村民农妇、矿工织工之类,油画尚未充分成熟,但素描的根基却打得十分扎实。从三十三岁到三十五岁(1886-1888)是他的巴黎时期,这时他闯进了印象派的大观园,目眩情迷,不知所措。他接受了光和色的洗礼,换了一副调色板,学起印象派闪烁缤纷的技巧来,一度更尝试点画派的新手法。这时他的风格最不稳定,作品也较弱,但是锻炼了印象派的技巧,日后在表现新境时却正好用上。从三十五岁到三十七岁逝世为止(1888-1890)是他的表现时期。这时梵高的艺术经迅速的成长已臻于成熟,内心旺炽的感情活火山一般喷溅在画上,无论是人像、静物或风景,一上了他的画布,莫不蜕化为鲜黄、艳红、诡蓝、谲绿的奇迹。这两年的丰收期变化仍多,可以再分为阿罗、圣瑞米、奥维三个阶段:不过,奥维期虽然也有惊人之作如“奥维教堂”、“嘉舍大夫”、“麦田群鸦”,可是大半作品的结构已经松懈了下来,不能再维持阿罗期那种坚实而有光辉的饱满感。在阿罗的十五个月,杰作迸发而出,是梵高艺术生命的全盛期。
巴黎印象馆的梵高作品不算丰富。荷兰时期只得一幅“荷兰农妇头像”;其实这幅画不是一幅独立的作品,只是那幅代表作“食薯者”的局部草稿。梵高的画多数收藏在荷兰的美术馆里;他的侄儿,也就是西奥之子,小文森特?梵高(Dr. V. W. Van Gogh)的手里也有不少。巴黎时期只得五幅,包括那幅轻柔的“阮维叶市的人鱼饭店”。阿罗时期只得八幅,其中“午憩”是效米勒笔法,“阿罗的舞厅”则师高更画意,近于日后的“先知派”风格;其他五幅均为名作,依次是“吉普赛篷车营”,“比利时诗人巴熙像”,“阿罗的女人”,“自画像”及“阿罗的梵高卧室”。印象馆中梵高的画,大半是私人的捐赠,例如巴熙的画像便是诗人自己所捐。至于奥维时期,也有八幅,多为嘉舍医生之子保罗?嘉舍所赠,其中三幅“嘉舍大夫”,“嘉舍大夫的花园”,“嘉舍小姐在园中”,正是梵高住在嘉舍家里受其照顾时所作。我在这些灿烂的作品面前徘徊顶礼,恍如面对一个裸露的伟大灵魂,觉得那人的骨已冷了,但那人的灵魂仍是热的,如果我敢伸手去抚摩那些画,怕仍然是烫手会痛的。梵高,是我的忘年忘代之交,只觉得他的痛苦之爱贴近吾心,虽然曾译过一部《梵高传》,仍感不能尽意,很想将来有空再译出他的书信集,或是鲁宾医生那本更深入更犀利的传记《人世的游子》。
……